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六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人类脆弱性与跨文化传播的伦理起点》,作者潘麒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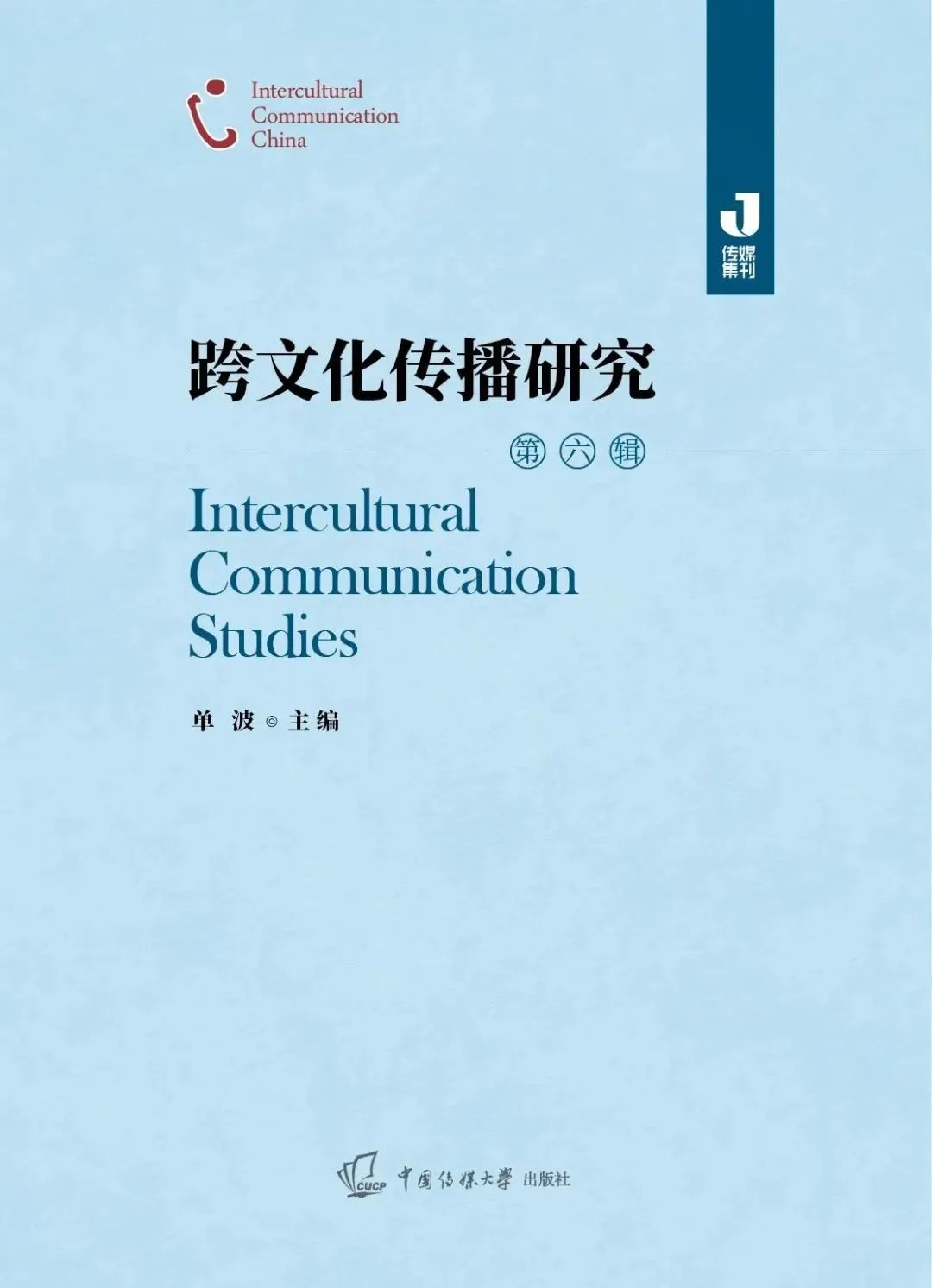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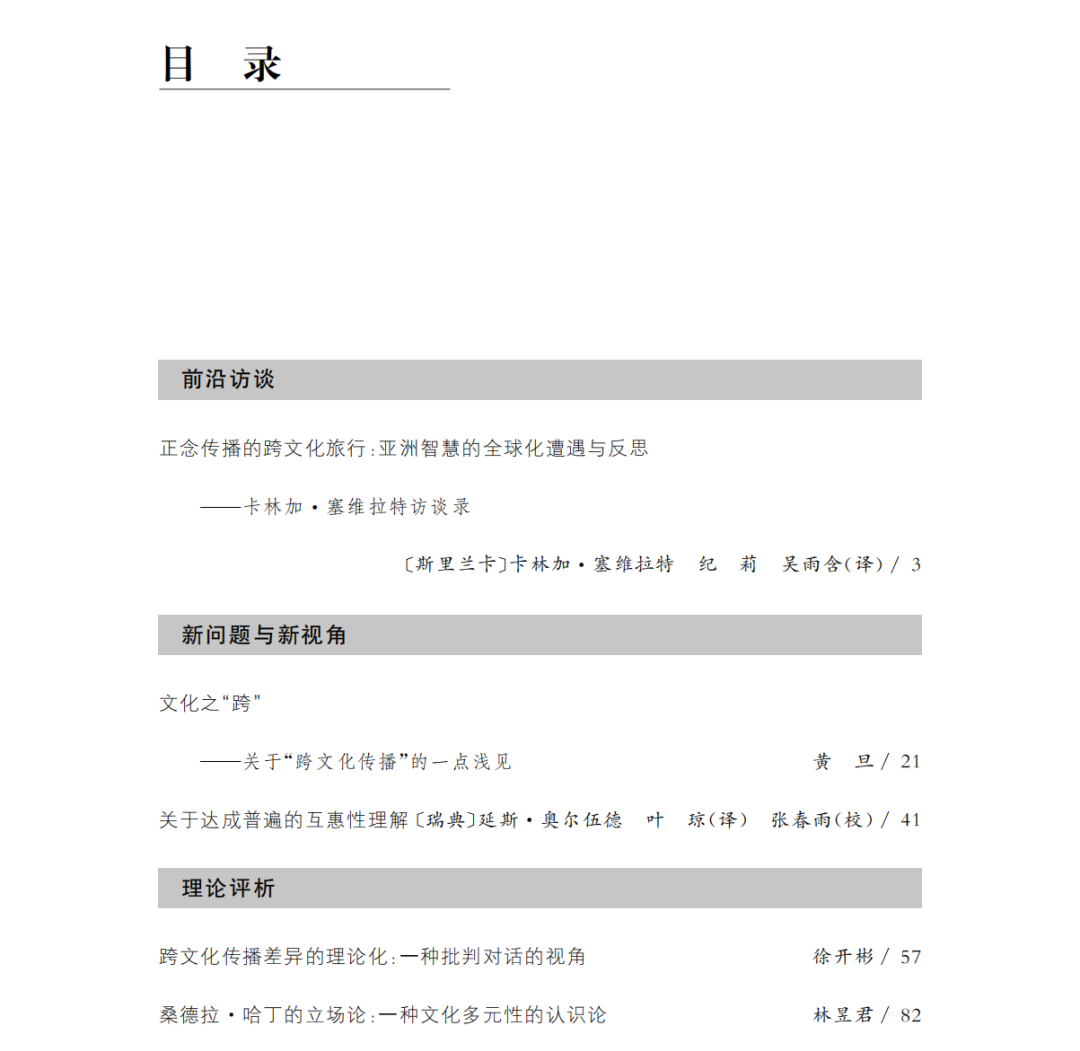
人类脆弱性与跨文化传播的伦理起点
潘麒羽
摘 要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多种文化间的交融与冲突为跨文化传播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为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良序传播,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其规范要求。本文主张,跨文化传播活动主体所共享的脆弱性特征可以为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提供证明。人类脆弱性是人类自身易受伤害的长久存在状态,其向外表征为人类活动中的种种不确定性、风险与挑战。脆弱性既是人类的内在属性,也是人类活动不可避免的外在特征。正是基于人类的脆弱性,人类才需要同情、理解、团结的主体行动能力与习俗规范要求。在人类脆弱性的视角下,跨文化传播所追求的不同文化间互惠团结的交往关系能够得到更好的辩护。人类脆弱性也为跨文化传播活动提出了“承认脆弱性”以及“与脆弱性共存”的规范要求。由此,人类脆弱性得以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伦理起点。
关键词
人类脆弱性;跨文化传播;互惠团结;包容差异
当代人类生活中的文化多元性不仅是宏观层面历史与传统的隔阂,还延伸至微观层面自我与他者的分歧。文化的多元性给跨文化传播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多样文化间的隔阂与分歧诉求着一种跨文化传播,它意味着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理解与合作。与此同时,文化多元性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引发的隔阂与分歧也对这种跨文化传播之可能性提出质疑。由此看来,我们可以将跨文化传播理解为一种“异中求同”“求同存异”的探索。在当下建构多元文化的良序传播关系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传播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这种传播关系如何可能通向平等且互惠的关系?”的基础性挑战。
面对多样文化之间存在隔阂与分歧的现实,寻求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基础是回应挑战的必经之路。杨云飞立足于一种普遍主义哲学思想的考虑,主张康德(Immanuel Kant)“以交往为内容的世界公民理念”与“在自我与他者互动中达到理性一贯性的启蒙思维准则”共同阐明了人类交流的合理性与如何交流的规范,可被视作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的哲学基础。诚然,康德的哲学思想能够为跨文化传播活动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辩护,但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所提供的先验普遍性也会遭到对其理论前提(诸如人类的理性能力、自由意志等)的否认与质疑,其普遍主义的哲学立场并非坚不可摧。可以看出,针对跨文化传播的探索工作还需要研究者不断添砖加瓦。
本文主张从跨文化传播的行动主体,即人类的内在属性与其活动的外在特征出发,探索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规范要求。这并不同于上文所提到的康德式先验观念论立场,而是尝试以人类自古以来共通的基本感官经验为基础,总结出存在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人类普遍经验,也就是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不可被否认的经验事实。这种经验事实的普遍性意味着其在现实经验层面的无例外性。在多元文化的叙事中,我们很难从人类的价值观念、思维逻辑与风俗习惯中找到真正意义上无例外的普遍性。然而,人类的肉身性的共通存在样态提供了可能,它便是人类的脆弱性。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纳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学者都强调人类自身与人类活动中的脆弱性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类脆弱性是人类自身易受伤害的长久存在状态,其外在表征为人类活动中的种种不确定性、风险与挑战。脆弱性既是人类的内在属性,也是人类活动不可避免的外在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的种种文化创造与自主性活动正是对脆弱性不同程度的回应。基于此,本文试图论证人类脆弱性是跨文化传播的伦理起点。
一、人类脆弱性与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最先感受到的便是文化间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寻求多元与差异中的经验共识与共同理解则是文化之间交流与对话的关键所在。单波指出,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以及交流如何跨越性别、国籍、种族、民族、语言与文化的鸿沟?”那么,人类脆弱性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首先,人类脆弱性是跨文化传播行动主体们共同享有的经验共识。思想史上不乏对人类自身属性的探索,而由于文化、传统、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行动主体对人类自身属性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普遍的常识经验,考虑到人类的肉身性存在状态,便会发现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都“具有同一性和连续性的动物性躯体”,并承受着由此带来的身体与行动的脆弱性、依赖性与无能为力。作为人类自身的属性,脆弱性意味着人类容易受到种种侵害和痛苦的影响,经常与诸如伤害、需求、依赖、关怀以及剥削等概念相关联。尽管不同文化对人类自身属性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人类脆弱性的普遍生存状态是经验层面上不可反驳的基本事实。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类脆弱性阐述的是人类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可持续性受到侵害的可能性。”由于人类在生命的不同成长阶段会面临不同的威胁,也可能遭受诸种外部不安全因素诱发的不利影响,人类脆弱性呈现出内部的生命周期性与外部的系统结构性,并且可能不断变化和长期存在下去。由此看来,无论跨文化传播的行动主体们在文化、传统、观念等层面存在多大差异,都无法逃脱脆弱性的规定与限制,也都共享着脆弱性的体验。
其次,人类脆弱性有助于跨文化传播的行动主体们形成完整真实的自我认识,加深多样文化间的共同理解。麦金太尔认为,人类脆弱性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我们的脆弱性和苦难,以及我们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这两组彼此相关的事实明显具有独特的重要性,任何作者如果想要令人信服地描述人类状况,都必须赋予它们核心地位”。脆弱性说明了我们与非人类动物之间的同一性与连续性,人类的欲望、判断、行动等创造文化的要素并没有完全与非人类动物的属性相脱离。在巴特勒看来,脆弱性“先于‘我’的形成。它是一种条件,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暴露’于相互关系之中,‘暴露’于他人的影响之下”。人类脆弱性这种事实不仅是日常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先在的存在状态,即人类肉体的可侵入性和易受伤害性。伴随着这种脆弱性,降生后的人类更是无从选择地落入某种交往关系之中,并被动地承受着这种交往关系对自身原初的教化与塑造,这种不可避免的依赖与无能为力既是人类脆弱性的延伸,也是人类理解自身、理解他者的逻辑起点。
可以看出,人类脆弱性为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普遍的人性基础。人类时常因自身的脆弱性而感到无能为力,需要在与他人、群体相互依赖与合作的关系中谋求兴旺发展。尽管各类文化中存在对人类本性的多种解读,但人类的脆弱性属性揭示了诸种解读下的基本事实,为跨文化传播在行动主体的层面提供了前提共识。跨文化传播能够以人类自身的脆弱性属性为起点,进行多样文化间共享相同前提的交流、对话、理解乃至合作。由此,人类脆弱性为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提供了说明。
二、人类脆弱性与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
尽管人类自身的脆弱性属性为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可能性提供了辩护,但我们不能仅仅基于跨文化传播中行动主体们的共同属性来探索跨文化传播的基础,而是还需要结合行动主体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行动特征来应对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质疑与挑战。在这一方面,不同文化对人类脆弱性的普遍认识以及克服人类脆弱性的共同追求,为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提供了说明。
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现实中的人类并非如理论家设想的那般完满自足,而是有限的、脆弱的存在者,其行动也极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人类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外,并不是总能得之所欲。纳斯鲍姆将这种现象称为“善的脆弱性”,她认为人类对善与美好生活的追求会受到运气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具有脆弱性。正是源于善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人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多种善的冲突和矛盾,个体的外在善难以逃脱偶然性命运,人类的美好生活也愈加脆弱。
当人类脆弱性向外表征为种种实践活动时,它便与运气、偶然性、不确定性、风险等概念紧密相连。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人类活动的这种外在的脆弱性。首先,它与人类自身的内在脆弱性相伴而生。人类囿于自身的脆弱性,或是难以辨别情理是非进而做出错误的选择,或是由于意志薄弱而难以坚持正确的行动。其次,在文明冲突、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人类活动多元价值评价标准加剧了其脆弱性的外在特征,为我们的行为选择增加了更多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最后,环境灾害、战争、制度不当等种种加剧个体依赖性与无能为力的外在因素都时时提醒着我们,脆弱性从未远去。
人类的依赖性与脆弱性表明人类本质上是一种有所需求、有所依赖、有所依恋的存在者,人类活动的脆弱性特征也表明了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这与跨文化传播“以交流跨越鸿沟”的核心关切不谋而合。跨文化传播的活动是在主体和主体间形成的互动过程,它进一步把“主体间性转换成文化间性,形成文化的互惠结构,提高每一个个体超越自身和与其他文化互动的能力,从而建构完整的自我意识”。在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超越自身、合作互惠———这既是克服人类脆弱性的基本要求,又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目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进步也可以被看作抵御脆弱性的漫长斗争。通过诉诸理性和技艺的庇护,人类试图摆脱外在运气与风险的摆布。由于对充满变数与偶然性的命运心存忧惧,人们努力寻求确定性,其实就是在以某种方式克服由人类内在的脆弱性引发的依赖性与无能为力,进而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的自主价值。正如纳斯鲍姆指出的:“消除人类生活中的运气,就意味着由我们自己来掌握生活,同时排除一切有赖于外界的和不可信赖的因素。”
面对日益复杂的人类生活与多元文化,仅仅通过个体或单一文化共同体的努力,无法完全克服人类脆弱性的不利影响。然而,跨文化传播的特性与优势使人类得以在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中体会人类脆弱性的存在状态,吸收借鉴不同文化的智慧与长处。由此,人类的脆弱性状态恰恰呼唤着良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而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正是承认这种脆弱的现状,并试图通过增强抵抗脆弱性以及自主选择的能力,最终与之和谐共处。
三、人类脆弱性与跨文化传播的规范要求
在人类脆弱性的视角下,不同文化得以拥有基于普遍共通经验的前提共识,从而使跨文化传播成为可能。由人类脆弱性带来的种种不确定、风险与挑战是不同文化共同存在的现实难题,需要借助跨文化传播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互惠团结的交往关系,这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因此,人类脆弱性成为跨文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这自然为跨文化传播提出了第一种规范要求:承认脆弱性,促进文化间互惠团结。同时,尽管对脆弱性的克服与超越是跨文化传播的驱动力之一,但无论是人类自身的脆弱性,还是由其延伸出的人类活动的脆弱性外在特征,都是人类长久存在的普遍经验,不可避免,亦不可消除。人类脆弱性为跨文化传播提出的第二种规范要求便由此产生:与脆弱性共存,包容文化间的差异冲突。
人类脆弱性为跨文化传播提出了“承认脆弱性,促进文化间互惠团结”的规范要求。尽管脆弱性作为人类的一种普遍存在状态可以在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中得到直观验证,但脆弱性仍然难以成为跨文化研究的主流视角,思想史中的经典理论也鲜有从脆弱性切入的。由于脆弱性往往是苦难的根源,它难以得到肯定与赞美,但这并不妨碍脆弱性应当获得承认并被认真对待。在跨文化传播的活动中,承认脆弱性就意味着融入脆弱性视角,思考由人类自身的脆弱性属性而形成了哪些文化观念。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可以看到这些观念的对应形态,以及它们各自处理实践问题时呈现的各异模式。然而,在承认人类脆弱性的基本前提下,我们会发现上述种种文化观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有着相似的与可比较的因素。正是由于人类都具有脆弱性的基本属性,人们才得以形成了一种以合作为基本模式的依赖互助关系,这种关系催生了诸如仁爱、关怀、团结等文化观念。巴特勒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并不只是用来描述主体形成过程的历史事实,它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的规范面向,我们必须依据这一层面思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状态,以及个体生命与人类生活中诸种结构性因素的脆弱不安,既是人类长久存在的生存状态,又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力图克服和超越的。这些普遍共通的人类经验构筑了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的基本框架,并需要通过同情、关怀、团结等伦理规范实现人类生活的繁荣兴盛。
了解并承认人类脆弱性是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前提要求,而“我们的依赖性、理性和动物性必须被置于相互关系之中来理解”,这与跨文化传播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文化间的共性、差异、冲突与传播都需要在一种相互交往的关系中被加以反思与探索,交往之中呈现出的脆弱性正是不同文化受众的共同处境。承认这种脆弱性与交互关系,也就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做出了互惠团结的道德承诺。我们可以从日常经验中发现多种保证互惠团结关系的因素,曹刚将这类维持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归纳为三个方面:以道德共识为基础的精神纽带、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物质纽带、以互助友爱为基础的情感纽带。基于人类脆弱性的视角,我们可以在跨文化群体之间依次找寻到上述三种类型的联结纽带。人类脆弱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依赖性打破了对个人纯粹理性自主的抽象设定,原子式的个人主义道德观并不足以回应人类这种关系性存在者提出的道德诉求,而“道德的集体主义”通过引入他者伦理精神实现对人类脆弱性的积极回应。同样,人类的脆弱性也决定了人类对生产合作与物质交换的迫切需求,人们进而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相互联结在一起的互助友爱的情感。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间交流并寻求承认的过程,巴特勒点明了其中包含的与他者共存的意味:“这种需求并渴望他者的交流过程发生在最广义的语言之中,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存在。要求他人承认自己,或者要求承认他人,并不是要求承认人们的既有存在,而是追求变化,引发改变,冀求同他者相关的未来。”人类脆弱性引发的相互依存关系与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内在逻辑相一致,人们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不断重复着与他者之间基于共同文化认同的彼此承认,并在交往过程中寻求着与他者共存的共同繁荣。因此,跨文化传播活动便内在蕴含着互惠团结的规范要求。
我们已经通过人类脆弱性的视角看出跨文化传播活动中面向他者的内在精神。他者往往意味着与我的“差异”,其实跨文化传播本身就蕴含着“在差异中寻求共识”的过程。与此相对的是,跨文化传播的障碍恰恰在于“同质化所带来的褊狭的传播机制,以及在以一种文化理解他者文化、支配他者文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同质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跨文化传播的过程是寻求彼此承认,并不追求同质化的确定统一,而追求差异性的共存。然而,当我们引入人类脆弱性的视角时,文化间的差异性还暴露出可能往往被我们所忽视的异质文化的弱势地位与不平等问题。我们可以在人类历史中发掘诸多“落后文化”受到“先进文化”的冲击、侵蚀乃至最终消亡的案例。然而,上述这种以优劣划分不同文化类型的做法并不符合跨文化传播的基本伦理精神。反之,“保持各自的文化价值,同时又保持平等的跨文化对话,是跨文化伦理的底线”。在这一问题上,人类脆弱性的视角为跨文化传播带来的启示在于,人们需要认真分析和对待异质文化所呈现的所谓弱势倾向,尊重差异,而不是强行寻求共识。承认不同类型的文化可能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处于某种相对的“弱势地位”,这种强势与弱势的抽象差别为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去理解不同文化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适应性及其价值语境。正如单波所指出的,跨文化传播需要“建立主体间流动的共同价值,但不走向普遍主义或本质主义,也不认为存在全球核心价值,而是尊重对共同价值的多样表述,丰富共同价值的内涵,实现伦理价值的无限创新性”。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理解他者文化便是理解自身。我们应该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理解并接受差异性,在差异中理解自我的意义,在对话中建立互惠性理解。与脆弱性共存,包容文化间的差异冲突,便是人类脆弱性为跨文化传播活动提出的第二种规范要求。
人类脆弱性分别为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做出了辩护,并向跨文化传播提出了“承认脆弱性,促进文化间互惠团结”以及“与脆弱性共存,包容文化间的差异冲突”的规范要求。可以看出,跨文化传播活动与人类脆弱性密不可分。人类脆弱性所要求的同情、理解、团结等主体行动能力以及相应的习俗规范,与跨文化传播的主体“根据具体语境、性格、目标及期望创造交互式文化认同,特别是人有移情能力,即站在他者的立场去思考、去体验、去表达情感的能力”不谋而合。人类脆弱性与跨文化传播的伦理精神相互交融,它们共同追求着文化间的互动交流、合作共享,共同捍卫着文化的价值多元与繁荣发展。在此意义上,人类脆弱性正是跨文化传播的伦理起点。
引用参考
潘麒羽.人类脆弱性与跨文化传播的伦理起点[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2(02):99-108.
作者信息
潘麒羽,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讲师,电子邮箱:pqy199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