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七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对话如何可能?》,作者肖劲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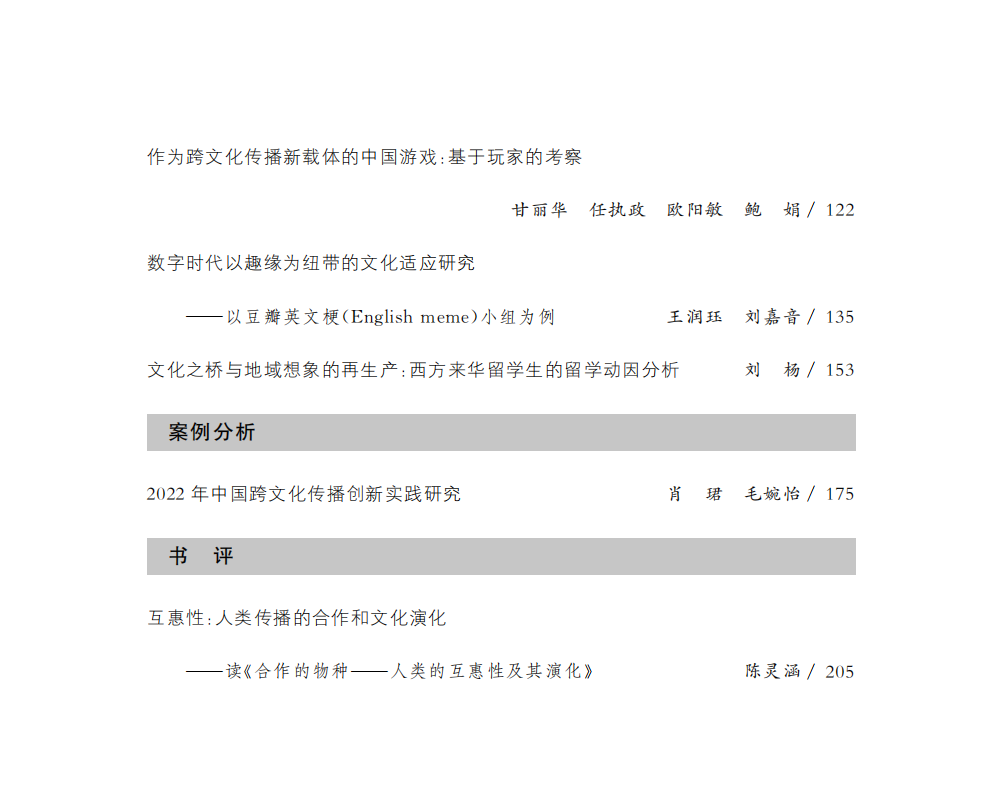
对话如何可能?
肖劲草
人类寻求对话,但又时时被“对话如何可能”困扰。要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关于对话的伦理分析,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讨论对话的伦理价值及其具体表现;二是分析和反思对话现象,发掘其中的伦理因素、伦理前提和价值取向;三是讨论对话者应拥有何种美德来让对话变得更好或克服其局限。
作为一种平和的、多边的交流形式,对话已在众多实践领域展现其价值。就认知而言,苏格拉底提倡使用“辩证法”来发现思维和观念中的矛盾和逻辑,重视以对话的方式追求真理和智慧;伯姆强调对话对“共同思考”(think together)、共享性(participation)思维的重要性,注重对话带来的共同性、共享性、参与性等在认知方面的贡献。就伦理而言,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哈贝马斯等倡导的对话伦理学试图克服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中的“独白性”和“严格主义”,优化关于普遍性道德规范的辩护,对基于共识与交往奠基之上的道德规范提供形式与程序上的保证;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为普遍性的道德规范提供论证,分析依靠商谈形成共识的理想情境。就存在论而言,马丁·布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巴赫金挖掘对话存在论上的价值与意义,强调人是思想着的存在,人的思想具有内在的对话性。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强调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思想并非主观的个人心理产物,而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际。人也是关系性的存在,在将他人客体化、工具化的“我与它”的关系之外,马丁·布伯把目光投向“我与你”的关系,指点对话的路径,揭示对话性是这种关系的重要特征。哈贝马斯与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认为对话将自我展现为参与者、共在者,自我在与超越者和他人的对话中敞开,进而理解人的存在。由于对话对思想和关系具有建构性,因此对话内嵌于生存,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上述领域中,对话在推动互惠性理解,提升交流效率和认知水平,在促进共识、协调行动、维护和平等方面具有丰富且深刻的伦理价值,其发掘和阐释需要实践者和研究者携手推进。
根据伯姆的介绍,英文中的“对话”(dialogue)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dialogos”,其中“dia”的意思不是“两个”而是“穿越”(through),“logos”的意思是“词”。如此,对话呈现一种“……经由语言中介而生成……”的结构,这也符合伯姆看重意义生成、知识生成的理解。对话好似一台机器,会在话语互动后产生“新东西”。伯姆也以此将对话同“讨论、辩论”(discussion)、谈判(negotiation)区分开,因为讨论、辩论只是为了说服,不产生“新东西”。但在古希腊文化中,“logos”除了“词”的意思外,更代表着“理性”,“dialogos”意味着“经由语言”,更意味着“经由理性”。理性的人可以和非理性的人说话,却难以想象两者间的对话,“和疯子对话”似乎蕴含着矛盾。对话要能进行,对话者要相互理解语言和言说的内容,但这在“和疯子的对话”中难以实现,因为理解需要理性的保障。如此,“dialogos”要抑制“非理性”,缺乏理智者、暂时无法使用理智的人无法成为真正的对话者。人们在日常的观察中也能发现,对话可以轻松,可以严肃,但不会疯癫。常人可以同疯癫者闲谈,听疯癫者言说,但疯癫者无法成为对话者。疯癫是对话的终止。
目光转向中国,古文中的“对”“聊”等词呈现了中国文化关于对话的体认。根据《字源》的分析,“对”有应对、对答之意,其内涵与外延比日常使用的“对话”要窄,但“对答”突出了话语互动中的“回应”,其虽为单向的,但要求各方“同频在线”,而非自说自话。要“对得上”,就不能是独白或伪装成对话的多人独白。“聊”字则更有伦理意蕴,聊字从耳,一个表示说话的词语不从言,而从耳,突出了“听”在话语互动中的重要性。言说是对话的一方面,听则是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境中,能够去听、愿意去听、有耐心去听更为困难,更有价值。善于倾听是交流的美德。中国文化有重视“听”的传统,“圣”的繁体为“聖”,字中有耳,圣人是善于听的人。如果说英文中的“dialogue”突出“logos”所彰显的“语言中介”和“理性基础”,中国文化的“对”与“聊”则突出了“回应”和“聆听”的价值。
当下“对话”的使用强调对话者之间的平等。权力是对话的重要背景因素,强与弱、高与低、先与后、多与寡、傲慢与谦卑,乃至对手之间若要对话,需要暂时悬置权力的差别,维持交流中的平等。平等意味着对话者遵守相同的话语互动规则,大家要都能发言,能聆听彼此,能相互提问、相互质疑并能要求对方回应。平等及其蕴含的相互性将对话同训话、布置任务、下达要求区分开。对话是一个平等的场域,利益不一的个体,权力不同的团体,势不两立的对手,因为各种缘由,愿意在对话的场域中暂时悬置优势、成见和傲慢,进行平等的沟通。不平等的人之间,历史中的奴隶主和奴隶之间,贵族和平民之间能愉快地聊天、讨论问题,但“位高”的一方没有回应的义务,可以对回应说“NO”,“位低”的一方则没有提问和提要求的机会。还有一些以实力为后盾的谈判,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所谓的交流不过是桌面上的“按力分配”和讨价还价,不具备对话性。平等还意味着在对话的情境中,保持基本的尊重和礼仪,不能一言不合就掀桌子。发生在不平等者之间的对话最困难,也最珍贵。
如此,人们可将对话的核心内涵初步视为以语言为主要媒介,以理性为基础,以彼此聆听为前提,以交流中的相互性和平等性为特征的话语互动方式。日常交流中“与文本对话”“与自然对话”等表述也很常见,“文本”和“自然”因能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人的所思、所感、所问,激发人的思考而被拟人化为“对话者”,因此具备了对话性。这些可以被视为类比意义上的对话。
对话召唤着对话者的美德。第一,平等是对话的特征,平等相待是对话者最重要的美德。平等涉及对话者间的相互承认,相互承认后,大家才能获得对话的“席位”,上得台面,在同一张桌子上交流,而非台下听训或身后旁听。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大型对话,作者是对话的组织者,让作者同具有同等价值的主人公平等交流。但在现实中,平等交流并非天然的产物,总有或明或暗的标准在规定谁有资格成为“我”的对话者,规定“我”有没有资格成为“他”的对话者。在对中西文论互鉴的讨论中,使中国文论在“中学西传”中获得平等的主体性对话地位是相关领域学者的重要任务。弱势一方要成为强势的对话者,即便是暂时的、临时的对话者,也需要额外的努力和付出。相互承认的标准是什么?谁有资格成为对话者?对话的话题是什么?如何确定对话的规则,这一规则是否不偏不倚?其根据和程序是否合理,经不经得起辩护?这些都是平等背后包含的现实与伦理考量。平等相待有赖于对话者的修养,有赖于对话者对自身所处文化、政治与经济地位及其根据的觉察与反思,有赖于对话者面对世界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姿态。
第二,聆听是对话者的另一项美德,没有聆听就没有对话。人是言说的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我言说,我存在”有其自然倾向。此外,权力也总爱“插嘴”,有将对话变成一言堂的欲望。听清、照办、免谈,凭借实力跳过对话是权力言说的常见姿态,更有假装倾听、表演对话和利用对话的欺世欺人者。在人人都有麦克风,表达和交流部落化的环境下,聆听面对着克服言说欲、拒绝权力的不当诱惑、走出成见等诸多挑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美德在于良好地实现理性,美德作用于情感欲望的领域时,被称为伦理德性,作用于理智领域时被称为理智德性。我们可以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方式,但搁置其理性为先的立场。聆听首先是伦理德性,要求对话者能运用包括理性在内的各种能力,例如借用习惯、礼貌乃至怀疑论的力量,管理、反思和悬置一些激烈且具有对抗性的情感和欲望,暂时悬置想去言说的主体性,将自身置于去倾听、去理解的位置。聆听也是理智德性,要求聆听者具有倾听的智慧,不仅能听懂字面内容,还能深入理解,听出弦外之音(不明说的话)、难言之隐(说不出的话)和不传之秘(不想说的话),并知道何时需要倾听,何时需要言说,进而把握听与说之间的尺度。
第三,对话者还要有一定的勇气。在某种意义上,对话意味着伦理冒险。当言说者彼此承认,变成平等的对话者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马丁·布伯笔下的“我与它”的关系,不再仅以有用的视角看待彼此,还赋予彼此尊重和信任,并在对话中呈现或多或少的真诚,即言说自己相信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向对话者敞开,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要。但由于这种平等的交流可能是暂时的,对话并不一定能帮助各方建立长久的“对话关系”。因此,敞开、信任和真诚都面临被滥用的风险。另外,成为对话者还意味着面对可能的质疑、批评和要求,在“我与你”的关系中遭遇如怨恨等的第二人称反应性态度。这时,对话者无法“退一步海阔天空”,将自己从“你”变为“它”,伪装成不用回应、无须面对、不必承担和不受约束的“局外人”。如果说我愿意与谁对话,会检验对话者的价值观和格局,那么,我是否愿意成为对话者,是否愿意同陌生人、竞争者乃至反对者对话,将考验对话者的勇气。人在对话中不一定收获肯定、理解和赞美,也要面对否定、误解与批评。对话是契机,也是冒险。
第四,对话者还应审慎。对话有长处,也有短处,审慎能让对话者看清对话的局限与边界。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一书中曾对赋予对话过高的伦理价值提出不同见解,数千年来无论是交流技术的提升,还是对交流主体的建构,追求灵魂之间完满理解的努力终归无奈。传播学的目标不限于追求完满的互相理解,还应看到协调行动的价值。对于一时难以理解的言语,人们不妨任其“撒播”,“将意义的收获交给接受者的意愿和能力”。对话的部分局限源于其对理性的依赖。理性为对话的有效和相互理解提供了基础,但这种依赖也牵扯诸多伦理问题。一是理性的话语能展现的内容和意义是有限的,很多东西依赖非理性的显现方式。很多情感、体验和感受难用语言表达,一些真理、价值和启示需要通过矛盾或不可理喻来展现。理性无法超越经验和历史的局限来描绘、诠释和揭示某些意义,犹如对话无法穿越经验的限度与沟壑挽回柏拉图笔下的两次死亡——苏格拉底之死和走出洞穴者之死。二是权力有可能渗入理性,将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乔装成“真理”“知识”或“合理性”,抑制一些本该对话的内容。因此,某些疯癫或荒谬可能穿透迷雾,也常有人借疯人、痴人和幼童之口来“道说”,但却因“无逻辑”“不合理”或“自相矛盾”而难以融入当时的对话,只能“随缘撒播”。因此,对话者应保持审慎,对“理性的对话”和“对话的理性”保持一定程度的反思,在具体境遇中思考其边界和根据。
如此说来,对话伦理的实现需要对话者的修养、心性和智识,也需要建构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并对交往世界中的各种逻辑保持审慎,动态地思考和调整各种逻辑的使用边界。最为重要的是,当我们的内心为对话所召唤时,对话的可能性就悄然降临。
引用参考
肖劲草.对话如何可能?[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3(01):1-6.
作者信息
肖劲草,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编辑、武汉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电子邮箱:282459306@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