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八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共情传播:谁能与我共舞?》,作者刘军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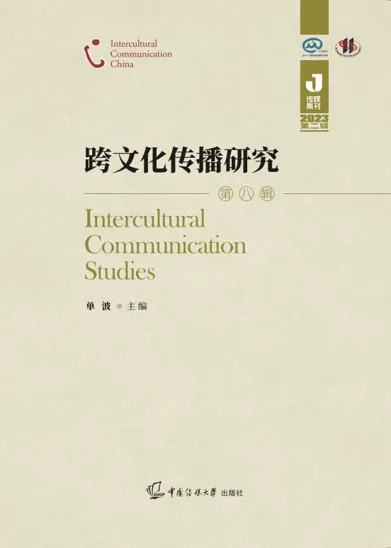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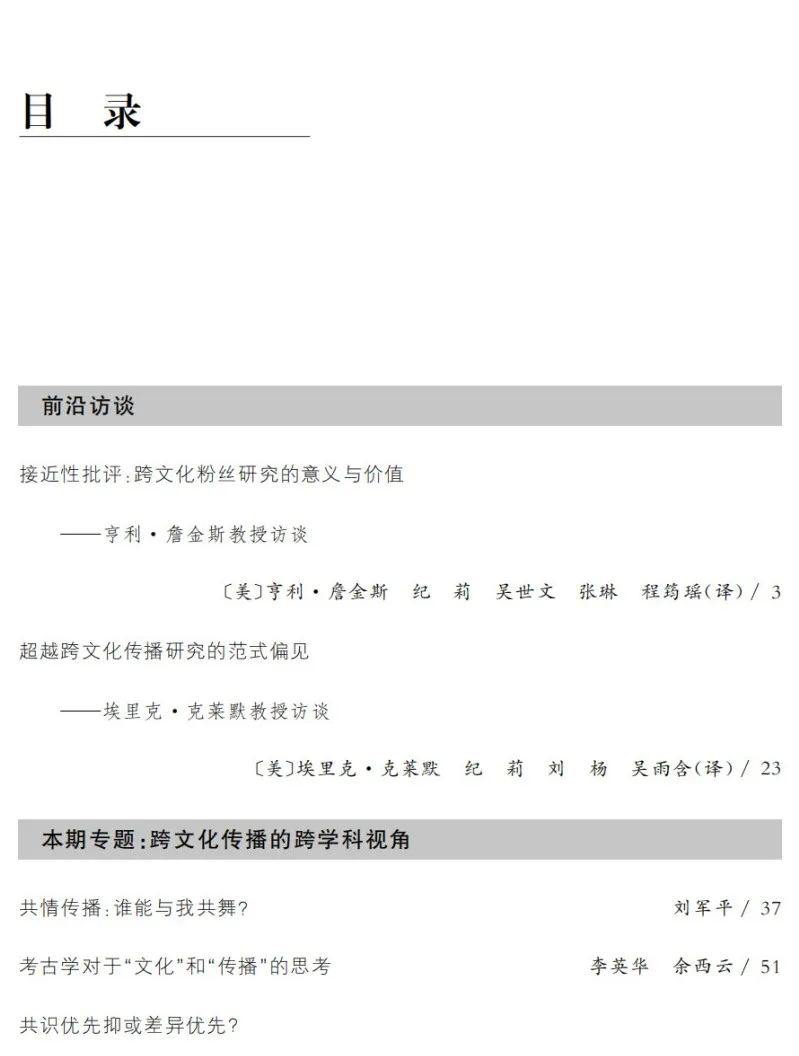

共情传播:谁能与我共舞?
刘军平
摘要: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探讨了共情传播的含义,分析了中西共情传播的基本范式的基本特征,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通共情模式,论述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及海德格尔解释学视野下共情传播的哲学意义。本文认为,承认文化他者的差异性并在差异性中寻求同一性是传播共情的基础。各种不同文化间性,形成了混杂共同性,正是共情因素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领悟世界的他者性和自我性之间存在关联性,也就意味着共情。放弃主客二分的工具主义思维方式,转向“我族相对主义”,有利于文化之间共情的契合和理解。最后本文提出,随着新技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共情主体、共情对象及共情方式将面临新的挑战。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平台创新
共情作为心理学概念,在当下的传播学领域被频繁使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对“共情”(Empathy)的界定是:“理解他人情感和问题的能力,意指同情、同感,共鸣。”狄尔泰用德语词“Hineinversetzen”来表示共情的“感同身受”,用“Nichbilden”来表示模仿或再创造的“重构”,用“Nacherleben”来表示“体验”内在经验。共情的基础是理解和欣赏,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审美判断力的达成提出了“共同感”(Sensus Communis)的概念,认为欣赏判断必须依赖一个主观性的原则,只能通过情感而不是概念传递。“情感的这种可普遍传达性却是以共同感为前提。”只有在共同感的前提下,客观的对象通过主观必然性,才能达成普遍赞同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个人的情感和他者的情感彼此符合客观必然性的条件,是双方能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加达默尔说:“共同感在这里显然不仅是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而且它同时是指那种导致共同性的感觉。”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解释了传播过程是“一种双向特点”的关系,该关系的成功与否在于“分享信息符号”的意义。共情与传播的结合,构成了当下人们解读人、信息、媒介及文化现实的另一种视角。易言之,共情传播涉及多种文化、多种因素、多种层级、多种传播语境,共情能力的提升依赖于对共情文化较全面的考察。其传播的有效性必然包含着对自我的认知,对文化他者的共情及对当下传播新技术新语境的洞察与理解。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从不同维度、不同理论视角来认识共情传播的影响与作用。
一、中西共情范式的特征
共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基调。它是一种从差异中提炼普遍,强调共同感,避免冲突,主张和谐共存的共情模式。这种交互沟通文化模式,在《易经》《尚书》中出现端倪:一阴一阳一静一动互动,生化五行再生化万物,充满了生命的目的性意义。中华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说明了“人心”与“道心”的关系,提倡恪守道心的中正之道,突出了尽性的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先秦儒家《中庸》中天道与人道的参赞化育,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融通,皆说明个性与客观外界和谐统一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天地共情,社会共情、人际共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点。从至圣先师的“仁爱之心”到亚圣的“恻隐之心”,到宋儒的“蓄草”而感怀“四时佳兴与人同”,皆揭示了传统中国重视至善,肯定人道与天道的有机连续性和相互依存性。“于是,在达至儒家圣人境界的过程中,具有深沉宗教精神的人与‘天道’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契合。”就人际共情而言,儒家推己及人,忠恕之道、发明本心等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注重“他人取向”以及融合心性内外的能力和共情力。中国心性哲学的现代转化含义是融通心性的“外理化”和“外理化”,“合内外之道”。“这是因为心性本来具有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圆融差异的潜能,而其本身的结构与过程也如‘圆性论’所示就是此一潜能。”自我与外物、自我与他人的圆融对话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共情呈现方式。个体由物而“感我”,联“通”物我,与他物达成感通,方能生起事象,涵摄他物,形成生生不息的感通路数。唐君毅曾提出感通论作为阐明中国哲学的一种模式,值得重温。易言之,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儒家仁爱学说、和谐理论等为现代社会的各种共情传播提供了中国式感通共情范式。这种“天人合一”观认为,自然与社会、天与人,存在一种“取象比类”的同构关系。《易传》所说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主要强调的是君子借由人格、境界的修养,能够与天地、日月、四时和鬼神相合,能够“神遇万物”,“美利天下”,从而实现形而上的超越。相较于中国的感通共情范式,西方的共情范式聚焦点在于知识论,其知识优先于价值,体现了一种机械的心理的投射,或者是自我,本我与超我的人格分裂的暂时和解。在知识论范式关照下的“情”,只不过是需要认识的不同的认识论范畴。进而言之,西方范式共情的目的是理解知识中的“人”的心灵。或者说,马丁·布伯所言的“I-Thou”关系,与其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不如说是人与上帝临在的化身的关系,本质上形成了世俗与神圣的二元对立状态,或者是人与工具理性的经验共在。两种范式各有所长,“道并行而不悖”。相比较而言,中国式共情范式中人与“自我”,“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超越的终极实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存在紧张与分裂,从而构成了儒家整体和谐的共情生态系统。在这种共情生态系统中,从自我之“诚”,过渡到成己成物,个人、家庭、社会、天下、自然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密切关联链接,进而凸显了其独特的伦理价值共振共生系统。无论是性即理或心即理,皆体现了原性与理的圆融融合。这种时中、中和的宇宙观、伦理观和生态观,体现了整体性和共生性的和谐关系,个体与整体的平衡和整合共情。中国儒释道文化的万物一体的整体观,万物相生相依的辩证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可作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跨文化传播的资源,被予以挖掘和进行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因为跨文化传播是一种全球性的关联互动,涉及多元文明对话,其中的中国式共情范式可为当代跨文化传播理论提供另类范式。从这一点来看,斯韦尔论及传播的社会功能时,说明了跨文化传播环境与不同社会的相关性、以及代际之间传播社会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乃“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二、解释学视野下的共情与理解
从解释学视野看共情传播,它不仅存在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之中,也可以指任何主客观之间的交流与应答。这种应答是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到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关注的理解与解释之维的重心。主体独特的审美体验和代入是人们熟知的一种共情关系。共情能力,指的是一种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从而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心理解释中的理解者的共情能力意味着超越自身的认知,而去理解作者意图的能力,它既是一种信息编码解码的能力,也是一种重建作者心理意图的能力。用这种心理解释学说明解释者与作者的关系,“就像一个灵魂试图与另一个灵魂进行交流一样”。作为交际者,解释者和译者,我们如何与信息的发出者站在同一层级上?那就是个体在自身努力和心理移情(mental transfer)的基础上,运用解释学循环方法,在整体与局部之间循环往复才能实现。作为跨文化交际者,对自我与他人的理解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环运动的,与自我与他者的理解才能趋于一致。“理解话语首先做到和作者理解得一样好,然后做到比作者理解得更好。”这一命题并不意味着,跨文化传播的信息交换是一种线性重复,而是一种重构,一种永无止境的创造活动。所以,共情能力是一种理解他者的对话能力,对话关系在不同语境和不同时代做螺旋运动展开。共情并不只是意味着个体与他者趋同模仿,而是个体在追求普遍性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特品质。从解释学角度看,狄尔泰对孔德以来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以突出人文科学的理解力。“自然科学说明自然的事实,而精神科学则理解生命的表现。”所谓的“狄尔泰鸿沟”强调的是,自然科学采用外在经验模式,以“假说”为主要特征,因而自然科学的客观有效性是超时空、超历史的;而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则采用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凸显体验和内在经验以及历史意识。共情能力在人文科学的理解中占据突出位置,其注重的是生命体验和效果历史。狄尔泰尤其重视共情因素在理解和解释中的作用,反复说明共情能力(Einfühlung)不是内省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过程,而是指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感同身受地去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狄尔泰认为“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以心传心,是因为思维的契合和普遍性存在”。同理,跨文化传播的共情,并非顿悟、玄思和心理想象,而是一种生命体验。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某种神秘的心理传递的过程。英文“temperamentally suited"指的是自我与他者的意气相投或心心相印,从而形成一种感情纽带(bond)。跨文化传播的“境遇意识”,在海德格尔的视野中成为“此在”与“与他人共在”,或者说“此在”就是“共在”。“共在”作为‘在世界之中与他人共在’,讲的首先是‘自我’与‘外物’以及‘他人’之间的、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不可切断的关系。他们之间相互蕴涵,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与影响,任何一方不可须臾缺失。”作为“此在”敞开的式样,表现为情态、理解和沉沦,“与他人共在”则揭示了世界与他人的“对象意识”。“因此‘存在着’对于‘此在’的存在,是一种形式存在的表现,也即‘在世之在'是‘此在'的基本状态。”(Being-in is thus the formal existential expression for the Being of Dasein ,which has Being-in-the-world as its essential state.)在我看来,海氏的共在是共情的基础存在。舍此,无法由共情推出共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尊重他人存在、他人价值、他人主张、他人文化和他人体验。唯其如此,用共在作为共情的包容性基础,跨文化交际和传播才有可能。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接续着狄尔泰所说的生命体验、理解和共情能力。理解从世界中的投射维度显露自身。跨文化主体和主流媒体呈现的本真状态是一种自我显露,非本真状态是一种沉沦,二者关系凸显了媒介和文化精神价值沟通交往的辩证现实。这种关系是从主体间性的互动到文化间的互动,通过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解者的对话凸现。具体而言,海德格尔重新定义了“解释学循环”,即从文本的整体到局部的关系,转移到存在者在不同语境之下的生命体验的“此在”循环。唯有如此,跨文化阐释的有效性在这种普遍主义关照下,才真正能够成立。当自我与他人的信息沟通、话语冲突、文化差异与情感态度出现相抵梧的阐释,只有融化在双方共享的共情之中才可能消弭。“与他人共在”的话语传播的基础是共情与角色定位,连接自我和他者的是文化间性的解释循环,化解二者之间的张力则依赖单波所说的“互惠理解”。从个体角度看,“互惠理解”即是体验者进入一种“神入”状态,正如《听闻远方有你》这首歌唱的那样:“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这种同理心的共感,植入了他人的感受和情绪,进而做到双方相互理解和情感上的融洽。传播者带着共情体验,进入了一种心理投射状态,强化了感受他人内心体验的过程。
三、辩证共情与文化他者
共情含义的另一个维度则是理解他者问题的能力。当两种文化相遇,自我在与他者的遭遇中,更加理解并突出自身的独特性,互补互证、双向阐发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在新的文化场域(Cultural Field)之中,二者便由于各自的特殊性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性质,必然建立一种新的潜在的共生关系,成为既非前者又非后者的新的融合品种,从而促进了异质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后殖民学者霍米·巴巴用“混杂性”和“含混性”来描述这种话语和身份特征。文化他者的意义在转译之后被传译,独特性和普遍性达到一种遭遇的平衡,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辩证共情。“和而不同”也可以说是这种辩证共情的另一种表述。辩证共情的同一性是承认对话双方存在矛盾,但这种对立面并不否认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结和相互吸引。自我意识和自我行为的展开,受制于统一性的框架。一与多的关系也就是多即是一,一即是多的辩证存在。对立统一规律不仅是客观事物的辩证法,亦是辩证共情的方法论。因此,文化传播的共情应该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张力存在。解决“文化折扣”和“对空言说”的途径,以及消除冲突和偏见,在于双方除了相互欣赏相互同情相互支持之外,还需要理解双方存在的问题。承认差异和问题所在是传播共情的基础。群体间性、民族间性和各种不同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正是共情因素中不可或缺的机质。赛义德提出的“对位阅读”即是解决共情矛盾,涵化文化他者之异的途径。“对位阅读考虑的是多声部维度﹐而不是主导声音”。此外,洞察“理解的前结构”是一种“共情”能力。加达默尔认为:“一切理解必然包含某种前见,它包含着一种先行判断,同时具有肯定和否定价值。”理解和解释过程一定会触及倾听者的灵魂,理解者将传播的情感融入听者的情绪中。如果传播者不理解对方的情感与他所表达情感的关系,那么,他的解释不可能有效地传播话语意义。信息传播的不畅通揭示了文化折扣的原因,“心同此理”的立场是站在他者的位置去交往,去传播。中国对外传播和文化“走出去”,必须重视这种文化间性,唯其如此,文明的互鉴互赏才能做到“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只有这样才可以谈公分母的“共”,才能产生“情”的正向回应。
既然跨文化共情可从中国传统美学角度予以观照,那么,如何将传统审美共情转化为现代媒介共情?审美共情无疑是一种创作或文学审美批评的主客交融的心理过程。它亦是一种共情传播之模式。人将感情投射到物体,或者物体投射情感到人,产生共情的种种形态。这种共情是自我主体在心理内部建立一个“他我”(alter ego)结构来移情地理解他者。这种移情是自我主体通过想象,联想等方式实现的。“外射作用就是把在我的知觉或情感外射到物的身上去,使它们变为在物的。”从身体情感的感知,到文化价值信仰,皆是如此。文艺审美的共情,传播中新闻标题对文学语言的套用,常常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感。辛弃疾写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但觉得青山“妩媚”,而且似乎觉得青山也以词人为“妩媚”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使景与人合二为一。朱光潜通过援引里普斯的移情说参证中国古代的心物交融说。“它是情感的‘表现’,是自我(观赏的自我)与非自我(空间意象)的同一,因此含有‘自我价值’的意识在内。”有鉴于此,共情传播意图在审美者与审美对象之间“由物及我”和“由我及物”的情绪和审美互动,可以经常援引文学暗喻,套用话语模式增强渲染力。传播者作为文化场景的审美者,有必要涵养产生共情的意识,不断提升共情素养,培养跨文化传播的敏感力。“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正是指情感在审美过程中的共情作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场景、不同对象、不同种族,换位思考,提升语言交际能力,理解其深层次文化心理和文化禁忌,放弃本土文化高于异质文化的先见和偏见,适应陌生化文化的偏好等,皆可作为将交际信息转化为共情的手段策略。
四、共情境界与共情能力的涵养
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之间之所以存在相互欣赏,产生共情,皆因为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多重主体性的存在。一方面,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是共情的艺术写照。主体移情于物,意溢于壮美,“有我之境”的主体投射表现比较富有情感色彩,“故物皆着我色彩”。跨文化传播中,主体情感的孕育和溢出,有利于共情的交流和传递。另一方面,“无我之境”的主体情感表现得深曲平静,也是“我执”的一种放弃。“我说”不如“道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虽然花不说话,但传递了人的喜怒哀乐的信息。“在一般的外射作用中物我不必同一,在移情作用中物我必须同一,比如花的凝愁带恨本是我移情过去的,但因为凝神关照,无暇顾及花与我的分别;一般外射作用由我及物,是单方面的,移情作用不但由我及物,也由物及我,是双方面的。我看见花的凝愁带恨,自己也不免陪着愁恨。”万物皆有灵性,放弃“我执”,敞开自我,才能感受他者之情。庄子的坐忘和心斋,是进入此种精神境界的两种法门,也是感知宇宙,与道大通的共情修炼方式。只有放空自我,才能接纳他者。主体和理性的消解,有利于进入万物一体的“无我之境”。
共情是人的本质属性,代入感是人的想象力使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寻找友声和知音,是人和自然的一种天然需求。在跨文化传播中,共情能力高者与天地万物之间存在“不隔”。钱锺书在《论通感》里提及的“红杏枝头春意闹”是一种拟人化的共情。“通感”把听觉、视觉、味觉、触觉沟通起来,这样红杏也可以拟人“闹”春。如果共情理论以主体间性作为支撑的话,山川河流、草木鲜花、鸟兽虫鱼等皆是对话的主体。只有顿悟开窍者,才可以“化蝶”进入此等澄明世界,才可以对话于有灵性的万物。角色代入是进入共情环境的一种涅槃化身的途径。再如,在传统文学中,代言诗是作者化身诗中艺术形象,以第一人称身份、口吻、心理“代入”,模拟他者。相对照,古希腊、古印第安等文化将山河大地皆视为有灵性的生命并赋予其主体性地位,即系一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天地、四时、万物不是通过言说,而是通过“道 成 肉 身”的 显 现,对话于人,施“感”于人。“通”是物之实施于我,“感”是我之受感于物。物我链接,感而遂通。这种共情观既可视为一种超验主义,也可指向一种实际传播行为和情感。主客观的消弭或“万物一体”的观念,并不意味着传播行为的单向度,恰恰相反,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存在着一种实然或虚拟关系。在施拉姆看来,文化传播很难设想喃喃自语,只有哈姆雷特的独白才是单向行为。即使文化娱乐也存在一种契约关系,即传播者对虚拟人物也需要一种共情心。大型文化体育活动中的开幕式场景展示及吉祥物的选择,体现了由物及我的情绪感染和真实场景,以浸入式体验让观众产生喜爱和认同。人们由于人生体验相同而产生代入感。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一时走红,除了自然遗产与人文遗产的和谐搭配外,其形象也体现了非物质文化的人文情怀和科技奥运的现代动感。其传播环境和传播意象在人们心中激起共鸣和愉悦感,正是由于反映了跨文化传播的普遍心理结构。这种深层次心理结构也就是李泽厚所说的“乐感文化”,即以“情本体”为主轴,注重个体的感性生命,关注人际和谐,以儒家文化的“游于艺”“成于乐”及“天人合一”的心理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核心。
共情理论对于中国当代中国形象的重构、跨文化传播的效果等命题的研究来说,意义尤为重大。中国的国际传播除了对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意识形态、阅读习惯、审美价值取向等进行深入了解之外,还应该重视世界文化的共通性。在中国形象的“他塑”与“我塑”之间,兼顾言说自我与理解他者。他者并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并不是纯粹的异己之物,而是完善自我的重要媒介。跨文化传播共情的最高境界,在我看来,乃是能够体验临济宗所说的“以心印心,心心不异”的心法。在跨文化传播和译介中,通过互文暗通的意象、联想意义的传递,可以增强“我”在他者心目中的接受效果,彰显他者言说的特殊文化价值。本内特提出的跨文化对他者文化的否定、抵御、最小化、认同、适应、整合的六要素,包含了价值立场和情感转换的不同阶段,可作为涵化他者的方法。本氏认为,跨文化交际的学习者可以通过预设和建构文化差异,以培养跨文化的敏感性和相关技巧。跨文化交际学习者通过一系列训练,可以从“我族中心主义”转向“我族相对主义”。显而易见,跨文化的训练情境中,伦理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异域的考验或异化伦理策略,相较于文化涵化策略,更能检验其文化包容性和文化共情心态。归化或格义虽然包含着一种文化整合,但也同时意味着文化抵御。无论如何,跨文化传播应该放弃“我执”,换位思考,凸显共情因素。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说明了场与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文化的相交相汇和融通借鉴,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其传播的总体效果依赖对他者的认知与共情。“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在历史上对异国的认知当中,总会有一部分内容流传下来﹐进入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这种积淀下来的因素在知识场中占据一个相应的位置﹐并通过各种关系网、各种相互作用而对一个具体作者施加影响,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部分或全部地接受这种对异国的社会集体想象。”跨文化传播共情失败的典型事实是,对他者文化的曲解和简单化,甚至漫画化和象征化。
结语
随着数字人文时代的到来,多模态、新媒体的出现,传播共情的方式变得日益复杂。OpenAI推出的人工智能ChatGPT,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传播共情关系和共情价值基础。一方面,人们狂热地庆祝它强大的信息编码和解码能力,惊叹其信息传播效果,感叹它的理解能力和生成能力,对其顶礼膜拜。另一方面,信息误导及其伦理问题所产生的风险后果,无不引起人们的忧虑。由于其具有接近人类的智力,“孪生智能”ChatGPT会不会进化成一个新的物种——科技智人(Technological Homo Sapiens) 如此,传播者的主体性和偏见意识会被消解,共情方式和共情对象发生了变化,主体结构反过来也被宰制和臣服或处于互为主体的状态。进而言之,如果能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类人智能方向取得突破,在传播领域实现类人听觉、类人视觉、类人语言和类人思维,“孪生传播者”就可能成为现实。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 Stiegler)提出的身体媒介化即是“代具性”: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人的代具进化,也就是自我实现技术的外在化。特斯拉发布的Optimus综合了人的感知系统、思维系统来实现移动、感知、学习等行为,具身性的人形机器人具有人类类似的感知,其感知和情感会如何呈现?人工智能ChatGPT之后新媒体传播的新方向在哪里?如何打造新的传播意识,媒介传播者如何与机器发生共生共振?从而形成传播的相互赋能,交互共情的“异质同构”?由自由意志组成的大众传播在技术赋能的社会中,能否得到技术他者的默会认同?不仅如此,随着媒介生产者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一个众声喧哗、纷纷扰扰的网络世界让人目不暇接。编码解码的非对称性日益增多,“假新闻”(Misinformation)在没有具身身份显示的情况下,让人莫辨真伪。最近,一系列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教皇弗朗西斯身着时髦的白色河豚外套,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逮捕,马斯克与通用电气公司总裁玛丽·博拉手牵手,原来这些图片是一家名叫Midjourney的平台的杰作。毋庸韪言,AI工具可以产生新的创造力,但同时其所生产的传播媒介,也污染和威胁到信息生态系统。此外,在国际传播中,当用户意识到“信息茧房”背后存在推手时,对某类特定推送的“宣传”信息就会产生抵触和先入为主的偏见。因此,国际传播的符号话语需要培植和嫁接“软销”环境,传递相类似的情感经历和构建目的语话语的叙事方式,来促进数字时代的传播共情。
对于媒介生产者、使用者及社交媒体平台而言,信息推介、情感交流和价值创造同样重要。不仅如此,人工智能时代媒介生产内容与共情因素涉及不同文化的受众,副文本的共情行为如弹幕、评论、交谈,新媒体的交互性、无界性和即时性等因素构成了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从而对情绪信息进行加工以达成同向解读和情感共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人际传播进入公共传播后,共情主体的众声喧哗将成为一种常态。尽管现代新技术、新媒体有调动使用者情感的强大能力,但共情能力和媒介诚信问题还有待评估。主体身体的“义肢化”,远程登录的不在场,数字化构序存在替代了生命负熵,虚拟主持替代了海德格尔的“此在”,共情传播是否还有真情实感?同时,拟真影像的虚拟现实,让受众也感受到“五色令人目盲”,感受到如恍兮惚兮的声光电媒介的场景,体验到身临其境、欲罢不能的感受。此外,人工智能平台的共情能力还依赖智能的内容生成、长期记忆、情感感知和沟通能力。与其说人工智能的“心灵”是对人类心灵结构的模仿和复制,不如说是对其功能性的模仿。完全复制人类心灵,甚至与人实现真正共情,则需要上帝般全知全能的智慧。
无论如何,全球范围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不仅改变了整个媒体行业,还影响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交际传播方式,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影响者文化”(Influencer Culture)。从新媒体到“心媒体”,信息共造彰显的是体认体知的表达,凸显的是其所承载的心灵情感及其所传递的文化价值。无论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心灵将与人工智能共生共荣,共情共识,相互辉映,并与其共舞共蹈。这似乎成了新技术时代媒介传播的宿命。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礼记》文化关键词流变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YJA86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用参考: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