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八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考古学对于“文化”和“传播”的思考》,作者李英华、余西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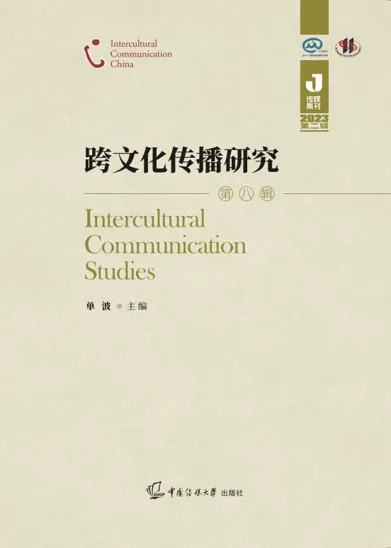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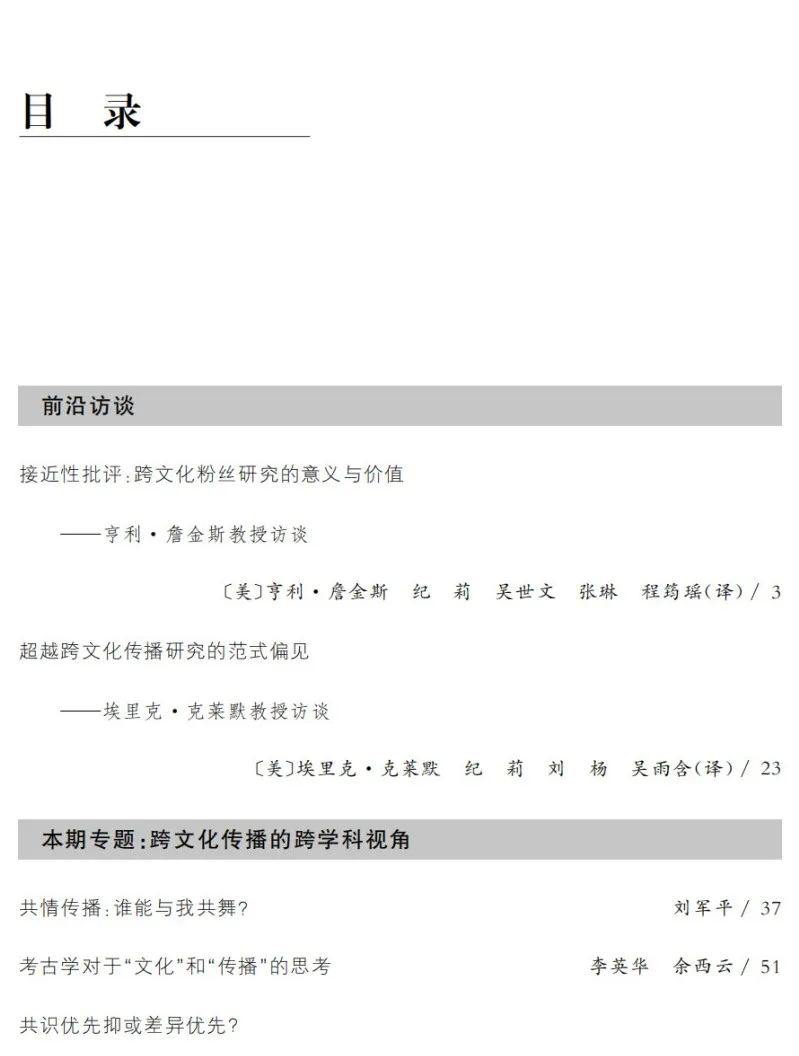

考古学对于“文化”和“传播”的思考
李英华、余西云
摘要:
考古学以地下出土或地上存在的各类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学科的方法阐释和复原古代人类的文化与行为,达到“透物见人”的核心目标。本文从静态的物质遗存出发定义能代表“人们共同体”的“考古学文化”,再来探讨和阐释“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古代人群与文化或社会的动态关系是考古学尤其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学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路径。本文对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和“传播”等重要概念进行了梳理,以期从宏观角度介绍考古学对于文化传播的探索与思考,促进跨学科的交流互鉴。
关键词:
考古学;考古学文化;传播;交流;互动
“透物见人”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目标,地下出土或地上存在的古代的各类实物或曰物质遗存是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所以考古学的几乎所有研究方法的提出和进展都是围绕如何从物质遗存上升到对背后人群或个体的认识来进行的。人作为具有文化属性的动物,其文化形态与内涵极其复杂多样,所以“文化”构成了考古学中最经典也是运用最多的一个概念。如果说物质遗存以及所定义的文化均还停留在静态层面,那么,对它们反映的背后人群或个人的相互关系的探讨和解释就是动态层面的复原或重建了,与此相关的概念包括传播、互动、迁徙、扩散、交流等,其中“传播”是引入时间较长、运用较多的一个概念。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概念入手,从宏观角度介绍考古学对于“文化”“传播”的探索与思考,期待能与当今跨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研究进行跨学科的交流互鉴。
一、考古学中的“文化”
“文化”这个来自民族学的概念于20世纪初期被引入史前考古学,“考古学文化”概念最先被德国考古学家科辛纳(Gustaf Kossinna)用来整理考古材料,他在《日耳曼民族的缘起》中就将考古学文化的传统与民族传统关联和对应,并试图通过考古学文化的整理来探讨德意志民族的起源,因而他的研究具有种族优越论的色彩。随后,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的《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真正确立“考古学文化”并用它重建了欧洲史前历史的框架。柴尔德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整体观和唯物史观,摒弃了科辛纳的种族主义倾向,提出“一群特殊的特征品……绝大多数具有物质文化的特点,但也有很多精神方面的特点,它们在某一时代的某一相连地带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群相联的特征品便是考古学家所说的一个文化”,使其成为研究史前人群遗存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工具。
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定义和区分的基础是物质遗存的相似性,逻辑上存在两个预设。一是物质遗存的特征代表了人们头脑中不同的思想、社会组织、经济方式或不同的行为习惯,二是运用这些物质遗存特征及组合(即标准)就能定义文化,或代表“人们共同体”。更确切一点说,它代表了考古遗存中可见的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区域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物质遗存共同体,可以划分为聚落形态、墓葬形制、生产工具和武器、生活用具以及装饰品等5种成分,所以某一具体的考古学文化就是时间和空间构成的特定情境中的全部物质遗存的总和,其本质就是物化形式的文化内容。在多个层次的物化形式的文化内涵中,那些标志性的带有鲜明时空特色印记的物质遗存和(或)组合通常被定义为“文化因素”,也就是可以拆解的考古学文化的要素构成,进而被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进行比较,以厘清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和文化生成发展的本质性特征。与考古学文化基于物质遗存的建构思路不同,这是基于考古学文化深入拆解的一种解构方法,与地层学、类型学一样都是在考古学文化研究中要运用的基本方法之一。
以考古学文化这一研究工具为基础,结合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以及碳十四测年数据,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认为中国早期文化可以分成面向内陆的文化和面向海洋的文化两大板块,下面至少可以分为6个大区,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大区下还可划分考古学文化及其地方类型。以此为基础,苏秉琦先生进一步提出“满天星斗说”、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来解释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演化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学界对这几大区系内部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进一步细化和深入,几乎在所有地区都发现了丰富的考古学文化。时至今日,学界已经可以制作以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北方地区,长江中游、下游,华南地区,西南地区为横轴,以绝对年代为纵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考古文化年代简表。由此,中国确立了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时空框架,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谱系脉络、书写中国历史的最早篇章,奠定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所以,考古学文化概念及相应的研究范式之于史前考古的基础地位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同时,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要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历史文献密切结合也构成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当然,对于“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界多年来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和争论,比如,考古学文化的理论预设是否成立,考古学文化本身是否具有客观性,考古学文化与族群是否存在对应的可能性,等等。不过,尽管不同学者理解的考古学中的“文化”可能不同,而且20世纪初期以来随着时间发展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在文化观方面出现了分化,但是无论如何,“考古学文化”到目前为止都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它同时包含了时空、组合等要素,其提出的意义在于把遗存的研究由年代特征扩大到了传统、地域的特征,摆脱了19世纪基于地质学的史前史序列编排范式的束缚,使史前考古学研究完全可以从遗存本身出发,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新角度来研究史前史,最终能建立起各地区的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所以它为探讨史前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单位,是通过考古学重建史前史的前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说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造诣极深、无可匹敌”,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提出“给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对世界史前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考古学中的“传播”
如果说考古学文化实现了从物质遗存出发对“人们共同体”的静态建构,那么“传播”可能是考古学中广泛使用以对考古遗存背后的内涵特征进行动态阐释的概念之一。“文化传播”借用自文化人类学,在考古学中通常被定义为“一种发明被社会接受的过程,即新的意识或新的文化特征从一个人或一群人向其他人或群体的扩散”,以此为基础对考古学遗存相似性和差异性背后的原因和机制进行动态阐释的理论就是我们熟知的“文化传播论”。
文化传播论是起源于20世纪初欧洲的一种文化人类学理论,内核是对19世纪末流行的“文化进化论”(尤其是单线直线进化论)的质疑和反对,认为人类缺乏创造性,社会的独立发明是十分罕见的,所以,相似的文化不是独立发明发展的结果,而是文化中的模式从起源地向外传播的结果,换句话说,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借用”(或“采借”)总是多于独立发明。在这样的逻辑下,传播论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三种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理论主张,即英国的极端传播论派、德奥传播论派和美国传播论派。德奥传播论派又被称为“文化圈派”,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格拉布纳(F. Gräbner)和奥地利的施密特(W. Schmidt)等。他们都是人类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学生。该派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就像涟漪,从原点慢慢扩散出去,不论地理远近,只要文化特质类似,就是文化传播或采借的结果,而独立发明要在寻找不到传播的迹象后才能确定。要寻找文化传播的迹象,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考察。极端传播论派以英国的艾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为代表,又称泛传播论派、太阳石器学派或埃及起源论。该派认为人类文明如此复杂,是不可能被多次独立发明的,只有古代埃及才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美国传播论派以威斯勒(Clark David Wissler)和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eber)为代表。威斯勒根据大平原部落相似的文化特质划分出了不同的文化区,认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只能用传播来解释;克罗伯以威斯勒的工作为基础,开创了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适应关系的研究先河。随后,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时空模式”(Age and Area Model);为了研究处于持续变迁中的人群或因历史上的文化接触而导致多元渊源的文化场境,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明确定义了“涵化”这个概念,“涵化”也被引入考古学关于史前人类文化互动的研究中。
学术界很早就采用传播论解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安特生(J. Andersson)基于他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活动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产生了比较大的学术影响。1921年,北洋政府的外籍专家瑞典人安特生主持发掘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村、不召寨等遗址,标志着以田野考古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1923年,安特生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用传播论的观点解释仰韶文化,提出彩陶西来说:“仰韶陶器中,尚有一部分或与西方文化具有关系者。近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同,远或与欧洲相关。施彩色而磨光之陶器,即其要证。与此相似之陶器,欧洲新石器时代或其末期亦有之。如意大利西西利岛之启龙尼亚,东欧之格雷西亚,及俄国西南之脱里波留,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地方,皆曾发见。各处之器,各有特点。然与河南仰韶古器之器工花纹,皆有极似之点,夫花纹样式,固未必不能独立创作,彼此不相连属。然以河南与安诺之器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两地艺术,彼此流传,未可知也。诚知河南距安诺道里极远,然两地之间实不乏交通孔道。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
为了证明彩陶西来的观点,安特生于1923—1924年间在甘肃和青海东北部进行了调查与试掘,1925年发表《甘肃考古记》,介绍其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将甘肃远古时代(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初期)分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这六期,即所谓“六期说”。安特生在甘肃发现了丰富的彩陶文物:“河南之彩色陶器,虽与甘肃所出者,有密切之联系,然仍自各成一族。”虽然无法准确判断是甘肃的彩陶早还是河南的彩陶早,他还是提出“彩色陶器之故乡,乃近东诸部,为一般学者所承认者也。著者深觉精美陶器之有彩纹者,其制作之术,首抵甘肃,次及河南。此说固属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基于传播论的猜测。此后,中国学术界用新的考古发现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复的回应和批评。
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西方学术界用传播论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与相似性的解释,理解和解读中国人种、文化与文明的起源。瓦西里耶夫的论点并没有坚实的材料作为支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想象和推论得出的,有一些推论很快为考古新发现所否定。
当然,无论文化传播论还是文化进化论,都是考古学界对人类文化社会,尤其是史前人类文化与社会,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进行动态阐释的理论选择,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都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新范式的传入,学界对这两个理论的认识也渐趋客观中和。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对这两个理论做更深入的论述,而是对考古学常常涉及的“传播模式”以及几个与“传播”相关但不同的概念做简要介绍。
考古学由于不可能发现古人生活生产留下的所有遗存,所以很难原样重建古代文化传播的细节和过程,相对可行的是借用多个领域(包括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的观察,对古代文化传播发生的方式和机制进行概括,提出一些可供考古学研究参考的阐释模式。
当然,除了传播以外,考古学对人类物质遗存所反映的人群、文化与社会变化进行动态阐释的概念还包括变迁、发明、迁移、扩散、同化、涵化、交流、互动等,它们都是对文化变化的原因和方式的一种揭示和表达,各有其内涵和外延,相互之间也有重叠或交叉,考古学家使用它们的情境也各有不同,但是它们都体现了对古代人群的文化和社会的动态关系进行高层面阐释和模式化归纳的追求。下文对它们也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和概括,以便与“传播”概念联系起来比较和理解。
“变迁”是指万事万物变化转移的过程,文化变迁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开始的从未停顿的过程。相对而言,变迁这个概念比较中性,与变化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文化内部的变化可能会导致考古学可见的文化变迁,也可能不会在考古的物质遗存中留下痕迹。从其过程和机制来看,变迁一般分为两种,即无意识的变迁和有意识的变迁。无意识的变迁多为缓慢的过程,开始于一个偶然的甚至是细小的事件,以至于任何当事人都无法预测以后连锁反应带来的社会后果。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时就没想到它将给整个大陆旧文明带来毁灭,同时导致新文明的诞生。而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无意识的变迁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化经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有意识的变迁是由个人(社会上层人士)或某一社会阶层所发动,按照计划对社会的个别文化要素或局部制度进行的改革、变法或维新。历史上有名的有意识的变迁如公元前4世纪末我国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当代的实例如文化人类学上有名的“康奈尔秘鲁计划”,即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艾伦·霍姆伯格(Allan R. Holmberg)为了让受剥削的秘鲁印第安人农奴居住的“维柯斯”农场独立解放而推行的改革,这个改革因为以革命的手段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最后获得了成功。
“发明”意味着新意识的诞生,即认识到了先前一无所知的东西,并对新获得的知识予以运用,创造出过去不存在的事物。从本质上讲,这个概念排除了人们从外获得的新意识,因而不是传播的结果。人类历史上既有无意识的发明,也有有意识的发明。前者如史前的石器装柄、陶器烧制等,后者如结核病防治方法、登月计划、纺织机生产、家用汽车制造等。人类社会的重大变迁一般不是由单一发明引起的,而是由许多小发明积累而成的产物。
“迁移”一般是指人群的移动,旧石器考古和古人类研究中常用“迁徙”表述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人口的大规模移动。迁移往往被列为传播的一种,它与传播的区别是,迁移通过人口本身的大规模移动而发生,但传播往往包括意识的扩散,换句话说,人口的迁移可以产生文化传播,也可以不产生文化传播,而传播可以经由人口迁移实现,也可以不经由人口迁移实现,所以(人口)迁移与(意识的)传播是互相独立的概念,考古学阐释中也需要对其作出区分。
“扩散”指物质、意识、文化特征甚至人群从源生地向外扩展、分散的过程。它可以是自发的,也可能是自觉的。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领域也常用此概念,比如现代人的起源与扩散。扩散与传播有区别,扩散的外延比传播更大,也就是说,传播是扩散的一种,但扩散不一定导致传播。
“同化”指一个群体完全接纳一种外来文化的过程。如果考虑两个文化的地位及关系,则它也指“改变一个被征服或被吞并文化的诸方面,使其变成适应统治文化形式的状态”,在该过程中,“统治文化倾向于强迫别的文化采用自己文化的某些特征,在表面上看起来获得了适应”。“同化”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学研究移民问题时常用的概念,一度在研究中形成了比较突出的同化主义倾向,遭到现代人类学家反对,因而成为“涵化”概念提出和确立的背景。
“涵化”指“人类种族或部落因文化或艺术接触而变得相近似”,也可以是“一个人群对另一个人群的文化输入”或“人群对外来文化的采用和同化”。如果考虑两个文化的地位及关系,学界实际上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以北美人类学界为主,认为是“一种文化的某些方面被带入另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以相对平等互惠的方式,经调整使之适合该文化”的过程;一种是当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经济文化上都比较强大的社会接触时,由于不平等关系,弱小社会经常要被迫接受较强大社会的很多文化要素而对其文化要进行广泛的假借,这个过程就是“涵化”。当然,这两种情况也可以被认为是涵化的两种形式,即文化因素的自由“借入”和改变及强制变化,所以,涵化与同化和文化变迁之间既存在关联,也有不同,比较复杂。
“交流”和“互动”也是考古学在阐释人群文化动态关系时普遍使用的两个概念,相对中性,分别指“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给对方、相互受益”和“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考古学文化互动或文化交流研究是“通过特定的人们共同体同其他人们共同体相互交往中遗留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其交往的原貌,揭示其交往的内涵、形式、途径和实质,恢复其交往的历史”,所以更多的是坚持实证主义思想,“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而较少停留于对上述概念的纯理论辨析上。
三、讨论和思考
考古学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利用所发现的一切物质遗存(含宏观和微观遗存)阐释和复原古代人类的文化和行为,最关键的是实现“透物见人”的升华,所以“考古学文化”及以此为基础开展的人群文化互动关系研究和阐释非常重要。进入21世纪以来,考古学与多个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交叉,使考古学从遗存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大幅增强,而且在构建古代人类文化框架的基础上,对古代人类行为的探索更加细致深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古DNA研究在提取和测序分析方法上的突破,为数十万年至几千几百年前的古代人类的起源、迁徙、扩散、传播、互动、交流等动态关系的阐释带来了新的认识。时至今日,结合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古DNA和现代人DNA进行的研究表明,考古学上所见的古代人类历史的动态图景变得异常复杂,既要区分人群,也要区分个体,既要区分文化或意识,也要区分技术,既要鉴别传播,也要考虑进化,每个层面运用的证据不同,阐释结果也有区别,甚至针锋相对。因此,作为古代人类研究的共业,考古学十分需要在多个学科、多重证据之间进行更有效的交叉整合,明确专长,凝练目标,以便更好地“透物见人”。本文仅为笔者的粗浅思考,还有全面深入探讨的空间,希望能与相关学科的研究进行交流互鉴。
引用参考:
李英华,余西云.考古学对于“文化”和“传播”的思考[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3,(02):51-62.
作者简介:
李英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教授,电子邮箱:lyhfrance2005@yahoo.fr;
余西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教授,电子邮箱:yuxiyun@aliy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