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八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基于情景的对话:邀请修辞与跨文化沟通的修辞实践》,作者刘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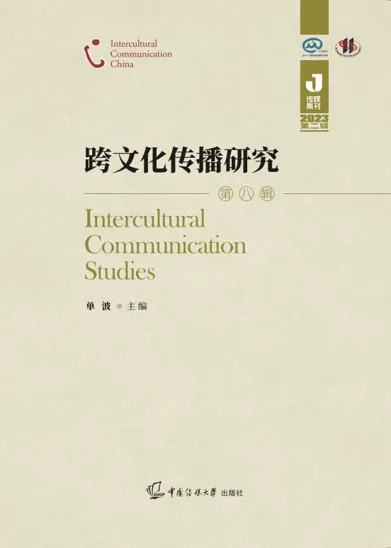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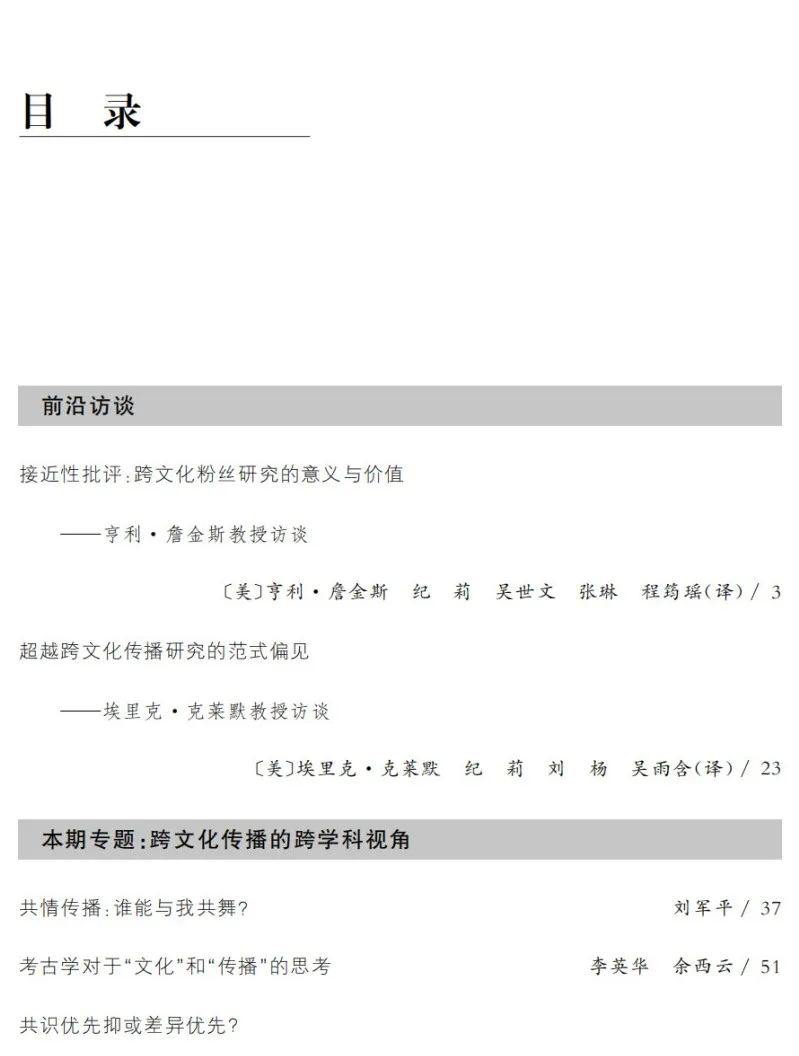

基于情景的对话:邀请修辞与跨文化沟通的修辞实践
刘涛
摘要:
作为当前备受关注的一种修辞形式,邀请修辞(invitational rhetoric) 超越了古典修辞学的“劝说”模式,强调将受众“邀请”到修辞者的世界中,以促进彼此的共同理解,而实现“邀请”的常见方法是创设一个自由的、平等的沟通情景。邀请修辞将情景推向了认识活动的中心位置,其超越了古典修辞学所强调的情景工具论,也超越了新修辞学所强调的情景反映论,而倡导一种全新的情景认识观念——情景信息论或情景媒介论。面对跨文化沟通中普遍存在的偏见与冲突问题,邀请修辞所强调的“以情景为方法”的理论路径无疑从修辞学视角拓展了跨文化沟通的认识视角和实践模式。而要实现情景意义上的跨文化“邀请”,客观上需要重构情景的生成语言,一是从论证转向事实,二是从论辩转向行动。在数字媒介环境下,数字叙事极大地释放了“邀请”的想象力,跨文化沟通亟须重视并拓展数字情景生成的修辞之道。
关键词
情景;邀请修辞;跨文化沟通;古典修辞学;新修辞学
一、邀请修辞与跨文化沟通之可能
跨文化沟通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寻找那些“居间”的资源、符号、语言形式及理解模式,以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对话。而“居间”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进入文化认知与传播的理解框架,本质上揭示的是媒介意义上的连接、中介及生成功能——这三种功能实际上打开了“居间”的三种理解方式,并形成了跨文化沟通的三副面孔。其一,连接意为一种接合形式,即一种文化迈向另一种文化,并“捆绑”在某一结构性的文化系统之中;其二,中介意为一种配置方式,即借助中介化的技术装置或驱动体系,文化得以“显现”,并与其他文化建立了调停关系;其三,生成意为一种依存结构,即文化之间存在某种隐性的作用和张力,其特点便是形成了协同共生、共同进化的存在状态。实际上,在跨文化沟通实践中,“居间”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方式,也回应了跨文化得以实现的沟通“语言”。由于文化之“跨”并非文化的“异”与“同”的问题,而是承认人类生活模式多样性基础上的跨的“文化”,因此,跨文化沟通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发现或重识那些“居间”的资源与话语,以建立文化之间的某种接合关系、调停关系或生成关系?
由于文化之间的“相遇”必然指向一定的现实情景,加之文本意义生成也依赖于既定的语义情景,因此,考察文化之“跨”的“居间”功能,不能忽视情景本身的配置结构及其内部语法。情景既是主体活动的发生场所,又是传播行为的组织原则,亦是文本语义的阐释规则。必须承认,对文化“交集”的识别或建构,依赖于“中间地带”本身的阐释规则,而情景则在符号学维度上回答了意义阐释的元语言(meta-language) 问题。正是在情景所构筑的锚定系统中,“居间”层面上的意义通约成为可能。因此,从情景维度出发,思考“居间”功能是实现方式,是本文重点思考的一个研究论题。
跨文化传播预设了文化有别,而文化之“别”同样存在语境意义上的“情景之维”。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Hall) 曾将文化 区分为“ 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 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 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即文化的传播与理解高度依赖于现实情景,因此,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总会面临“中国人令人费解,城府很深,不可理喻”的指责。按照霍尔的观点,如果说低语境文化可以相对容易地在语言逻辑层面进行沟通与理解,高语境文化则需要回到一个更大的情景结构中加以识别和认识,“大多数信息或存在于物质环境中,或内化在人的身上;需要经过编码的、显性的、传输出来的信息却非常之小”。正因为高语境文化受制于复杂的现实规则限定和影响,中国人的传播实践呈现出丰富的超语言逻辑。必须承认,在具体的文化沟通实践中,这里的“语境”本质上指向的是一个情景问题。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只有回到语境与情景维度,才能真正识别文化之“跨”所面临的阻力和障碍,进而在情景维度上回应跨文化沟通所面临的情景问题。
情景问题是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命题,本文则主要从修辞学的视角加以探讨,尝试拓展跨文化沟通中情景研究的修辞学想象力。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其语言六功能模型中,将“语境”(context)视为“指称性”(refrential)功能,意在强调传播结构中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共享之“物”对于理解的重要意义。语言之所以能够建立一种指称结构,是因为存在语境维度的意义锚定结构。从修辞学的视角来看,语境意义上的指称性功能,本质上体现为一个修辞情景命题,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修辞学视角出发,审视跨文化沟通中的情景问题,从而在修辞维度上寻求文化之间的对话之可能。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当前学界备受关注的一种修辞理念——邀请修辞(invitational rhetoric)切入,探讨跨文化沟通中的情景问题及其生成原因。
邀请修辞是索尼娅·K.福斯(Sonja K. Foss)和辛迪·L.格里芬(Cindy L. Griffin)提出并倡导的一种修辞理论。该理论延续了女性主义修辞的传统,认为古典修辞学是一种父权制的修辞方式——修辞者的自我价值(self-worth)实现,源于通过施加权力来影响他人态度,其目的是通过改变他人来建立控制关系。福斯在女性主义修辞传统的根基上,建造起邀请修辞的大厦,以创造一种平等的交往关系,从而向弥漫着霸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人类交往体系发起挑战。相较于古典修辞学的劝说观,邀请修辞并非试图通过说服来控制他人,而是尝试建立一种基于平等(equality)、内在价值(immanent value)和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 原则的修辞形式。福斯与格里芬指出,邀请修辞是“对理解的邀请,是创造一种植根于平等、内在价值和自我决定的关系的手段。邀请修辞意在对受众进行邀请,让他们进入修辞者的世界,并像修辞者那样看待世界”。
多年来,福斯和格里芬一直深耕这一研究领域,并于2020年将学界的相关文献整理成著作《邀请式理解:邀请修辞研究指南》出版。按照福斯的说法,邀请性的互动交流具有七大特征:其一,理解是交际的目的;其二,参与者带着开放的态度倾听他人的不同见解;其三,参与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其四,双方寻求“权力共享”(power-with)而非“权力控制”(power-over);其五,任何改变都是自主选择的结果;其六,参与者带着“愿意妥协”的心态参与互动;其七,彼此之间接受并欣赏差异性。当前,作为一种修辞理念和实践,邀请修辞引发了修辞学界的普遍关注,其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文学艺术、健康医疗、跨文化传播等领域。例如,杰森·A.谢里尔(Jason A. Sharier)研究发现,邀请修辞有助于增强宗教领域的跨文化沟通效果,因为其促使修辞者以更具同情心(sympathetic)和同理心(empathetic)的方式来讨论宗教主题。基于邀请修辞的理念和视角,福斯进一步提出了邀请传播(invitation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命题。不难发现,邀请传播可谓是邀请修辞的一种实践形式。如果说詹姆斯·C.麦克罗斯基(James C. McCroskey)提出的修辞传播(rhetorical communication)旨在打造一种以修辞者为中心的可控的、劝说的交流体系,建立在邀请修辞基础上的邀请传播则致力于创设一种邀请式的修辞情景,以达到对话发生的“邀请”功能。
如何实现邀请修辞的“邀请”功能?福斯与格里芬特别强调要创造外部条件,允许他人在尊重和平等的氛围中提出自己的观点。相应地,安全(safety)、价值(value)和自由(freedom)构成了情景生成的基本条件,即“修辞者能够认识到他们的目的并非说服他人,而只是创造一种环境,以促进理解;对于他人观点给予足够的肯定和尊重,并促进平等关系的建立”。概括而言,邀请修辞旨在倡导一种积极的对话,而对话发生的关键在于创设一种自由的沟通情景。而在邀请修辞中,如何邀请以及邀请何为,客观上需要“用情景说话”——只有当情景本身包含或呈现了真实的、客观的、多元的信息线索时,“邀请”才能真正在情景维度上“落地”,并上升为一种消除偏见、弥合冲突的修辞实践。2009年发生在云南静宁县的“躲猫猫事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24岁的青年李乔明在看守所“离奇”死亡,警方给出的解释为他在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因头部受伤而死。面对网友的集体质疑,云南省委宣传部采取的方法是邀请网友参与调查。尽管邀请社会人士参与重大敏感议题调查的举措,能够体现官方尝试与公众对话的诚意,然而,由于网友不具有专业侦查能力,加之李乔明已经死亡,现场可以获取的线索和信息非常有限,因此“邀请”行为更像是一场平息舆论的展演。究其根源,是因为这里的“邀请”行为并未真正还原对话发生的真实情景,亦未提供调查推进的现实线索,最终,这场声势浩大的网友调查在喧嚣之中无疾而终。
在跨文化沟通实践中,文化既是冲突发生的潜在动因,也是化解冲突的解释语言,而后者则有赖于邀请式的情景创设。在郑晓龙导演的电影《刮痧》中,美籍华人许大同的父亲采用中国传统的刮痧疗法为孙子治病,却被美国儿童福利局指控为虐待儿童,因此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官司。孩子背上由于刮痧而留下的一道道“伤痕”,无疑成为两种文化竞相解释的符号——中国文化将其视为一种普通的治疗手段,而美国文化则视其为一种虐待儿童的罪行。显然,这场冲突是在文化维度上展开的,其根源在于对刮痧“伤痕”的元语言争夺,两种文化都尝试赋予自身话语一定的合法性,但却因为话语深层的认知框架无法调和,而难以找到可协商、可通约的对话“语言”。如果进一步审视文化冲突的发生原因,则不能不提及沟通系统中的情景因素——冲突大多发生在一元声音主导的场景之中,这种特殊的情景设计,使得彼此难以“看见”对方,和解之路异常艰难。实际上,跨文化沟通中的冲突性场景,本质上体现为单一文化主导的封闭空间,这里没有通往外界的“出口”,也缺少可以实现对话的连接“媒介”,彼此都深陷于被偏见所包裹的“牢笼”中,无力地论辩。由于缺少沟通与协商的公共性基础,一系列独白式的生活场景铺设了故事发生的基本情景,而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情景本身难以实现两种文化的调和。如果情景本身的规则体系及其配置逻辑并非基于对话的目的加以设定,那跨文化沟通便失去了对话得以发生的情景基础。而最终,两种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和解,并非基于直接碰撞之后的臣服,亦非建立在某种论辩体系之上的说服,而是因为创设了一个邀请式的而非劝说式的交往情景——西方文化主动进入中医文化,在相互“看见”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发现了一种理解“伤痕”的通约语言。
二、情景何以发生作用:从古典修辞学到新修辞学
当邀请修辞赋予了情景极为重要的实践功能时,我们有必要回到修辞学的知识脉络,进一步探讨修辞与情景之间的内在关系。唯有厘清情景在修辞中的话语“位置”,才能真正认识修辞在情景维度上的“展开”方式,从而把握跨文化沟通中“邀请”实现的修辞情景问题。实际上,在修辞学的历史河流中,从古典修辞学到新修辞学,修辞观念的每一次“靠岸”,情景问题都从未离场——只不过在不同的修辞观念中,情景的意义和功能存在一定差异。基于此,本文重返修辞学的知识史,揭示情景之于修辞的认识内涵,并在此基础上以邀请修辞为理论话语,进一步探讨跨文化沟通中“邀请”得以实现的情景生成方式及其修辞语言。
(一)古典修辞学:作为修辞手段的情景
古典修辞学诞生于具体的社会场景,如公共演讲、法庭抗辩、道德教育等——情景既是修辞发生的实践场所,亦是修辞知识的生成条件,修辞的语言与情景的语言深刻地嵌套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情景的修辞知识。简言之,修辞发生在情景之中,而情景本身的系统构成及其潜藏的矛盾与问题,不仅决定了修辞的出场方式,也决定了修辞的问题意识。相应地,古典修辞学所关注的修辞术,本质上是对既定社会议题的发生情景及其功能和使命的一种策略性回应,即既定的社会议题铺设了相应的社会情景,也设定了相应的修辞目的,而修辞知识恰恰是在情景自身的属性和语言基础上形成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公共演讲时,将其细分为三种不同的演说类型——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和典礼演说,认为三者不仅对应于不同的实践场景,还指向不同的情景问题——“政治演说用于劝说和劝阻。诉讼演说用于控告或答辩。典礼演说用于称赞或谴责。”同时,由于情景属性存在差异,三种修辞实践分别预设了不同的修辞功能,并且在情景的“语言”上体现出相应的时间“偏向”——政治演说主要面向未来,诉讼演说主要面向过去,典礼演说主要回应当下。在不同的修辞情景中,修辞的命题及其情景“语言”分别体现为“确实的证明”“或然的事情”以及“或然的证明”。不难发现,古典修辞学的知识体系,主体上体现为一种基于情景的知识——修辞发生在社会公共空间,也存在于既定的社会情景,其目的是“以修辞的方式”回应具体情境中的问题。
必须承认,古典修辞学所关注的情景,并不局限于社会维度的议题情景,还深入文本生产维度,关注意义生产维度的语义情景。纵观古希腊修辞学提出的五大经典命题(修辞“五艺”)——发明(invention)、谋篇(disposition)、文体(elocution)、记忆 (memory)和发表(delivery),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修辞实践中的情景问题。具体而言,“发明”所关注的话题生产和争议宣认,实际上意味着重置意义感知的认知框架,其中必然包含了对某种情景关系的重构与再造;“谋篇”所讨论的语义系统问题,旨在构造一种暗合特定情景规则的语篇结构,其关注的意义系统,依然是沿着语境意义上的情景内涵展开的;“文体”所强调的语言风格问题,不过是对既定情境中受众需求及认知特点的一种回应,其潜在假设是:唯有文本的语言风格符合传播场景的内在要求,才能产生更有效的劝说效果;“记忆”所思考的记忆方法问题,越来越多地转向了一种基于情景的记忆策略,即通过复活信息的情景结构和关系,以提高演说者的记忆能力;“发表”所对应的传播方式问题,早已超越了口语传播时代的口头叙述问题,延伸到媒介传播的讨论维度,而进入电子媒介时代,传播功能的实现逐渐转向了对情景的调适、重组与改变,因此古典修辞学意义上的“发表”不能忽视传播结构中的情景要素。概括而言,古典修辞学推崇的发明、谋篇、文体、记忆和发表问题,都存在一个基础性的情景认知向度。
实际上,古典修辞学视野中的情景,无论是社会维度的议题情景,还是文本维度的语义情景,更多的是将情景置于修辞对象或修辞策略的认识维度,视情景为一种生产性的修辞要素——通过对情景的策略性构造与配置,达到某种劝服性的修辞目的。不同于邀请修辞所关注的自由的、平等的、存在性的情景,古典修辞学主要在“修辞术”层面讨论情景——情景并非一种自反性的存在语境,而是进入修辞的工具、手段、策略维度,它因劝说而生,并服务于劝说的目的和使命。情景所打开的语境结构,包裹着主体的意图,充斥着教化的欲望,流淌着劝说的基因,潜藏着无声的暴力,而一种隐性的、匿名的话语和权力恰恰是在修辞笼罩的情境中被悄无声息地生产出来。由此可见,情景问题进入修辞视野的原因,或是作为有待解决的“问题”出场,或是作为修辞发生的“场景”出场,抑或作为文本生产的存在“条件”出场,其共同特点是将情景推向了修辞认知的“策略”维度,即通过将情景纳入修辞的考察视野,形成更有针对性的修辞术。
(二)新修辞学:作为修辞发生条件的情景
如果说古典修辞学主要是在工具、手段、策略维度思考情景问题,新修辞学则将情景视为修辞行为的发生基础,认为修辞的本质不过是对既定情景的适当反应,由此视情景为一种认识话语,代表性的理论话语为劳埃德·比彻尔(Lloyd Bitzer)的修辞情景(rhetorical situation)理论。比彻尔将“情景”和“语言”视为修辞的两大基本要素,前者类似于“问题”或“疑问”,而后者则是对问题或疑问的直接“回应”或“回答”,由此赋予了情景极为重要的修辞认识潜力。例如,在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描述的特洛布列恩德岛上,渔民捕鱼的“情景”决定了语言的内容和形式,“收网”“放手”“起网”等语言形式之所以被构造出来并进入日常生活领域,与“捕鱼成功”这一任务密切相关。如果抽离“捕鱼”这一任务情景,这些语言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修辞行为及其意义实践,不过是既定情景规约下的符号性反应与表达。
情景问题之所以上升到新修辞学的关键位置,是因为修辞行为存在普遍的情景生成基础——修辞因情景获得意义,并在情境中成为修辞。相对于古典修辞学的劝说体系,新修辞学沿着三个维度重构了修辞的观念,而重构的思路和方法则是“转向情景”。第一,新修辞学超越了古典修辞学以语言“使用者”为中心的修辞体系,延伸到语言“接受者”一端,开始关注人类交往结构中的认同问题。新修辞学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 (Kenneth Burke)将“同一”(identification)问题视为修辞发生的基础,认为修辞的真正目的是促进“共同理解”。而“共同理解”的实现方式则指向情景维度的修辞实践,即依照情景的内在规定性组织修辞行为,以实现情境中的修辞认同。第二,新修辞学超越了古典修辞学的文本语义考察范畴,将修辞的内涵延伸到人类的生存环境,由此关注一种普遍的修辞动机问题。按照新修辞学的观点,人类的生存环境存在一个基础性的修辞认知维度。而环境本质上也是一个情景维度的概念,情景和修辞之间便存在一种相互生成的结构——修辞铺设或设定了情景的语言和规则,而情景也限定了修辞的出场方式和发挥空间。例如,伯克的戏剧五要素模型——由行动(act)、行动者(agent)、手段(agency)、场景(scene)和目的(purpose)共同构成的一个关联体,讨论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通过要素之间的搭配组合来完成修辞情景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解释情境中的修辞动机。第三,新修辞学超越了古典修辞学的语言框架,将目光转向了人类符号系统中的象征行动(symbolic action)范畴,这使得图像、音乐、雕塑、舞蹈、建筑等一切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形式都被纳入修辞学的分析范畴,从而摆脱了修辞学长期以来的“语言依赖”问题,最终转向对多元符号形式的修辞关注。当非语言符号成为一种修辞对象时,新修辞学所关注的情景问题,便超越了文本意义上的语境(context)认识框架,并且延伸到情景本身的符号系统,这意味着修辞情景研究需要关注情境中一切携带象征功能的符号构件——作为情景构成的要素与内容,其中的图像形式、空间构造等非语言符号,既是修辞关注的对象,亦是修辞作用的后果。
概括而言,无论是古典修辞学,抑或新修辞学,都将情景问题推到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论位置。如果说古典修辞学所关注的情景更多地意味着议题、发生场景、实践领域等概念内涵,其修辞内涵可以概括为“情景中的修辞”,新修辞学则将情景本身视为一个修辞对象,认为修辞行为不过是对既定情景的符号性反应,因此在情景维度上重构了修辞的观念和内涵,其对应的修辞内涵则为“情景的修辞”。
三、文化“ 交集”的实现:来自情景的“ 邀请”
不同于古典修辞学在工具论上思考情景问题,也有别于新修辞学将情景问题上升为一种认识话语,邀请修辞则将情景视为修辞发生的认识内容,即修辞的理念是邀请,修辞的目的是建立基于情景的理解,修辞的方法是创设一个自由的、自在的、自然的情景。情景不仅意味着修辞的场所,而且体现为修辞发生的直接认识对象。正因为情景超越了背景、场所、地点的意义维度,而上升为认识的直接内容,因此可以提炼出邀请修辞的情景观——情景即信息。在邀请修辞的符号系统中,所谓的信息,并非镶嵌在情景之上或隐匿于情景之中的其他对象,而是情景本身。相应地,邀请修辞极力倡导的情景创设,并非构造一个信息得以存在的外部环境,亦非重建一个信息得以阐释的规则体系,而是搭建一个联通彼此的沟通情景,其特点便是将那些预先设定的立场、观点、主体意图都悬置起来,将纯粹的、自然的情景本身推向认识的中心位置。
在跨文化沟通系统中,尽管情景创设必然伴随着人为建构的过程与痕迹,但建构的方向与语言并非封闭的、论辩的,而是以承认多元为价值基础,积极向世界敞开,邀请对方进入情景之中——我的情景,亦是你的情景。保罗·哈吉斯(Paul Haggis)在电影《撞车》(Crash)的开场设置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旁白:“在洛杉矶这座城市,人们总是躲在冰冷的建筑后面,这里没有心灵的触摸,相反,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很可能就是剧烈的碰撞。”影片开始时的撞车场景,更像是一个微妙的隐喻,预示着文化之间猝不及防的张力和冲突。看似平静的交往情境中,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种族主义阴影,偏见、歧视、刻板印象铺设了日常交往情景的底层语言。影片中的这一情节令人深思:一名非裔演员在表达“别那样讲”时,使用了“Don ’t talk to me about that”这一表述,这在非裔导演看来并无不妥,然而,剧组中的白人却对此产生异议,认为非裔人群的“正确表述”应该为“Don ’t talk about that”——前者相对文雅,一般为白人的“专属用语”,而后者相对粗鄙,符合人们对非裔人群的刻板印象。显然,这一剧场情景并非邀请性的,而是携带着偏见与歧视,其底层的元语言系统指向一个时代无处不在的社会歧视。如果情景的元语言系统受制于一方的隐性支配和控制,并且失去了对话得以发生的自由基础与平等结构,那么,文化之“跨”所寻求的交集区域便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邀请修辞所强调的情景,并非霸权话语规约下的独白式情景,而是非操控性的情景,是现象学的情景,是自然主义的情景,是悬置了劝说意图的情景。
可见,在邀请修辞那里,情景既是沟通的媒介,亦是沟通的内容,它超越了古典修辞学所强调的情景工具论,也超越了新修辞学所强调的情景反映论,并且沿着两个维度拓展了情景的修辞内涵:一是情景信息论,即情景构成了邀请修辞的认知主体,受众所获取的信息即是情景本身;二是情景媒介论,即情景本身构成了一种连接结构和中介关系,而彼此之间的理解达成,源于对方进入一个熟悉的、通约的、可对话的情景之中。
概括而言,邀请修辞将情景推向了认识活动的中心位置,即信息并非附着在情景之上的“对象”,亦非滋生于情景之中的“果实”,而就是情景本身。按照心理学的建构主义观点,人类认知活动中的意义建构依赖于情景的创设,正是在情境中,认识活动拥有了更丰富的外部线索和关联结构,从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的认知结构。邀请修辞充分认识到情景本身在沟通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其上升为“邀请”的现实条件,同时视其为“邀请”的直接对象。不同于一般的沟通方式,由于跨文化传播存在文化之间的区隔或距离,以“情景”为基础的“修辞方案”构建则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
相应地,邀请修辞所强调的“平等”“内在价值”以及“自我决定”同样存在一个深刻的“情景承诺”,即能否达到“邀请”而非“劝说”的修辞目的,根本上取决于修辞主体的情景配置理念和方案。无论是“平等”所关注的身份问题,还是“内在价值”所强调的主体性问题,抑或是“自我决定”所讨论的认知方式问题,都要求参与者之间的沟通本质是对话,是相互理解,是承认相互的主体性。而要达到沟通活动中的“邀请”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修辞方案便是以情景为方法,构建基于情景的对话系统。纵观当前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尽管情景被推向极为重要的沟通位置,但作为沟通发生的场所或语境,情景究竟是促进了主体间的平等对话,还是掩饰甚至加剧了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本质上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情景修辞“语言”。不可否认,当前的跨文化沟通往往充斥着各种隐性的、匿名的、复式的压制关系,而这一劝说效果的达成,更多的是通过对情景的策略性设计完成的——情景表面上呈现的是一个中立的、描述的、客观的、现实的环境结构,但选择何种素材、侧重何种主题、讲述何种故事,最终往往服务于极为隐蔽的劝说目的,即便是当前较为流行的零度修辞,也往往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另一种修辞。例如,旨在讲述美国西进运动的大平原印第安人博物馆(The Plains Indian Museum),主要选择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交往故事作为情景修辞资源。尽管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但其中的情景修辞方法却是通过“忘记”来制造“记忆”,这里没有杀戮和死亡,也看不见印第安人文化所遭遇的侵蚀与消亡,西进运动最终在由“敬畏修辞”(rhetoric of reverence)所构筑的故事情境中,变成了一种朝圣式的“和平之旅”。
如何构建“邀请”得以发生的“修辞方案”?一种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方法便是以情景为修辞对象,实现从“控制”到“邀请”的情景语言转换。在美剧《迷失》(Lost)中,亚裔夫妇的“遭遇”如同一个微妙的隐喻,形象地阐释了跨文化沟通的情景转换方式。一架从悉尼飞往洛杉矶的客机不幸坠落在一座孤岛上,不同国家、种族、性别、职业的乘客在这里被迫“相遇”。在接下来的“日常生活”中,一场跨文化之旅拉开序幕。这场“猝不及防”的意外,促使每个人被迫进入一个陌生的交往情境之中,由于外部秩序暂时失效,众人被悬置在一个由“初始认知”和“经验知识”所设定的伦理、情感及利益交往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语言”,主要依赖于自我对他人的“原始印象”——正是在这一特殊的情景结构中,自我对他人的想象方式限定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内容和交往边界。剧中的韩国夫妇在充斥着偏见与歧视的情境中入场,他们在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模式中,被建构为公共生活中的“失语者”——妻子的沉默寡言,丈夫的保守、粗鲁、怪异,加之韩语和英语之间存在着沟通壁垒,都使得他们与西方话语主导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这种“交流的无奈”源于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模式——在西方人眼里,韩国夫妇实际上是以“亚裔”标签的整体形象出场的,他们存在的目的便是完成多元世界的象征性“拼图”。在最初的交流情境中,亚裔夫妇的韩国身份是被隐匿的,他们被迫笼罩在“东方”的总体规定性之中,失去了主体身份上的自我。而在后续的情节中,韩国夫妇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认可,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进入了一个邀请的对话情景,完成了情景语言的转换——白人妇女哮喘发作,生命垂危,韩国妇女从山上采摘草药,以极具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救治方式,帮助病人渡过难关。正是在生命叙事所铺设的文化情境中,亚裔群体才得以真正进入“集体”,“东方”也获得了合法的出场方式,并与西方文化实现了和解。不难发现,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话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沟通发生在超越常规沟通规则的新的情景之中,由此重置了情景运作的底层规则——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语言受制于种族话语的隐性支配,新的情景语言则超越了“东方与西方”的二元框架,在种族话语之外打开了一个新的沟通情景,其特点是在伦理、生命、情感维度上编织了一种可能的通约语言。
四、基于情景的对话:何以可能?
邀请修辞赋予了情景积极的认识位置,并将其推向实践的向度——人们源于沟通的需要,对相关要素进行重新选择、组织和整合,以建立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性的、装置性的环境系统。长期以来,情景被视为一种对象性的、背景性的、空间性的沟通要素,仅仅具有场景、地点、环境的物理属性功能,而主体与情景的关系,也被视为一种镶嵌结构,即情景更多的是作为意义的“支撑”系统和“供给”平台出场,其功能便是为意义活动引入诸多外部线索,以拓展和丰富主体认知的可能视域。但在跨文化沟通模式中,情景是“邀请”的重要“抓手”,要真正实现情景意义上的邀请,客观上需要重构情景的生成语言。
(一)情景中的框架:从论证转向事实
跨文化沟通之所以存在认知距离,甚至伴随着一定的偏见和冲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彼此之间缺少“共同理解”得以发生的认知基础。实际上,弥合偏见、消除冲突的基本思路,便是识别、发现或再造文化之间的通约语言,即根据认知距离产生的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情景创设工作。
纵观当前跨文化沟通的认知“壁垒”,更多的偏见和冲突主要发生在话语维度与观念维度。一方面,话语和观念都建立在论证基础之上——话语的正当性确立以及观念的知识性建构,必然伴随着逻辑与推演基础上的论证实践。正是在论证铺设的逻辑结构中,现实拥有了一种经由话语授权的描述方式、排除法则和分类体系,观念也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进入群体意识维度,成为群体行动产生的认识基础。另一方面,话语和观念往往又是修辞建构的“产物”,而修辞的基本作用方式便是对话语和观念赖以存在的认知框架加以激活或再造。因此,在跨文化交际模式中,话语或观念的冲突,本质上体现为认知框架的冲突,即人们赋予了事物不同的理解模式,由此建构了不同的“现实”。进一步讲,不同主体之间之所以产生认知距离,根本上是因为彼此身处不同的文化语境,形成了不同的认知范畴。范畴本质上对应的是一个认知框架命题,即个体在事物的属性界定、内涵归类、性质提炼上所诉诸的一套认知框架。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框架,是你看不见也听不到的东西。它们属于认知科学家称为‘认知无意识’(cognitive unconscious)的环节,是我们大脑里无法有意识访问,只能根据其结果(推理方式和常识)来认识的结构”。由于框架限定了人们认识事物的加工模式,故任何话语形式的建构,都存在一个基础性的框架生成逻辑,其文化意义上的认知后果是:框架冲突必然转向话语冲突或观念冲突,而话语或观念冲突也必然存在一个基础性的框架冲突。
因此,在跨文化沟通实践中,克服话语冲突或观念分歧的修辞学方法与路径,便是从框架问题切入,寻求彼此之间的框架协商可能及其通约语言。区别于其他场景中的框架运作机制,跨文化沟通中的框架冲突,更多地源于彼此之间缺少共同理解而形成了不同的“框架依赖”,由此建构了不同的“现实”。相应地,框架协商与调适的基本方法便是对框架进行“降维”处理,重返框架存在与形成的现实与经验维度,创设基于事实的而非论证的修辞情景,从而在事实维度上调适“原始框架”所携带的偏见和冲突,即通过对事实的重新挖掘与呈现,重新进行争议宣认,进而实现框架与框架的通约与对话。
之所以强调事实之于框架调适的可能,是因为在修辞学的传统中,事实框架不但意味着一种基础性的框架形式,而且是一种通往争议宣认(argument claim)的修辞发明实践。按照古典修辞学的争议点理论,框架存在一个普遍而深刻的“争议之维”或“争议之所”,而争议不仅铺设了框架“出场”的修辞情景,也构成了框架认知与存在的“显现”方式——不同的框架形式,不过是对争议的不同宣认方式。而回应争议的有效方式,便是回到事实本身。正因如此,古希腊修辞学将事实上升为一种框架形式,强调在事实维度上对争议进行宣认,以寻求一种基于事实的协商方式。古希腊修辞学家赫尔玛格拉斯( Hermagoras of Temnos)以法律修辞为例,将“事实”(fact)、“定义”(definition)、“品质”(quality)和“程序”(procedure)确定为修辞情景中的四大核心争议点,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争议宣认的四种框架形式——事实框架、定义框架、品质框架和程序框架。其中,事实框架意味着一种基础性的元框架(meta-frame),即一种解释框架的框架,其功能便是铺设了其他框架的生成语言。因此,跨文化情景创设的基本思路便是转向一种事实性的、陈述性的、白描性的情景构建理念,使得受众能够在情境中获取原始的事实信息,依照“现实原本如此”的加工模式,调适自我的初始框架,以寻求框架维度上的对话之可能。
概括而言,邀请修辞视域下的跨文化沟通之情景创设,需要回到事实这一基本的认知原点,以事实调和不同主体之间的框架冲突,重建公共对话的协商基础,具体的建构思路可以概括为:以事实代替立场,以陈述代替推演,以白描代替观点,从而将各种隐匿的主体意图和无意识话语悬置起来,以创设一个自由的、对话的交际情景。实际上,古典修辞学中的情景,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立场先行”的问题,其内部的规则往往是不平等的——修辞者不仅创设了情景的存在形式,还决定了情景的生成规则,这使得情景维度上的意义实践必然携带着某种隐秘的劝说欲望。例如,作为一种基本的元框架形态,定义框架(define frame)总是尝试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方式设置议题,通过对事物性质的界定和推演,限定或引导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模式,这显然不符合邀请修辞的情景建构理念。相反,只有当情景的构成方式更多地建立在事实元素、客观陈述、直接描述的基础上时,受众才能从那些隐蔽的话语“牢笼”中解脱出来,主动、独立且自主地绘制自我的认知地图,形成关于现实的理解方式。李子柒的短视频能够在海外引发广泛认同,离不开其在情景修辞上的探索——相对于其他专题片普遍使用的“主题先行”外宣模式,李子柒最大限度地淡化影片中的论证色彩,甚至很少使用旁白,最终通过对现实的深描和记录,打造了一个基于事实的而非论证的修辞情景。
之所以强调事实的而非论证的跨文化情景生成机制,根本上是因为论证中往往潜藏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态度和目的,不利于参与者形成独立的自我判断。在新冠疫情期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概念时,便通过概念隐喻的修辞模式,构造了一个充斥着偏见和暴力的符号情景。在跨文化沟通实践中,如何创建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认知情景,是邀请修辞首先需要回应的情景问题。然而,在被权力话语所支配的传播体系中,事实或者被权力或利益暴力遮蔽,或者被道德偏见公然掩饰,抑或被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悄然掩盖,因此,从论证情景转向事实情景,意味着需要讲述那些未曾被修辞术裁剪的故事,复盘那些未曾被话语和权力支配的现场,以及复活那些未曾被论辩裹挟的陈述与记录。在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中,那些由家人写给逝者的书信占据了较大的空间“篇幅”,游客行走于其间,经历并体验着彼此的故事。这些信件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中,其目的是打造一个沉默的、吸引人聆听的超时空对话情景。
(二)情景中的规则:从论辩转向行动
古典修辞学所关注的情景问题,主体上是围绕文本层面上的意义语境展开的,而语境构建的理念与规则,主要体现为劝说维度上的论辩模式,即语境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论辩性的文本情景,其特点是借助一定的叙事策略,建构或生成某种框架性的认知模式,以引导受众进入主体预先设计的话语“管道”,从而实现主体意图的合理化与正当化。在经典修辞学的“修辞五艺”中,“发明”和“谋篇”不仅意味着论辩发生的修辞策略,而且揭示了语境深层的论辩语言及其生成规则——“发明”所关注的话题制造,本质上意味着对某种认知框架的建构,而一种框架一旦在语言维度上被生产出来,便悄无声息地铺设了一种模式化的、图式性的论证结构;“谋篇”所关注的语篇组织,意味着对某种叙事情景的建构,而叙事活动中常见的讲故事,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故事化的论证方式,其特点是将修辞者的意图或观点悄无声息地植入故事情境中,达到潜移默化的劝说效果。不难发现,古典修辞学所关注的情景,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论辩情景,而情景作为一种修辞元素出场,旨在服务于论辩意义上的逻辑和推演。
在跨文化沟通实践中,由于不同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强弱之分,论辩很容易转向一种独白式的自我表演,而另一种声音则被迫陷入从属的、匿名的、沉默的位置,难以获得对等的“发声”空间。如何实现跨文化沟通中的“和声”与“复调”?一种常见的思路便是重构情景的生成规则——从论辩转向行动,在行动中寻求可能的对话方式。在邀请修辞的知识视域中,情景的内涵延伸到了“行动”的维度——情景不仅是主体相遇的“场所”,而且铺设了主体交流和对话的行动者网络。必须承认,跨文化沟通之所以存在刻板印象,是因为彼此之间缺少对等的可见性——当他人处于自我认知的模糊区域或黑暗区域,自我便会本能地根据某种认同需求,重构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其后果便是将对方推向文化意义上的劣势位置,以此获得自我身份的合法地位。正是在这种不可见的想象性关系中,刻板印象被悄无声息地生产出来,并作用于主体性的建构过程。而破除刻板印象的有效方式,便是将对方邀请到一个行动的情境中,赋予对方行动的自由和空间,以此重新审视自我与他人的交往结构。由北京师范大学于2011年发起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每年邀请外国青年来华进行影像创作,由他们自由地发掘素材,讲述故事。这无疑创设了一个行动的交际情景,从而将传统的文本情景延伸到行动情景。概括而言,由于不同文化处境中的个体存在一定的认知距离,“邀请”功能实现的跨文化情景创设方式,主要体现为改变古典修辞学所强调的以控制为目的、以论辩为手段的语义生成规则,而转向一种行动的交往情景。
实际上,从论辩转向行动,意味着通过跨文化情境中的行动设计,赋予彼此一种基于行动的连接方式,而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复调”效应,行动的内涵有必要延伸到“共创”的维度。只有在彼此深度参与的共创情景中,跨文化沟通才能彻底改写长期以来的“凝视结构”,并最终转向一种平等的、复调的、自由的“对视结构”或“共视结构”。之所以强调情景规则的共创内涵,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共创行动,往往能够最大限度地激活并放大彼此的可见性(visibility),进而在一个可见的行动框架中,使得彼此能够看见对方,进而形成更为稳定的连接关系和依存结构。2016年,千龙网发起的中外漫画家“1+1”结对共画最美北京活动引发了广泛热议,这里的行动情景设计规则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参与”,而是转向了“共创”的维度。
之所以强调共创情景之于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意义,是因为只有进入共创性的行动情境中,彼此之间才更容易形成一种协同共生的依存关系,这无疑有助于态度、信念、行为乃至价值维度的对话。埃里卡·W.奥斯汀(Erica W. Austin)和布鲁·E.平克里顿(Bruce E. Pinkleton)绘制了人类认知的金字塔模型,认为个体的认知行为是分层次的,从低到高依次为:感知(awareness)、知识(knowledge)、观点(opinions)、态度(attitudes)、信念(beliefs)、短期行为(short-term behavior)、持 续 行 为(sustained behavior)和价值(value)。随着认知层次逐级升高,认知结构愈加稳定,相较于低层次的感知、知识,高层次的信念、行为、价值更加难以改变。其中,价值代表了一种极为稳定的图式系统,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对话基础只能是“承认”而非“论辩”,正如奥斯汀和平克里顿所说:“当那些自命非凡的游说组织试图去改变公众的价值时,他们最后却失望地发现,这种尝试经常是没有必要的(unnecessary),而且是不现实的(unrealistic)”。因此,共创之于跨文化沟通的意义在于,构建了一个协同的、共生的行动情景,这有助于超越古典修辞学的论辩逻辑,打开价值对话的“行动之维”。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全新的情景构建理念,共创深化了行动的内涵,也改写了论辩的底色,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主体行动维度上编织了“共同理解”之可能。
五、讨论:数字叙事与“ 邀请”的另类实现
相对于较为宽泛的“语境”概念,本文所讨论的情景,属于一种具体的语境形式。从符号学视角来看,任何解释行为都依赖于一套元语言系统,而符号所处的语境便是一种基础性的元语言,其限定了事物的存在结构,也决定了事物的释义规则。必须承认,语境并非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范畴,而是存在三种常见的形态——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互文语境,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解释规则。不可否认,在现代媒介技术环境下,三种语境形态的形成及发生机制,都存在一个基础性的传播生成向度,即语境本身所携带的解释规则,往往需要诉诸媒介与传播的认识视角,如此才能完整地把握语境发生作用的“语法”系统。例如,在图像的阐释结构中,媒介逻辑已经深度嵌入图像的生成系统,由此形成了一种由“物”及“图”的阐释语言;与此同时,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互文语境所打开的图像释义空间,都需要回到“传播”这一基础性的生成装置中寻找答案,即传播的“语言”深刻地影响着语境的生成结构和解释规则。
必须承认,当前修辞学所关注的文本及其修辞情景问题,主体上建立在经典叙事学的“文本”概念之上,而新媒体环境下的数字叙事,如空间叙事、声音叙事、互动叙事、再媒介化叙事,极大地拓展了经典叙事的文本呈现形式及生成方式,尤其是通过对数字情景的构造,进一步延伸了文本与受众之间的“相遇”方式,并使得“基于情景的对话”呈现多种面向和可能。那么,在跨文化沟通实践中,数字技术是否有助于创设一种平等的、自由的沟通情景,是否有助于实现跨文化沟通的“邀请”使命,无疑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学术命题。
由于传播结构中的情景存在普遍的媒介化配置与生成基础,数字叙事之于情景的构建与生产实践主体上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文本语义情景的数字化建构。当前数字叙事的图像化、情感化、游戏化、剧场化“转向”,有效拓展了主体对话的“邀请”形式;二是现实情景的数字化重构。由于传播结构中的情景存在一个普遍的媒介化配置与生成体系,数字叙事有效拓展了数字情景(digital situation)的生产实践。只有关注数字叙事之于情景的建构方式及运作语言,才能在情境维度上拓展并创新跨文化沟通的邀请修辞实践。
在数字媒介技术的装置结构及其中介系统中,一系列新兴的数字情景形式(如VR空间、AR空间、直播空间、元宇宙、混合场景、导航空间)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除了对现实场景的数字化修饰与改造,数字技术还通过对叙事和位置加以绑定,将虚拟与现实整合进同一个叙事系统,一种新兴的数字情景形式——混合空间(hybrid spaces)由此生成了。更为重要的是,以VR、数字游戏为代表的交互式数字叙事,更是通过对新兴情景形式的创设与再造,解决了叙事中的身体“在场”问题,从而将身体安放在叙事之中,重建了作者、读者、文本、环境之间的复杂情景,这使得建立在具身性基础上的跨文化沟通之“感同身受”成为可能。当身体获得一定的叙事位置,并拥有一定的穿行能力时,情景的观念便发生了变化,其不再是静态的空间形式,而是呈现出一种流动的属性、状态和趋势。不难发现,数字叙事极大地释放了“邀请”的想象力,也拓展了情景的形式、语言及功能,未来的跨文化沟通之邀请式情景构建,亟须重视并研究数字情景生成的修辞之道。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及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2VRC068)的研究成果。
引用参考
刘涛.基于情景的对话:邀请修辞与跨文化沟通的修辞实践[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3(02):81-102.
作者简介
刘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