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传播与社会、乡村传播、国际传播、智能传播、经济传播和博物馆传播专题研究六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网络媒介与农村妇女自我赋权——以黔东北“闺蜜圈”闲暇实践为例》,作者胡晓映 吕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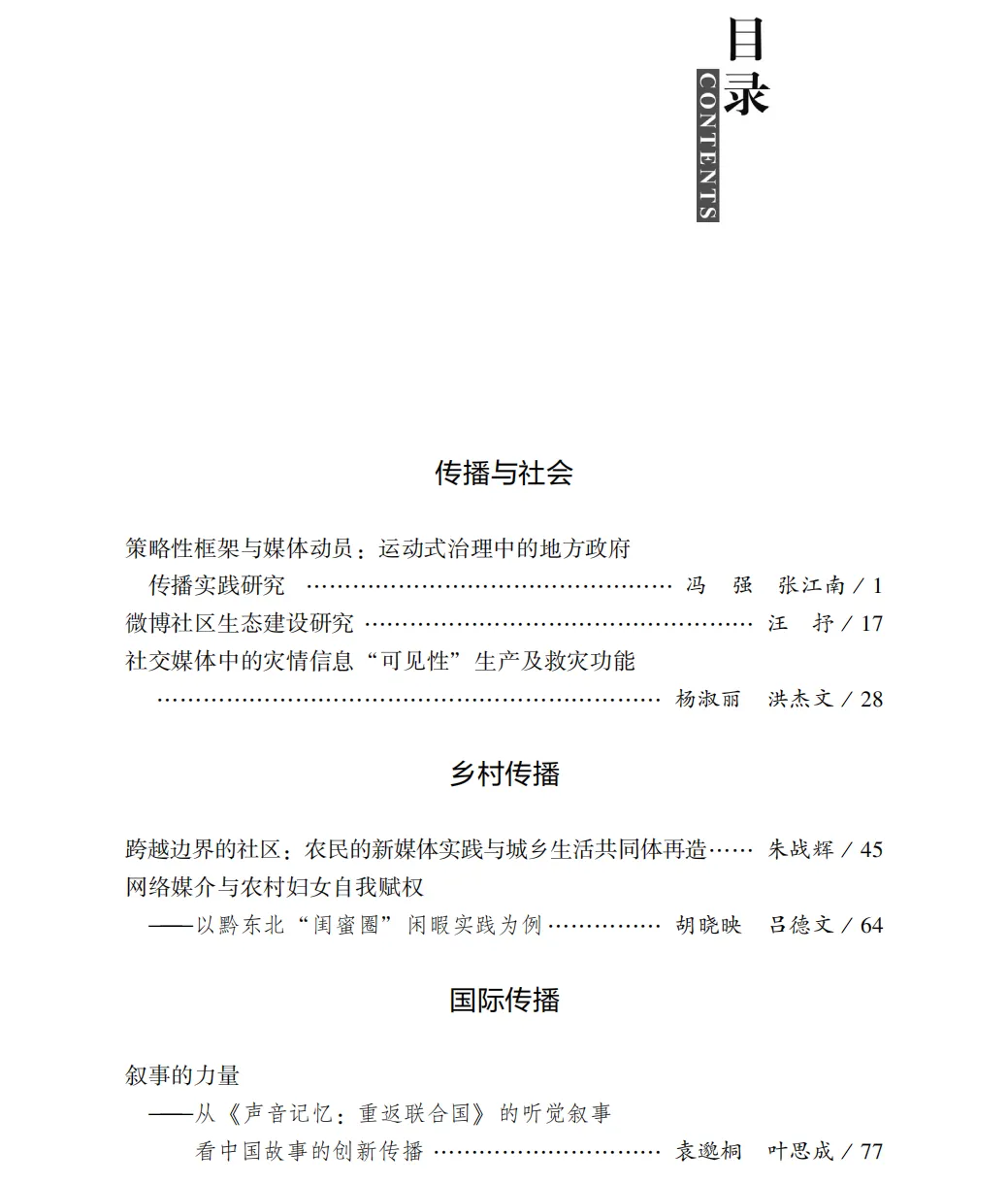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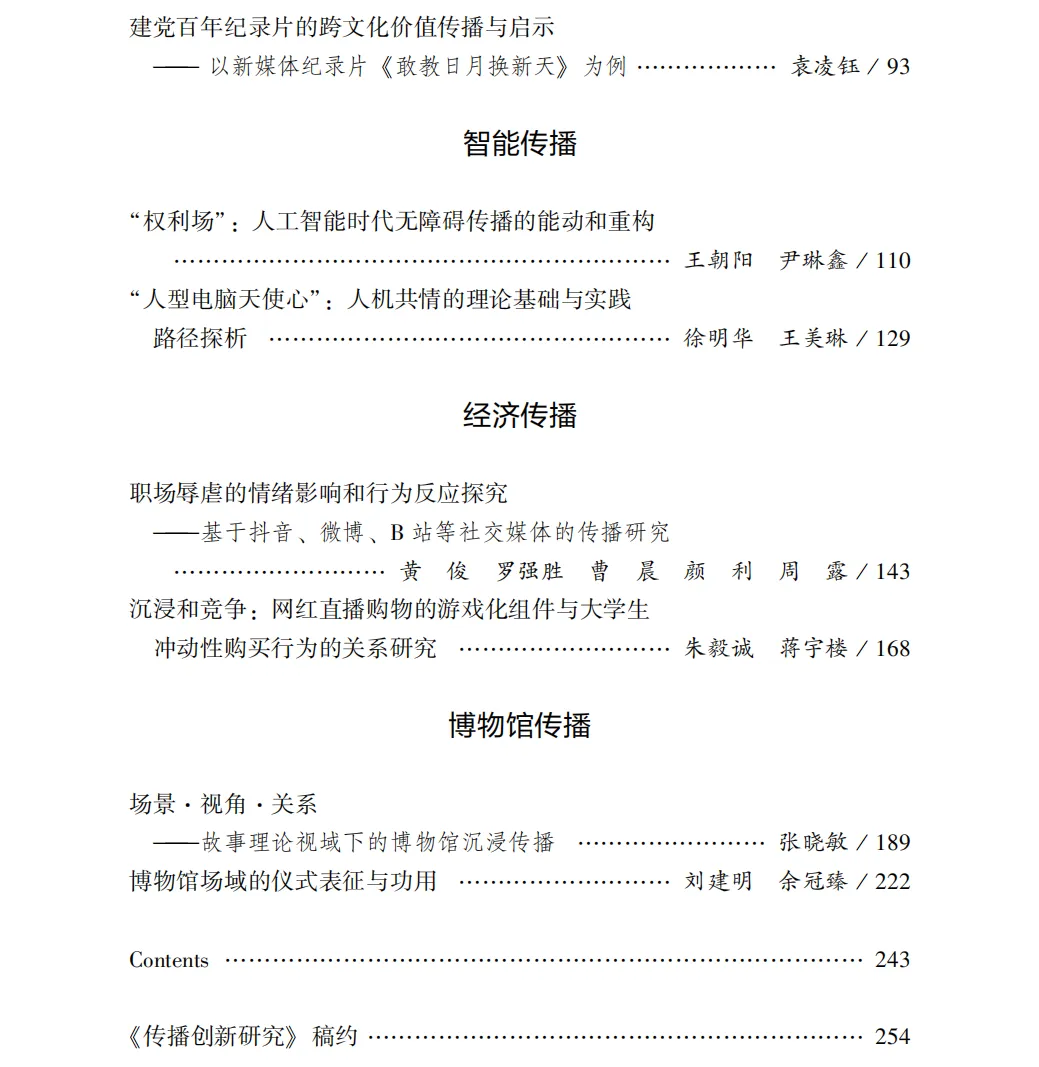
网络媒介与农村妇女自我赋权——以黔东北“闺蜜圈”闲暇实践为例
胡晓映 吕德文
摘 要
网络媒介深刻改变乡村女性的个体生活,促使其形成多样化的闲暇方式。本文以“闺蜜圈”这一农村妇女闲暇新方式为切入点,分析其具体实践及特征,探讨网络媒介在妇女闲暇与个体日常生活、乡村社会交往之间的功能。研究发现,网络媒介在乡村社会关系重构中的功能性,网络媒介的个体选择差异性,网络媒介的普及与妇女个体表达、价值彰显需求的契合性,是当前乡村女性“闺蜜圈”这一闲暇方式产生的三重因素。妇女在网络媒介基础上形成的新闲暇方式,能够实现妇女对个体价值、“自由”闲暇生活、个体情感释放的三重赋权,促进农村妇女个体意识的觉醒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
关键词
新媒体;“闺蜜圈”;农村妇女;闲暇生活
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进行深入探讨,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极具启发性,他认为收音机、电视机等现代媒介是“闲暇机器”,实现对生活领域媒介的分析和批判。这些“闲暇机器”深刻改变了社会关系,将全世界的信息无边界的带入个体生活,但其单向性将个体闲暇附着于机器之上,使闲暇朝个体化方向发展。移动网络和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发展使闲暇迈入新的纪元。移动网络的互联性使闲暇具有个体特征的同时,带有双向互动的中介属性,形成以关系为导向的、对话式的全息传播模式,扮演了公共与私人、社会与自我之间的桥梁。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媒介深刻改变了个体生活,这不仅表现在城市之中,也表现在乡村之中,使乡村生活呈现新特征。在全国各地的农村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前移动互联网深度嵌入农民生活。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3岁的孩童,都已成为网络媒介使用的主体,他们用手机看视频、玩游戏、网上聊天的生活片段,是当前乡村生活的常见景象。在人口流出、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妇女因照料老人、抚育子代等家庭分工留守家中,成为乡村社会的重要主体,同时是网络媒介使用的重要主体。农村妇女处于真实的传统乡村社会空间与虚拟的网络现代化空间的二元张力之中,网络媒介极大影响了她们的生活方式,推动其现实的闲暇生活朝多样化方向发展。在逐渐走向“半熟人社会”的乡村社会中,农村妇女通过网络媒介进行自我赋权,并在“闺蜜圈”等线上、线下的闲暇实践中,实现自身情感、价值和生活意义,促进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
一、文献综述
当前,媒介已经从以单向大众传播为主的第一媒介时代、双向和互动传播的第二媒介时代,向21世纪最新的沉浸传播的第三媒介时代转向。网络媒介成为当前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因素,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进而影响到妇女对自身生活方式的想象和实践。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女性成为乡村社会的重要主体,并日益成为网络媒介使用的重要主体。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的农村妇女,逐渐成为网络赋权的重要对象,受到学界关注。
赋权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歧视研究,后被引入社会工作领域,成为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的重要理论。网络社会的兴起给予赋权理论新的研究意涵和发展方向,使“为弱者的传播”转变为“弱者的传播”,该理论开始重视弱者的内部性、关系性和能动性。
传统媒介仅能实现小规模群体间的交流,难以实现对弱势群体的真正表达,反而容易形成武断的标签进而加深群体误解,但网络媒介的便利性、普及性和深度渗透性,能够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心理赋权、组织赋权和社会赋权,展现其传播赋权和意义赋权的特征。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新权力来源,能够向相对无权者进行权力转移,通过关系实现赋权,以支配和控制为核心的控制权正在消解,个体行动权和自由价值正在回归。由于网络媒介的重要角色,有学者将媒体素养教育看作性别平等倡导战略,实现媒介从“灌输”向赋权的功能转向,使妇女能够在参与式传播这一新媒介特征时代,充分利用传播渠道参与公共话题并发声,促进社会多元群体的表达。
虽然网络媒介开启了对赋权研究的新视角,但学界关于网络媒介对农村妇女赋权的实证研究较为有限。新媒体的赋权功能促进了乡村女性主体意识的崛起,打破了传统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控制,乡村女性通过网络媒介的使用构建新的社会身份与角色。石义彬、邱立对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赋权进行研究发现,留守妇女的工作、家庭职责分工和角色期待,使她们处于有限使用社交媒体的状态,但她们会积极借助社交媒体调节情感、维系辅助生活、获得自我认同,最终丰富留守生活。对于外出的女性农民工来说,网络媒介能够使她们更好的适应城市、获取就业信息、扩大生计来源、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以增加职业选择、学习知识提高技能,从而实现女性农民工从无权到有权、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路径,并且呈现不同生命历程中不同的网络媒介使用习惯和内容偏好,以满足家庭和工作需求。
在有限的农村妇女赋权研究中可以发现,对留守妇女、流动女工等身份的描绘,充分体现了农村妇女在所处社会结构中的弱势性,网络媒介凭借易得性、与工作的互嵌性成为农村妇女生活与工作的必备品,成为农村妇女自我赋权的重要途径。这一研究结果具有启发性,但并未真正凸显网络媒介的参与式互动及其独特的关系重构属性。赋权并不是简单的外部权力和资源的输入,而是要在社会交往、参与、表达与行动实践中实现从权力客体向能动者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深入农村妇女的生活、社会关系实践,探讨网络媒介如何实现农村妇女的自我赋权。因此,本文从农村妇女的闲暇生活出发,从以网络媒介进入后农村妇女间形成的“闺蜜圈”这一新闲暇方式出发,探讨“闺蜜圈”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生成逻辑以及网络媒介与农村妇女自我赋权的实现。
本文的田野调查资料来源于笔者2021年3月在黔东北C镇下辖的H村进行为期20天的调研。调研中,笔者对村委会成员、各年龄段妇女等40余位访谈对象进行深入访谈,形成对村庄情况的整体把握。H村在地理位置上属于镇郊村,与C镇距离仅几公里,距离市区十几公里。本地农业种植条件有限,土壤肥力低、耕作技术落后,现仍以水牛犁地为主,除极少数老年人仍耕种口粮田外,大多数村民放弃耕种进入市场就业。由于耕作条件恶劣及本地市场有限,本地村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出务工并持续至今,因此本地村民几乎都有打工经历,劳动力外流严重,在村人口以老年人、妇女和小孩为主。由于靠近市镇,本地有一定村民可非正规就业,男性多从事建筑、修车行业或自主创业,女性在家带孩子兼做小手工,或做建筑小工、个体户,时间相对闲散。作为具有典型西南特征的地区,本地消费习惯与其收入水平并不一致。本地娱乐业十分发达,C镇上半夜十二点仍有五六家宵夜摊生意红火,跟朋友吃饭聚餐、旅游是本地村民生活的重要休闲方式,因此,闲暇在本地具有正当性和普遍性,除了男性的闲暇方式以外,女性因为时间的灵活性也形成了独特且多样的闲暇方式。
二、“闺蜜圈”产生历程及其特征
“闺蜜圈”既区别于村庄内与劳动相嵌套的弥散性闲暇方式,也区别于个体式闲暇方式,而是在乡村熟人社会基础之上,以网络为媒介形成的具有共同兴趣爱好、行为模式的建构性组织。“闺蜜圈”从人员加入活动开始,各个环节都离不开现代媒介的参与。本文在对村庄妇女生活具有整体性把握的前提下,选取燕姐的“闺蜜圈”这一单个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探讨“闺蜜圈”内部结构及其产生历程。
本文研究对象———燕姐的“闺蜜圈”,其雏形出现于2014年,起因于燕姐组织的三亚之行。燕姐作为镇上家电店的老板,社会关系主要包括村内关系、镇上熟人关系、生意群体关系,她凭借超村庄范围的人际关系网,组建了以自身为核心的闲暇关系网络。
2014年,燕姐被旅行社的三亚宣传手册吸引,她利用自身熟人社会关系,组织村民、朋友等共24人,开启了三亚之行。当时费用为每人2680元,这对当时的村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也意味着参与旅行的村民生活条件相对不错,也对休闲有向往和兴趣。在旅行过程中,燕姐因手机像素最好,成为拍照主力,回村后,她通过给同游者分享照片,成为本次旅行的绝对组织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燕姐与其中两位成员建立了良好关系,但还未形成“闺蜜圈”,仅是私人关系的联结。回村后,因错过旅行而遗憾的另外两位女性具有较强的闲暇意愿,积极融入三人关系,由五位妇女组成的“闺蜜圈”雏形出现。
微信群的建立是“闺蜜圈”形成的标志。普通朋友或待加入的“闺蜜圈”成员能够参与“闺蜜圈”的活动,但她们不算正式成员,只有被拉入微信群,其成员身份才算真正被承认。以燕姐的初中同学张姐为例,她在2018年第一次参加“闺蜜圈”的出游活动,因为性格开朗、很爱互动,获得大家一致喜欢,在几次互动后,在所有成员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被正式拉入群,成为“闺蜜圈”的一员。“闺蜜圈”成员的必备特征有两个。其一,大家要能“说得来”。“闺蜜圈”作为个体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经常会聊一些较为私密的情感话题,如果“说不来”,一些话便不能在圈子里公开说,这就极大削弱了表达的随意性,就会“不敢无所顾忌的开玩笑,让人放不开”。其二,“闺蜜圈”成员中每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都要一样好。后续成员的加入主要以最初“闺蜜圈”成员的朋友身份为契机,但进入“闺蜜圈”后,新成员不能仅跟自己的介绍人一起玩,而是要跟每个人都搞好关系,打造情感平均化的关系群体。
“闺蜜圈”的活动十分丰富,主要分为日常活动和外出活动。“闺蜜圈”主要在本地范围内开展日常活动,正常情况是两周一次。“闺蜜圈”成员在抖音发现好的游玩地点便会分享到微信群,大家或者在时间充裕时说走就走,或者提前计划时间、安排出行事宜。外出活动是每年一次的出省旅行,自驾游或旅行团的形式都有。在外出活动中,每个人都有任务,如开车、订票、规划路线、照顾行李等,内部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妇女们虽然时间相对充裕、家庭发展压力较小、具有较强的闲暇需求,但会有意识地节省开支。外出旅游花销为800~2500元,在本地游玩以AA制为主,且活动一般是不要门票的免费景点、挖野菜,去KTV等娱乐场所也会充分利用网络优惠,每次出行一般为20~30元,最多也不会超过100元。从“闺蜜圈”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出,“闺蜜圈”具有三重特征。
首先,“闺蜜圈”具有内部组织性。从成员加入活动开始,成员就有相应的权利和责任分工。“闺蜜圈”虽然以燕姐为核心,但总体呈现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比如,新成员加入需要经过每个人的同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活动的发起者,即提供出行信息并约定时间。另外,为了避免不公平感,每个个体在出行中都要发挥作用,不能“坐享其成”。
其次,“闺蜜圈”是纯粹的情感互助单位,不能有小圈子以免群体分裂。在预备成员考察期,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跟所有人都“说得来”“玩得好”,这使“闺蜜圈”成为妇女排解情绪和情感疏导的重要方式。同时,为了保持情感的纯粹性和团体的持久性,圈内避免谈论家庭内部纠纷或利益相关话题,避免产生利益纠葛;出行要尽量选择有优惠的活动并采取AA制,避免产生利益冲突。
最后,“闺蜜圈”的闲暇活动并未脱离现实生活,而是嵌入家庭生活和乡村社会。从成员构成上来说,所有成员都是本地人并持续参与线下闲暇活动;从活动开展时间上来说,主要是在处理好家庭、工作事务后开展的,甚至有调节家庭关系的功能,如燕姐想要跟闺蜜外出旅行,为了征得丈夫同意,提议与婆婆一起去,也趁此机会缓解了婆媳矛盾,重塑家庭关系。
三、网络媒介与“闺蜜圈”的生成逻辑
(一)网络媒介下的关系重构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网络媒介区别于传统独白式线性传播模式,形成以关系为导向、对话式的全息传播模式。这种关系意味着依托于网络的强大交互特征,通过跨时空的电子对话进行人际关系构建,形成新的关系联结,这是网络媒介连接个体与世界最重要的表现。与此同时,网络媒介既改变了原本乡村社会样态,也与乡村独特的社会基础相结合,重塑乡村社会关系。
在人口流动、现代化因素介入等现实背景下,村庄公共关系的组织基础发生变化,逐渐向私人关系转向。在这一过程中,广播、电视等媒介的进入极大促进了乡村社会关系与闲暇的个体化,村庄公共性逐渐被消解。但以关系为导向的网络媒介的进入,契合了部分村民的个体闲暇需求,加深了闲暇个体化倾向,同时其交互性能够实现个体、村庄社会与整个世界的互联,形成多重可能选择,“闺蜜圈”这一新闲暇方式是这三个方面互动的结果。从“闺蜜圈”的产生、组织和发展的角度来说,媒介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闺蜜圈”成员关系界定、活动组织信息获取、出行活动辅助等多重功能。但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媒介并非形成超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联结,而是在乡村熟人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实现对现实关系的再联结、对村庄关系的重塑,形成稳定的社会关联群体。网络媒介具有实现再造社会关系的功能,其核心是与乡村现实社会关系、村庄传播节点共同发挥作用。“闺蜜圈”的组织者燕姐,处于乡村社会关系的“节点”位置,她利用网络媒介进行关系构建,并作为活动的组织者持续发挥作用,通过开展活动并将其拍摄成小视频发布到抖音、微信朋友圈,实现信息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在这一闲暇实践中,网络传播与人际传播实现了结合,构建稳定的在地化新组织方式,形成以乡村社会为基础、以具有组织性的妇女为中心的线上、线下乡村网络传播结构。
(二)媒介选择的个体差异
网络媒介作为重要的工具、手段,在不同群体中会产生不同影响,对不同年龄阶段、生活经历等的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媒介选择方式,进而影响其不同的闲暇方式的选择。这在“闺蜜圈”的人员构成上表现明显。
个体所处的人生阶段,是影响个体利用媒介手段选择闲暇方式的重要因素。田野调查发现,与媒介相关的闲暇方式选择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45岁以下的年轻农村女性,一方面要承担儿童抚育、教育等责任,另一方面要为工作奔波,支撑家庭发展。以一位生于1997年的留守宝妈为例,她每天都要照顾小孩、做家务,闲暇时间非常有限,她只有在小孩入睡后才能享受闲暇时光,在微博追星、玩游戏,通过追星构建关于世界的美好想象,通过玩游戏与自己的朋友圈再次联结,在网络世界获得短暂的“自由”。对于中年女性来说,由于子代长大、父代支持,她们的家务负担相对较小,但为了子代教育、结婚等发展性支出较多,家庭负担较大,因此需要深度嵌入工业体系,闲暇时间十分有限。她们经常会选择低成本、低交际性的闲暇方式,如刷短视频、跟练运动短视频等,既有闲暇性,又能锻炼身体。“闺蜜圈”的九位成员年龄均在45~55岁,正处于子代未婚或子代结婚但未有小孩的人生阶段,并没有繁重的照料子代或孙代的家庭负担,以及应对家庭发展的人生任务,具有参与闲暇活动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动力,因此能够充分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拓展丰富的闲暇生活。
在年龄阶段反映的闲暇方式选择背后,暗含的是个体闲暇时间、消费能力的差异。对于年轻女性来说,她们有消费和闲暇意识,但因时间安排服务于照料子代和家务劳动,缺少完整的闲暇时间;对于中年女性来说,她们因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减少了其为闲暇的消费开支,仍然以家庭发展为重心。但选择“闺蜜圈”闲暇方式的女性,她们凭借年轻时的打拼已经为子代结婚做好准备,或已完成人生任务,且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生活压力较小。同时,相对灵活的务工形式使她们有时间能够参与“闺蜜圈”活动。
(三)个体表达与价值彰显需求
女性受家庭角色的限制,休闲需求经常被隐匿于家务劳动、家庭发展压力之中,受到社会及其自身的忽视。当前,网络媒介对个体生活的嵌入,使女性更强烈地接受外部世界的差异化,并激发其更强烈的情感需求和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向往。
网络媒介独特的传播模式和丰富的传播内容,塑造了女性对新生活方式和情感关系的想象。在田野调查中,女性经常会提到丈夫不懂得浪漫、不会表达爱意,这已经成为影响夫妻关系、塑造亲密关系实践的重要因素。新鲜、丰富的网络内容极大冲击农村妇女原有的知识和认知体系,抖音等短视频的即时互动性、竖屏传播的沉浸感、画面营造的在场感等都成为吸引农村妇女的重要因素。网络媒介快速、精准的传播效果给予农村妇女极大冲击,在无形中推动其产生模仿倾向,比如更注重节日、纪念日等节点,注重与丈夫的互动及赞扬等。虽然此类夫妻间情感表达日益成为年轻人的生活互动常态,但在乡村中年夫妻中,丈夫往往不善于情感表达,普遍无法回应女性的情感需求。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往往使女性具有向外寻求情感表达和个体认同的内在动力。与之相对,乡村社会中产生的个体行为规范和社会舆论,对村庄生活的个体具有极强的约束性,妇女具有被期待的伦理角色和行为方式,如要会过日子、在村庄中会为人等,这些角色期待使女性的行为和情感表达被束缚,难以具有正当的闲暇活动和情感表达途径。
在家庭和村庄的约束下,女性个体往往难以突破心理界限,对闲暇活动和情感表达表现出向往却无法实现的状态。但在家庭制度松绑、人口外流、乡村社会公共性衰弱等背景下,女性逐渐从家庭和村庄的束缚中走出来。但依靠女性个人力量,往往依然难以突破心理界限,对主动寻求闲暇活动和情感表达,仍表现出向往却无法实现的状态。“闺蜜圈”这一组织化的闲暇方式,给予妇女结构性支持,既能减轻女性独自面对村庄和家庭限制的压力,也能满足个体对闲暇活动和情感表达的需求,在与闺蜜互动中实现自身意义和价值。
四、网络媒介与农村妇女的自我赋权
农村妇女面临双重弱势处境,从城乡二元维度来说,农村在资源禀赋、社会资本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从性别角度来说,在社会分工和家庭分工中,女性相对于男性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网络这一获致性强、去中心化的媒介工具,是当前农村妇女自我赋权的重要途径。
(一)网络媒介与社会和个体价值的实现
当前,互联网的兴起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权力结构,尤其是话语权的分配。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乡村社会关系,在网络嵌入后逐渐形成“去中心化网络格局”,每个个体都能够成为相对独立的“传播基站”,在网络场域中行使表达权,也能在其中获得自我提升和自身身份认同。
农村妇女的闲暇生活受限于琐碎的家务劳动,经常被忽视。传统社会的农村女性的闲暇生活是嵌入农业劳动和家庭生活的,具有弥散性、无意识性,往往不算是真正的闲暇生活。随着女性嵌入工业体系,女性有了一定程度的闲暇实践,但家务劳动的重任仍然使其闲暇实践难以实现,或因交往途径限制,被动性选择广播、电视等个体化闲暇方式。单向性的媒介带给她们丰富的信息,却无法承担女性情感、价值等需求的实现功能。随着关系互动性的网络媒介进入日常生活,她们能够通过便捷的媒介工具,丰富自身闲暇活动的种类,并通过互动构建多样化的闲暇生活,在满足“打发时间”这一浅层次闲暇需求的同时,在互动之中满足情感表达、情感互动、个体价值彰显等多方面需求。
乡村社会本身的熟人关系特征,决定了农村妇女依托网络选择闲暇方式并非是完全个体化的,而是在熟人社会基础上进行的。由此,农村妇女构建以线下关系为基础、以线上互动为核心的“闺蜜圈”闲暇实践。一方面,妇女依托自身在乡村熟人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不断扩展“闺蜜圈”的人员边界,并形成内部组织性,通过开展活动强化和重构社会关系。同样,当前网络算法通过抓取用户信息实现基于熟人关系、兴趣爱好的个性化推送,使信息在熟人之间传播更为便利,能够实现村内村民、外出流动村民的信息共享,形成与不在村村民的脱域性联系,网络发布的信息既成为村民见面时的话题谈资,也成为不在村村民了解家乡生活、变迁的重要窗口。作为发布者的妇女,在这一实践中便发挥着传播“节点”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妇女通过发布闺蜜共同出行时拍的抖音短视频、自拍照等,形成以“闺蜜圈”为中心的线上、线下个体形象构建和印象管理,如“会玩、会生活”“生活幸福”“时尚达人”等。通过个体化的形象展演,村庄中的普通女性都能够成为乡村社会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成为自我社会关系的中心。她们在村民、朋友以及陌生人的点赞、留言中,获得心理和生理上的双
重愉悦和肯定,从而实现个体价值的彰显,完成自我赋权。
(二)网络媒介与“自由”闲暇生活的实现
闲暇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良好的休闲能够实现个体的发展,以更好的回应生活与工作。闲暇可以分为内在休闲和社交性闲暇,前者是个体能够从活动中获得乐趣,后者则是为社交进行的活动,它虽然带有闲暇的属性,但受到所处身份的限制,被认为具有义务性,无法真正实现休闲,也难以使女性获得真正的休闲体验。
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女性长期处于难以实现真正“自由”的闲暇生活的状态。一方面,如从前文对青年和中年妇女闲暇方式的选择可以看出,妇女在家务劳动、家庭发展压力之下,难以有完整的闲暇时间,只能在嵌入家务劳动或工作后选择个体化闲暇,有限缓解劳动压力。另一方面,传统农村妇女所属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结构性关系,其互动附着责任而难以实现真正的闲暇。社会交往关系主要有血缘、地缘、业缘、趣缘四种。前面三种都属于结构性关系,其交往附着于身份,如亲人、邻居、同学,这些身份使交往中伴随责任,个体需求容易受抑制,难以实现真正的闲暇。以三者中最具建构性的同学关系为例。按理来说,这一关系具有可选择性,是建立在完全自愿交往基础之上的,但其交往仍承载责任。以燕姐的同学交往为例,她在与初中同学交往时经常感到不适。首先,兴趣不契合,同学们喜欢打麻将,而她对此并无兴趣,导致她在聚会时感觉无聊。其次,在城里住的同学经常想感受乡村生活,因此经常要她接待,她认为这是“占(她)便宜”,时间一长便会产生不平衡感。但因为是老同学,她不能直接表达不满,最终只能慢慢退出圈子。由此看出,参与同学聚会从形式上看属于闲暇,却带有很强的限制性,难以真正实现“自由”的闲暇生活。在妇女步入中老年以后,她们的生活压力、家庭发展压力都减轻,闲暇时间相对增多,其在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趣缘人际关系得以被激活,能够选择适当的闲暇方式。
在趣缘基础上,以网络媒介为依托构建的闺蜜关系,使农村妇女感受到“自由”的闲暇生活。“闺蜜圈”是以共同兴趣为前提组成的,其进入、退出以及活动参与都不具有强约束性,在彼此熟悉和开放的关系中,形成低压力的交往氛围。在交往过程中,她们会聊家庭,但仅限于情感层面,绝不插手彼此的家庭事务,也不会涉及任何利益相关的事务。设置这一边界,保证了闺蜜间交往的纯粹性。在微信群中,因为“能说得到一起,我们什么都可以说”,妇女能够无所顾忌的聊天,给予她们充足的表达空间;在日常出行中,她们通过抖音获取出行信息、打折的消费信息,更换不同的闲暇活动,丰富工作之余的生活;在每年一度的外出活动中,她们借助网络的工具性,如订票、导航、信息查找等,完成对家庭生活的“逃离”,真正享受独立的闲暇时光。因此,在“闺蜜圈”这一纯粹的情感互动与休闲共同体中,女性能够真正走出家庭,实现“自由”的闲暇生活。
(三)网络媒介与个体情感的释放
妇女的情感需求是其借助媒介构建“闺蜜圈”的内在动力。对大部分农村妇女来说,其关系网络相对有限,在血缘、地缘等先赋性关系之上,妇女很难有自由表达的空间。当前,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逐渐取代代际关系,成为家庭的关系主轴,但这一潮流对中年夫妻,尤其是男性的影响有限,但女性的情感表达需求和个体价值彰显需求日益凸显,“闺蜜圈”组织及其衍生的依托网络媒介的互动,成为回应女性双重需求的重要载体。
在乡村社会中,妇女的情感表达需求经常受压抑。一方面,妇女受家庭角色的约束。在传统家庭关系中,妇女扮演的多重角色具有较强的对应责任,而其中伦理要素大于情感要素,在与公婆、丈夫的互动中都要遵循特定伦理,仅与孩子的互动具有较强的情感特征,但其回应的情感需求有限。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内部人际互动带有的血缘、地缘等关系特征,使交往过程中附着的责任属性更强,难以形成个体化的亲密关系互动,限制妇女的情感表达。
“闺蜜圈”作为纯粹的情感互动和闲暇组织,成为农村妇女表达情感、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她们能够将自己不能跟丈夫和家里人说的感情问题跟闺蜜讲,获得闺蜜的安慰和开导,排解心里的苦闷,闺蜜也会尽力调解夫妻情感矛盾,起到稳定家庭关系的功能。同样,与闺蜜的外出游玩能够使妇女走出对家庭中丈夫情感支持角色的期待,在闺蜜身上获得情感支持。另一方面,她们通过抖音拍短视频展示自我价值,她们能够娴熟的掌握抖音中拍同款、用特效、开美颜等功能,拍视频本身就体现了闲暇的本质,并在拍摄中逐渐形成新的自我认同,精挑细选后将最优质的视频上传到网络平台,获得点赞和留言能够给予其极大的心理鼓舞,并持续构建自身在虚拟网络和现实交往关系中的形象。因此,农村妇女依托“闺蜜圈”的活动,通过网络平台上的个体生活展演,进行自身情绪表达和自我意义的构建,最终实现个体价值。
五、总结与讨论
“闺蜜圈”的产生虽是农村妇女个体选择的结果,但背后隐含丰富的社会转型意涵。在社会的快速变革期,乡村社会越来越受到现代化因素的影响,网络媒介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农村妇女从自身需求出发,利用现代网络媒介拓展闲暇方式,并形成差异化的闲暇选择。中青年农村女性因家务劳动、家庭发展压力等只能选择低社交性的个体化闲暇,45~55岁的女性因处于低生活压力期而有时间、有经济基础参与“闺蜜圈”闲暇。她们在自身熟人社会关系基础上,通过网络媒介确定交往边界、丰富闲暇活动形式与范围,进而实现个体价值、“自由”闲暇生活和个体情感释放的三重赋权。
网络媒介对妇女的赋权,拓宽了妇女对闲暇生活的可选择空间,蕴含丰富的意义。在网络时代,权力并不再附着于身份等现实条件,网络中个体是平等的,能够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传递,并通过参与、表达、行动实践完成自我赋权。在“闺蜜圈”的实践中,妇女的自我赋权并不是单纯依靠网络媒介习得知识、扩大交往圈、完成情感互动,而是在自有社会关系基础上重新构建自身社会关系、闲暇实践以及自我认同,实现一种“互动性赋权”,即权力在社会关系的流动中,弱势群体依托网络媒介的去中心化等特征,赋予个体主动获取能动力量的权力。依托熟人社会关系,农村妇女能够弥合因掌握有限技术而产生的“数码鸿沟”,真正实现自我赋权。因此,从农村妇女的个体解放和乡村社会关系重建的角度出发,要充分重视网络媒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进行有意识地引导,契合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文化振兴的现实要求。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胡晓映,吕德文.网络媒介与农村妇女自我赋权——以黔东北“闺蜜圈”闲暇实践为例[J].传播创新研究,2022(02):64-76+246.
作者信息
胡晓映,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