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前沿访谈、乡村传播、经济传播、健康传播、媒介记忆、智能传播专题研究六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网络平台治理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访特里·弗卢教授》,作者许建、朱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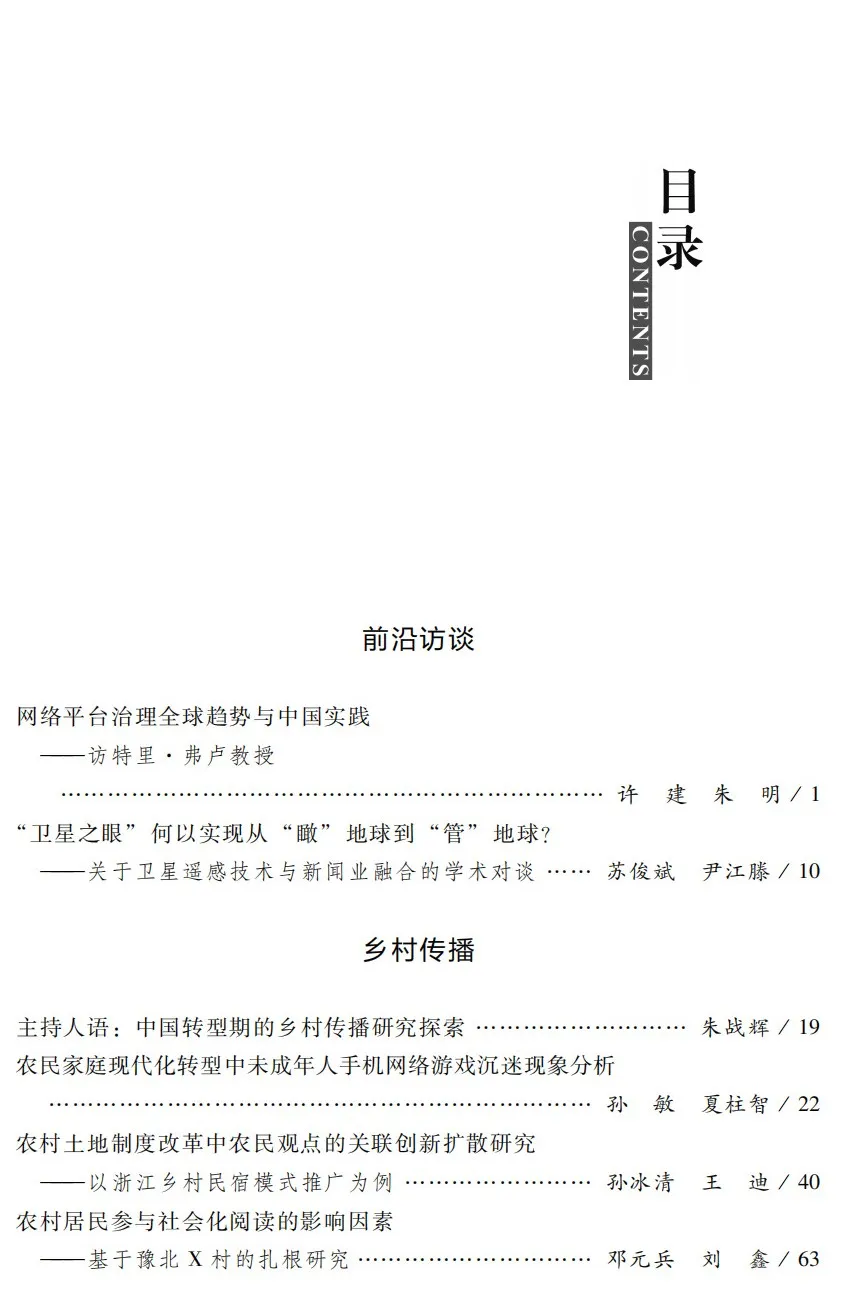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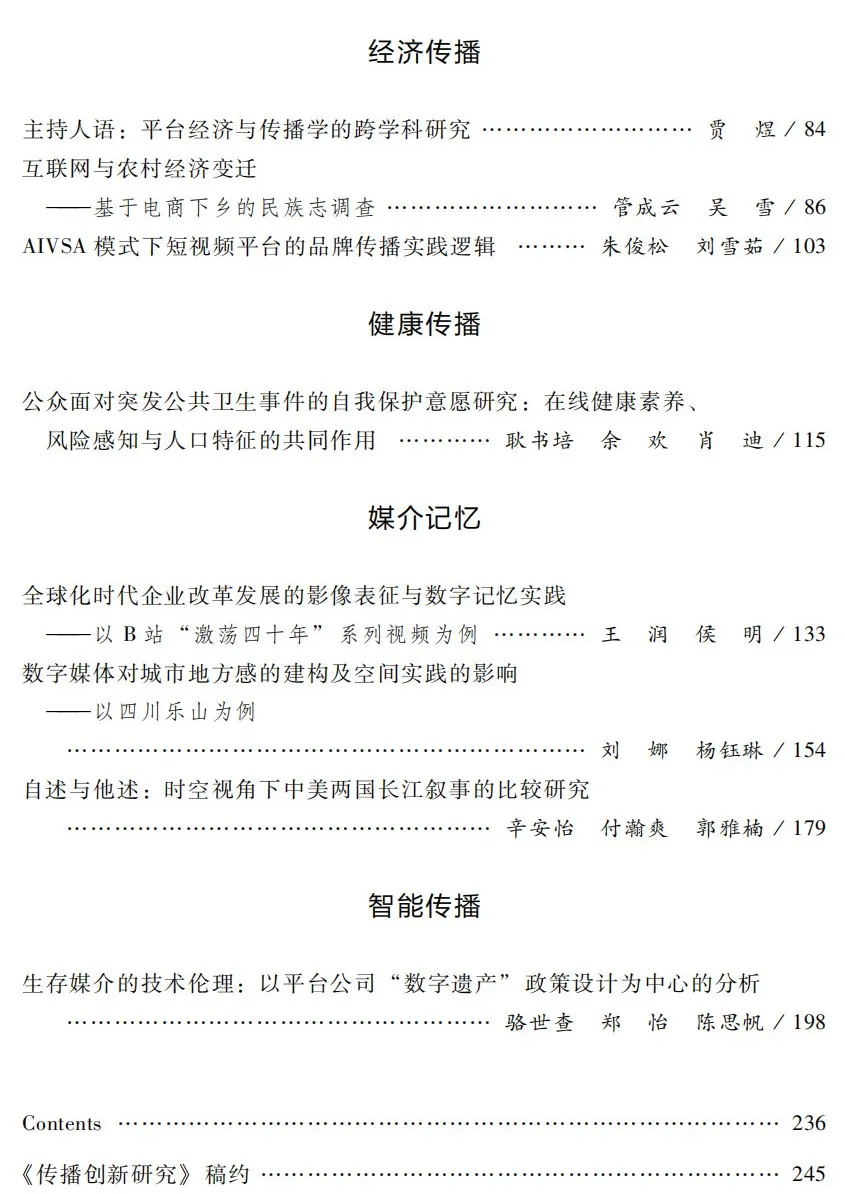
网络平台治理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访特里·弗卢教授
许建、朱明
访谈对象:特里·弗卢( Terry Flew)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数字媒体与文化系教授,是世界知名互联网研究学者。弗卢教授曾担任国际传播学会(ICA)主席(2019~2020年),目前为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并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伦敦城市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客座或荣誉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联合Sage出版的英文期刊Global Media and China副主编。其研究领域涉及数字媒体、国际传播、媒介政策法规、传媒经济、文化创意产业及互联网治理。弗卢教授已出版相关领域专著14本,代表作包括《理解全球媒介》(Understanding Global Media,2018)、《媒介经济学》( Media Economics,2015)、《创意产业、文化与政策》( The Creative Industries,Culture and Policy,2012) 和《全球创意产业》( Global Creative Industries,2013)等。其文章和著作被翻译成中文、阿拉伯语、波兰语和土耳其语等多种语言。
弗卢教授的新作《平台治理》( Regulating Platforms) 于2022年由国际知名的Polity出版社出版。该书很快成为互联网和平台研究领域的必读书目。作为第一本聚焦平台治理的英文学术专著,弗卢教授用了七个篇章系统梳理和分析了全球自由互联网的衰落、传播媒介的平台化发展、数字平台与传播政策、平台的管理与规制、平台权力和未来互联网政策,以及中国互联网和全球互联网治理等问题。书中既有对历史的回溯,也有对当前热点问题的评判性解读,内容涉及当前平台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弗卢教授认为,“治理”是数字平台的固有特性。最佳的治理模式存在于外部规制力量和平台自身治理实践的动态平衡中。平台治理政策框架的形成是媒介政策、信息政策和经济政策等多重政策融合互动的结果。随着全球大型平台企业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平台治理,全球数字平台的权力角逐也越来越激烈。
问:您好,弗卢教授!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这次访谈的邀请。首先,祝贺您的新书《平台治理》出版。这次访谈想围绕您新书里的内容和观点,并结合中国互联网和平台治理的一些问题展开。其次,想请您谈一谈这本书的写作背景、这个题目的重要性以及书中关注的核心问题。
答:非常感谢对我的邀请。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互联网,并讲授相关的课程。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很多互联网研究者对互联网的发展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甚至乌托邦式的幻想。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因为当时的互联网公司和政府都比较推崇“不受管制的互联网”( unregulated internet),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非常不同。经过了这段相对自由的发展期,全球范围内对网络空间管理的规范和法规越来越多,关于互联网治理的问题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传媒领域的学者逐渐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主力军,形成了现在的互联网研究( internet studies) 领域。在这一领域,“网络治理”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当前最受关注的平台治理问题。2016年,欧盟委员会对谷歌公司提出新的指控,指责谷歌滥用自己在网络购物方面的控制权力,妨碍公平竞争。谷歌公司也因此面临巨额罚款。这个事件使我开始深入思考平台治理问题。2018年的“脸书—剑桥分析数据丑闻”让我们看到了超级社交媒体对用户信息的控制力和数据滥用给个人隐私带来的风险。2021年,美国社交媒体巨头集体“绞杀”特朗普,再次展现了平台权力和对政治、民主的影响。这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事件,让我感到有必要写一本关于平台治理的著作。这本书主要关注传播媒体的平台化( platformization)趋势、平台化带来的问题、平台权力,以及针对超级平台的规范和治理问题。
问:“平台研究”( platform studies) 最近几年成为互联网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您能否结合这本专著谈谈您对“平台研究”的理解以及您自己研究的关注点?
答:当前,“平台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是关注具体平台的“物质性”(materiality)和“可供性”(affordance)。我的研究并不属于这一类。我更关注的是平台化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法律、伦理以及政策层面的问题。这和以José van Dijck为代表的阿姆斯特丹学派相似。我的书中并没有探讨像优步和滴滴这样具体的平台,而是关注谷歌、脸书和亚马逊这样的超级平台,因为它们是平台经济的巨头企业,可以为成千上万的平台提供关键基础设施。在中国,腾讯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平台企业。
我把“平台化”看作一种“过程”、“经济模式”和“数据驱动的资本主义”( data-driven capitalism)。平台企业和非平台企业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传媒企业目前都在逐步平台化或者已经完成了平台化,成为平台企业。越来越多的非传媒企业,比如麦当劳,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平台化的过程。当你通过麦当劳的App点外卖的时候,麦当劳就会收集你的个人信息。它如何处理和使用你的个人信息,会涉及法律和伦理问题,因此平台治理问题就变得很重要。我对平台的研究更关注的是平台化过程中出现的垄断、法律和伦理等问题以及在政策层面的应对和调整。
问:您在书中提到,“平台权力”( platform power)为平台治理提供了合法性。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平台具有哪些权力以及平台权力可能带来哪些问题?
答:平台具有“经济权力”,尤其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几个数字平台被几家全球超级企业控制,比如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和微软。这种垄断的格局已经开始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对信息的垄断强化了数字市场“赢者通吃”的逻辑,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的门槛越来越高,同时公众的选择越来越单一,更换服务商的成本越来越高。用户无法掌控平台对其个人信息的获取,存在隐私泄露等一系列风险。平台对算法的操控,直接影响用户能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哪些数字广告、新闻信息和创意内容能够被推荐,从而直接影响到数字经济创业者的收入和市场价值。
同时,平台具有“把关人权力”,可以决定什么样的信息需要被屏蔽、什么样的内容能被看到和传播。近年来,谷歌、脸书、推特等企业都经历过一系列关于假新闻、仇恨言论、错误信息的争议事件。平台可以说是“后真相”时代真正的幕后推手,影响着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哪些议题可以进入公共领域进行讨论,尤其是全球疫情期间出现的“信息疫情”(infodemic)已经对公共健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平台在“信息疫情”的产生中起到了最主要的中介作用。
平台的“政治权力”也不容忽视。以美国为例,超级平台企业定期参与符合自身需要的政治活动,成为美国政治中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说客。这种影响力不仅可以通过捐款和成为美国国会代表来获得,还可以通过其宣扬的开放、自由、创新的意识形态来获得。大型科技公司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企业游说者。传统新闻、出版和娱乐集团依然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企业经常游说政府采取行动来规范数字媒体平台。同时,对平台采取的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美国民粹主义反弹对平台权力和影响力进行限制的呼声。比如特朗普和一些政客提议拆分大型科技公司、加强对平台内容的管理,通过迎合民粹主义来获得竞选的政治资本。
在书中我总结了平台权力或者说平台垄断带来的七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们分别是隐私和安全、数字版权和保护、算法治理、错误信息和假新闻、仇恨言论和网络霸凌、信息垄断以及对其他类型媒体和创意产业的影响。平台权力或平台垄断带来的问题不仅包括我提到的这七个,还包括人工智能的伦理等。这些问题都是公众关切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公众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必要的平台治理手段来保障公众利益是十分必要的。
问:您能否具体谈一下,在平台治理的过程中,谁参与了治理?治理的模式有哪些?
答: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观点,数字平台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是平台治理的主体,三者形成了平台治理的三角关系,这种三角关系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自治”(self-governance),主要包括行业标准制定机构的成立以及平台自发地提高透明度、应对错误信息、制定政治广告标准等行为。脸书监督委员会(FOB)就是这样一个自治机构,为脸书的内容审核政策提供独立的意见。第二种模式是“外部治理”( external governance),主要指针对平台涉及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督促平台落实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法等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规范。比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德国出台的旨在打击社交网络中仇恨言论和假新闻的《网络执行法》等。第三种模式是“共同治理”(co-governance),主要指在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模式下,非政府组织通过与平台和政策制定者的对话,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共同制定政策,保证多方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三种治理模式在互联网和平台治理中通常被混合使用。
问:在您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中国互联网和全球网络治理未来。为什么您觉得中国互联网及其治理如此重要?
答:我觉得中国互联网是互联网研究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因为中国的网络生态系统与众不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中国的互联网和平台已经具有全球影响力,比如TikTok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同时中国的金融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如在无现金支付方面,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现有的英文文献中,对中国互联网的关注并不能很好地展现中国互联网产业以及互联网治理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更翔实的数据和更客观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治理思路和路径,展现中国互联网治理机制和框架的复杂性。只有了解了中国互联网,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互联网体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问:您在书中提到,反平台经济垄断是当前的一个全球趋势。最近两年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趋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平台巨头的垄断式发展。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全球趋势以及中国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措施?
答:和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相比,互联网发展的制度框架和社会对互联网平台的期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前的平台资本主义——少数几家跨国超级平台和科技巨头控制着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和数字经济市场的核心资源,已经史无前例地展现了这些垄断企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正如美国众议院在2020年提交的反对数字平台垄断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曾经生机勃勃并挑战权威的创业公司已经成为垄断公司,和从前的铁路、石油大亨并无差别。这份报告针对数字市场的反竞争行为、加强对合并与收购的规范管理、落实反垄断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不仅在美国,欧盟和英国最近两年也出台了反对数字平台和科技巨头垄断的法案和措施,比如欧盟出台《数字服务法》,来限制这些垄断企业的市场权力,试图避免一系列垄断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创新能力的降低、数字广告费的增长、服务质量的下降、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无法保障,以及新闻质量的下降。
中国作为平台和数字经济大国,近两年来也把反对平台经济垄断上升为互联网和平台治理的重要议题。2021年出台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美团等平台因涉嫌垄断被约谈或处罚,都释放了中国政府下决心推动平台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信号。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反对平台经济垄断和中国政府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政府希望以互联网行业为入口,规范财富积累,处理好财富分配问题,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可以看到,反垄断措施出台以后,中国互联网巨头越来越多地参与公益慈善,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助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可见,反对平台经济垄断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识。虽然不同的国家在反对平台经济垄断问题上有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目的,但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已经成为所有互联网和平台经济大国不可回避的议题。
问: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可以说是中国平台出海最成功的例子。但是最近两年,我们看到了不少关于TikTok的争议。TikTok在印度被强制下架,在美国也曾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险被封杀。想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TikTok作为“中国制造”的超级平台这几年被各国学者广泛关注。抵制TikTok的根本原因是,近年来“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的日益高涨。斯诺登事件加速了“技术民族主义”在全球的蔓延,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互联网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来保护网络安全。同时,TikTok事件说明了地缘政治对平台跨国发展的巨大影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美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较量,形成了新的“数字冷战”( digital cold war)格局,同时加速了全球“分裂互联网”( splintered internet) 的形成。
中国的超级平台为了跨国发展,会逐渐适应不同国家市场的政策环境,采用与其在中国本土不同的运营和监管模式。这也是大型跨国企业通用的模式,比如麦当劳在全球不同国家实行的差异化、本土化的策略。TikTok也在逐渐完善这种差异化市场模式。从TikTok的处境可以看出,未来随着全球“分裂互联网”的加剧,不只是“中国制造”的超级平台,跨国发展的超级平台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来自不同国家的规制的挑战。
问:中国政府历来主张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您觉得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会面临哪些挑战?其能否解决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矛盾和冲突?
答:首先,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并不是单一的。中国、俄罗斯和沙特等国家提倡的是“多边治理模式”( multi-lateral approach),认为国家应该在互联网治理中起最主要的协调和决定作用。这种模式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国家和西方互联网巨头提倡的“多方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 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相对立。他们认为“多边治理模式”会影响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和民主价值,因此抵制和反对这种模式。其次,即使在同一阵营,互联网的治理实践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也会不同。比如德国对仇恨言论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澳大利亚要求谷歌和脸书向澳大利亚的新闻内容付费。这些具体的规范对全球互联网企业来说是一种挑战,在不同的国家需要面对不同的法律法规。所以,互联网治理并没有唯一的标准和模式,治理的模式可能越来越多样化。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多边治理模式”提出的一种理想型的治理方案。中国作为网络超级大国,积极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并推广自己的网络治理理念。当前,互联网已经和地缘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国家与国家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理想型的治理方案,“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实施中一定会面临各种挑战。这种方案能否被普遍接受,取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国家与平台之间的博弈等诸多因素,是短期内无法预测的。互联网治理和全球气候治理一样,都不是单一国家可以完成的任务。各国都需要参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博弈、协商和影响。全球互联网治理也需要不同治理方案和路径的碰撞与协商,并不是某一个单一方案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问:您在书中指出,当前互联网和平台治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明显的“治理转向”( regulatory turn),而且国家在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中国,国家和政府一直在互联网治理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全球的互联网和平台治理在向“中国模式”靠拢呢?
答: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自由主义互联网”( libertarian internet)的理念日渐式微,“技术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我们确实看到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互联网治理。其实从互联网诞生开始,国家一直都扮演重要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宽带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推广网络素养教育等方面。2012年的斯诺登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这一事件让很多国家重新审视国家和互联网巨头的关系并重新评估自身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为了确保自身的网络安全,国家作为主体越来越多地参与互联网治理。
国家的积极参与和中国提倡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如果我们比较国家的参与形式、参与程度,国家和平台以及其他参与治理的社会组织的关系,还是会发现其和中国当前的治理模式有很大不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治理模式,但也在不断创新这种治理模式。比如越来越多地发挥平台、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所以,在“治理转向”和国家作用日益凸显的大趋势下,如何协调政府、互联网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如何发挥不同治理机构的协同治理能力,是网络大国面对的共同问题。同时,不同的治理模式也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尤其是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如何更好地起作用。
问:在中国,关注互联网和平台治理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您觉得这个方向的研究有哪些值得深入发掘的前沿问题?
答:我读过一些中国学者在互联网和平台治理方面非常优秀的英文文章,可能中文期刊的文章会更多一些。我认为平台如何跟本国政府以及全球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监管部门进行互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跨国发展的大型平台。在推动全球化战略的同时,这些平台需要适应不同国家市场的政策环境来维持可持续发展。
此外,互联网和平台治理涉及众多治理组织与机构之间的复杂的协调和互动。这种关系需要更详细的梳理和更细化的研究。比如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在互联网和平台治理中起到的作用有明显的区别,政府和其他治理组织与机构的关系也有差异,这需要我们有比较的视野和翔实的数据来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的互联网和平台治理有自己特殊的路径和模式,同时中国的数字平台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我相信中国学者一定会发掘新鲜的议题,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案例和视角。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许建,朱明.网络平台治理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访特里·弗卢教授[J].传播创新研究,2023(01):1-9.
作者简介
许建,博士,高级讲师,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传播与创意艺术学院,研究领域为互联网治理、网络文化以及名人。
朱明,硕士,哈尔滨学院党委宣传部,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