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十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情感、情绪与跨文化交流相关的一些未解问题》,作者〔瑞典〕延斯·奥尔伍德、吴雨含(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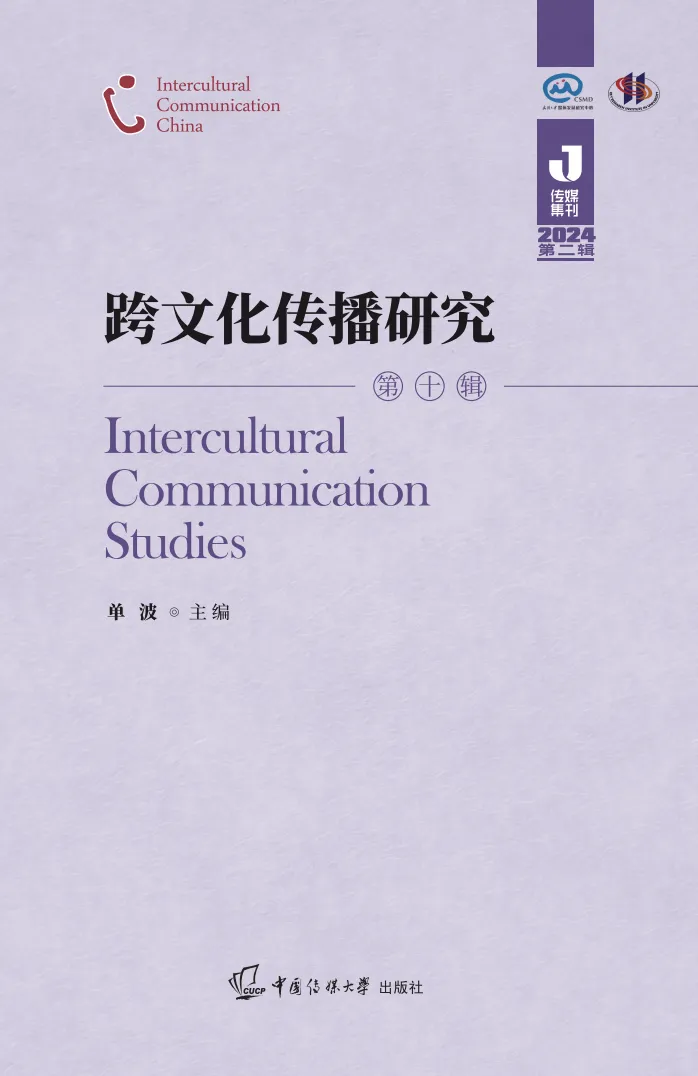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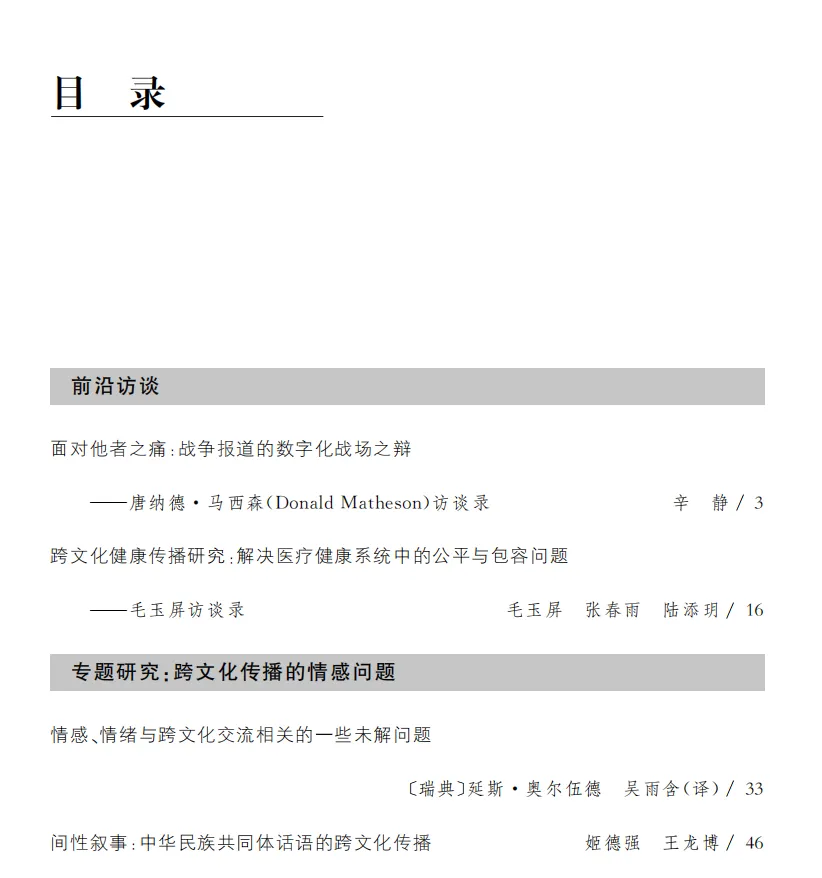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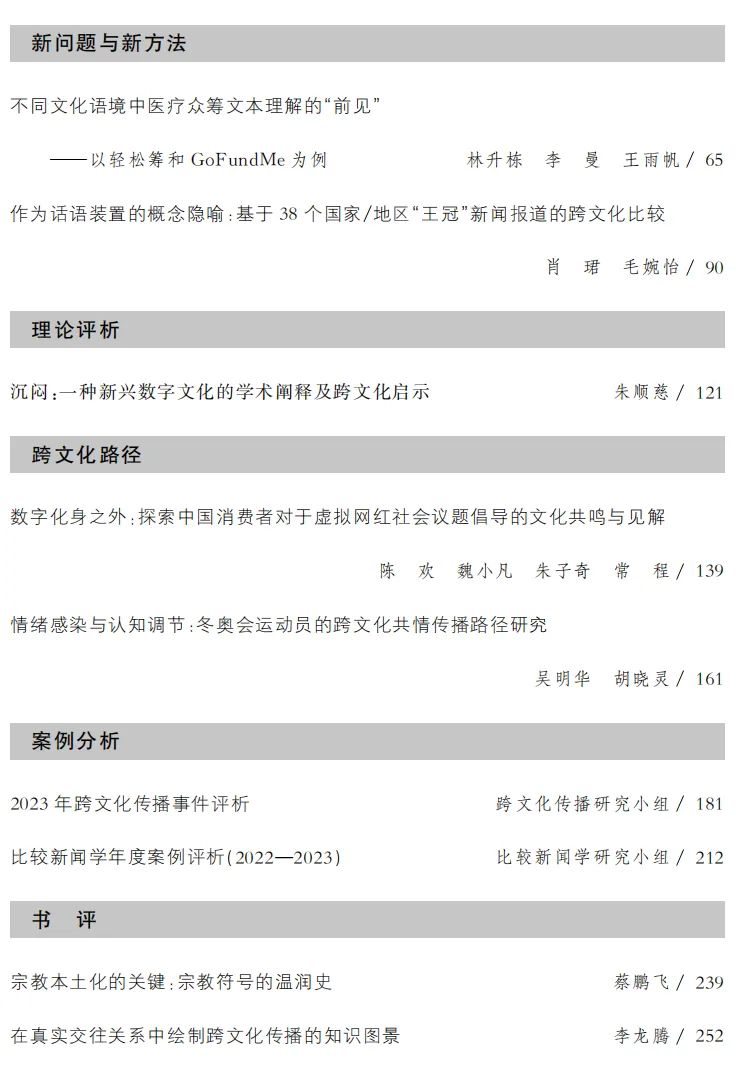
情感、情绪与跨文化交流相关的一些未解问题
〔瑞典〕延斯·奥尔伍德、吴雨含(译)
关键词:情感;情绪;跨文化交流
无论是在文化内部还是在跨文化间的交流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情感和情绪都在时刻影响着我们。然而,关于情感和情绪,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答。本文探讨了一些我认为仍有待商榷的与情感和跨文化交流相关的问题,并尝试给出一些可能的答案。
首先,从该领域的术语使用来看,各种术语的使用并不统一,目前尚不清楚“感觉”“情感”“情绪”和“情感倾向”这几个术语中,哪一个是最能概括该领域的概念。这些术语在意义和使用上似乎存在很大的重叠。此外,这些术语都难以被准确定义。或许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这些术语是家族概念(family concepts),它们两两之间可以相互关联,但并无一个共同特征能将它们全部囊括。或许它们构成了一个语义场,其维度尚不明晰。
在这些术语中,似乎“感觉”(feeling)一词的涵盖范围最广。我们可以从诸如“感觉自在”“感觉饥饿”“感觉困倦”“感觉寒冷”“感觉疼痛”等表达中看出这一点。最专业的术语可能是“情绪”(affect)(在哲学中常用)和“情感倾向”(sentiment)(在计算语言学研究中常用)。而“情感”(emotion)可能是这些术语中最具体、最中性的一个。出于历史原因,本文主要使用“情绪”(affect)和“情感”(emotion)这两个术语。
以下是我将讨论的一些未解的问题:
-
我们能否定义情绪(emotion)、态度(attitude)和情感(affect)等概念?它们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
-
情绪与交流及跨文化交流之间有何关联?
-
人类的情绪具有多大的普遍性?
-
不同文化对情绪的评价是否有所差异?
-
面对情绪与态度上的文化差异,我们应如何应对?面对相似之处,我们又该如何处理?
-
多语言使用者是否会在口述(和书写)不同语言时,关联不同的情绪态度?
-
我们应如何理解个体情绪与集体情绪之间的关系?
-
集体情绪的稳定程度如何?
-
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集体情绪?
-
是否存在情感共同体?
一、我们能否定义情绪、态度和情感?它们之间有哪些相似与不同?
现在,让我们考虑情绪、情感和态度(情绪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定义,并以偏见(prejudice)和错觉(illusion)作为态度的例子。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我认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对于情感的定义似乎仍是最好的定义之一,因此我将以斯宾诺莎在其著作《伦理学》中根据伦理和情感在人类生活和宇宙中的作用所提供的情感定义为出发点。斯宾诺莎定义了情感(affectus,传统上译为“情绪”):“我所理解的情感(affect),是身体(包括心灵)受到的影响,这些影响会增强或削弱身体的行为能力,辅助或抑制它,同时,这些影响产生出各种观念。”
《韦氏词典》(2023)将情绪(emotion)定义为一种有意识的精神反应(如愤怒或恐惧),主观上体验为强烈的感受,通常针对特定对象,并通常伴随着身体和行为的生理变化。这一定义与斯宾诺莎的定义相符,但略显狭隘。
基于这些考虑,我暂时采用斯宾诺莎启发的情绪/情感定义,即“调节(抑制、扩展和维持)精神和身体活动的内部精神和身体能量”。我们可以看出,上述三种情感定义都赋予该词非常广泛的含义。饥饿、口渴和疲劳都可以起到斯宾诺莎所描述的情感的作用(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将这些基本生理需求排除在定义之外)。这一定义与“情感在行为和认知发展中起基础性的作用”相符合,因为情感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们通常与生存相关,而这也意味着它们与运动(emotion的词源为运动)有关,即朝向或远离某个目标(战斗、逃跑)。比较一下与快乐、愤怒和恐惧相关的运动,情感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本体感觉的内部体验。表达“我为之动容”是表达你体验到了某种情感的方式。该定义指出了至少如何将基本情感与以下方面联系起来:
-
影响我们感知和理解的本体感觉(情绪驱使我们)
-
影响我们感知和理解的精神内部品质
-
态度和行为/行动——情感激励我们并为我们的行动提供能量(喜好与厌恶)
-
与情感能量相关的强度/觉醒/活动程度(潜意识-意识)
-
情感视角组织信息(情感能量)的能量基础——激活情感上相容的语境
列表中的特征不仅提供了一个普遍的基础,也提供了一种理解情感如何参与态度转变和观点采纳的方式。通过考虑关于情感地位和不同分析立场的辩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展这个列表,例如:
-
情感是身体能量、运动
-
情感是精神的(意识和潜意识)(传统观点)
-
情感是情境化的
-
情感不是具体的,而是三个维度(量表)的渐进组合,如评价、力量和活动,愉悦、唤醒和支配
-
情感是个体的
-
情感可以是集体的
除非这些观点被推向极端,例如“情绪只是生理的”或“情绪只是情境化的”,从而否认其他观点的有效性,否则这些观点看起来并不矛盾。因此,似乎没有明确的理由相信情绪/情感不能同时具备所有这些属性。相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不滑向极端,情绪/情感就可以同时具备所有这些特性。因此,在以下内容中,我将采用这种包容性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谈态度(attitude)。《韦氏词典》对“态度”进行了如下定义:①关于某一事实或状态的心理定位,例如积极的态度;②对某一事实或状态的感觉或情感。由此可见,情感与态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基本上,态度就是对于某个(心理)对象的情感,这些对象可以是状态或过程,例如,“我为你的事业(过程)感到高兴,但对你的较低薪水(状态)感到难过”。因此,我将态度纳入我们的讨论中。为了举例说明情感、态度和信念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我将提出关于偏见和错觉的定义。
偏见是对某事/某人的错误负面信念,而错觉是对某事/某人的错误正面信念。偏见和错觉与情感的联系是间接的。我们对持负面信念的事物大多持有负面态度,例如“不喜欢”;对持正面信念的事物大多持有积极态度,例如“喜欢”。但这两个例子主要表明的是,信念、态度和情感往往形成一个整体,并在下一步与行动联系起来。这正是经典的“将态度描述为认知、情感和意志(意愿和意图)特征的复合体”这一描述的基础。
如果我们相信情感词汇基于潜在维度构成了一个语义场,那么我们可能会好奇这些维度是什么。例如,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提出了三个维度:评价、潜力和活动;阿尔伯特·梅拉比安(Albert Mehrabian)提出了愉悦、唤起和支配,其中,愉悦与评价相关,活动与唤起相关,潜力与支配相关。然而,关于这些以及其他类似提议的争议很多,似乎还有概念性的工作要做。如果我们在主要的情感术语中加入情感性和态度性的术语,如偏见和错觉,我们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与斯宾诺莎对情感的定义(以及奥斯古德和梅拉比安的定义)一致的另一个特征是,大多数情感都可以以不同的强度/唤醒度/活动度来体验。强度的变化或许也与情感意识程度的变化有关。情感似乎在一个从无意识到潜意识再到意识的连续范围内变化,所有层次都会影响我们的体验。情感似乎也与基于情感组织视角的信息能量基础有关。我们调动情感能量来激活情感上兼容的情境。想象一下一只猫或一所房子(也许再加上音乐的强化),当你恐惧、高兴、愤怒、悲伤、惊讶或谨慎时,注意你体验到的不同感受。同样地,再考虑你对一篇待审文章的印象——当你持积极态度时(你会忽视缺点)、持消极态度时(你会关注缺点)、持中立态度时,或者充满热情、兴奋时。通过视角的选择,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感知和理解。
情绪能够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而且这些情绪可能是潜意识的,这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如何被我们所组织和加工的。我们可以思考光学错觉图像中从鸭子到兔子、从老妇到少女的视角转换,或者物理学中从粒子到波的视角转换,并思考情感能量是否参与了视角的选择。我们还可以思考视角如何激活语境,并激发我们在不同情绪(愤怒、暴怒、恼怒、心烦、生气)的语义领域中找到基本情绪的许多语境变化。除了对感知和理解起作用外,情感和情绪在参与群体活动和互动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要阐明这一点的细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我将转向情感/情绪与跨文化交流相关的若干问题。
二、情绪与交际和跨文化交际有何关联?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考虑所涉及的术语的定义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从定义“交流”(communication)开始,将其理解为“理解/信息/内容的共享”,这种“共享”基于交流者所采取的物理和心理行动。接下来,我们将“理解”定义为“在输入信息与存储的背景信息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现在,我们将这一定义与斯宾诺莎对情感(情绪)的定义相结合,即“情感是身体(包括心灵)所受到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增加或减少身体行动的能力,帮助或限制身体行动,同时,也影响我们对这些情感的认知”。结合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跨文化交流是涉及具有不同国家/民族背景的人之间的共享理解的一种交流类型,这要求跨文化交流者采取行动来共享输入、联系和背景。因此,情感/情绪也可以增进或削弱、促进或限制跨文化交流。如果情感是友好的、普遍的,并且具有共同的背景,那么共享过程可能会更加容易。研究情感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时,可以结合爱、友谊、合作、战争、冲突、竞争等情境来探讨。现在,让我们转向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从普遍性开始。
三、人类的情绪有多普遍?
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在1992年提出,愤怒、厌恶、恐惧、快乐、悲伤和惊讶这六种情绪的表达在所有人类文化中都可以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尽管还有许多文化尚未被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观点似乎是正确的。
然而,即使所有人类都可以通过哭泣来表达悲伤,也并不意味着悲伤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表达,或哭泣总是表达悲伤。事实上,艾克曼(以及其他人)所提到的情绪在哪些场合被认为是合适的表达,在文化上差异很大。例如,关于男性成年人在哪些场合哭泣是合适的,这一点在不同文化间就存在很大差异。由于这种差异,跨文化交流培训应该大量涉及对情绪表达在情境适宜性方面的文化差异上的了解及其处理方式。如果你遵循情绪的情境理论,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
另一个与情境适宜性差异有关的问题是,在情绪评估和情绪表达方面是否存在文化和历史差异。由于这似乎是确实存在的,我们也可以假设积极评价可能与情绪及其表达的出现频率更高有关。因此,在更多场合表达这种情绪,甚至体验这种情绪,就变得合适了。这种差异可能体现为“安全”和“保障”在当今社会中受到积极的评价,而在过去,“挑战”“勇敢”“好斗”等特质比安全和保障更受重视(在某些社会中仍然如此)。与此相关的是对冒险行为的评价差异,参见科尼亚(Cornia)、德雷塞尔(Dressel)和菲尔(Pfeil)的研究。
关于情境适宜性差异的第二个例子是沟通中对“不伤害”与“不撒谎”的不同偏好。是说出真相而冒着伤害他人的风险更好,还是避免批评并虚伪地恭维他人更好?在哪些语境中、在什么程度上选择这两种行为中的一种,各文化间的情况各不相同。
第三个例子涉及文化上公认的情感词汇方面的差异。对于艾克曼的六种基本情绪(愤怒、厌恶、恐惧、快乐、悲伤和惊讶),我们都可以在许多语言(也许是所有语言)中找到一个语义场,其中的每种情绪都有许多同义词。以包含“愤怒”这个词的语义场为例,在英语中,我们可以找到诸如激烈的敌意(acrimony)、狂怒(fury)、愤慨(indignation)、怒火(ire)、恼怒(irritation)、易怒(irritability)、暴怒(rage)、怨恨(resentment)、急躁的脾气(hasty temper)、易怒性(choler)、激动(conniption)、生气(dander)、烦躁不安(distemper)、怒气(huff)、激怒(infuriation)、易怒性(irascibility)、痛苦(soreness)、发脾气(tantrum)、小争执(tiff)、烦恼(vexation)、愤怒(wrath)等术语。通常,一个情绪可以有多达20个近义词,这是希尔斯(Hirsch)在研究英语中的“恐惧”和瑞典语中的“glädje”(欢乐)时发现的规律。然而,即使一种语言有表示艾克曼六种基本情绪的词汇,我们对比不同语言的语义场时,也会发现它们并不相同。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大量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第四个例子与人们常说的“情商”有关,戈尔曼(Goleman)将其定义为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和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以及在与他人交往时表达自己情绪的能力。不同文化对适当情绪的要求以及语言所支持的情绪范围各不相同,这意味着对情绪的敏感度和情商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一种文化中的情商可能并不等同于另一种文化中的情商。
综上所述,对于“人类的情绪有多普遍?”这一问题,我们发现,尽管通过身体动作表达情绪的方式似乎具有普遍性,但这种表达方式的适用情境却随文化而异。这种差异还受到对情绪本身及其表达方式评价不同的影响。受到高度认可和重视的情绪可以在更多情境下得到适当表达。我们比较基本情绪词汇周围的语义场时会发现,文化和语言差异似乎也非常普遍。这可能导致“情商”具有文化特异性。
四、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情感和态度上的文化差异,又该如何应对相似之处?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哪些情绪被视为积极,哪些情绪被视为消极,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在中国,保全“面子”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要顾及他人的感受和社会地位(不伤害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人们不说真话。而在瑞典,人们在“面子”方面的考量较少,更愿意公开说出真实但具有批判性、可能损害对方面子的话。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瑞典与中国的合作项目中出现误解。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时,通常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承认差异并展开讨论,尤其是当这种问题多次出现时。在处理相似之处时,这种开放的态度或许更加重要。因为沟通的目的是分享理解,而分享往往意味着存在相似之处,所以承认和强调相似之处并展开讨论,往往是个好主意。
五、多语言使用者在使用不同语言进行口头或书面表达时,是否会关联不同的情感态度?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语言使用者有时会发现,他们在使用不同语言进行口头或书面表达时,会关联不同的情感。例如,有些人声称,他们使用语言A进行口头或书面表达时,会感到比使用语言B更自由或更受束缚。另一些人则表示,比起使用语言B,使用语言A进行口头表达时,他们更愿意冒险。参见凯萨尔(Keysar)、海亚卡瓦(Hayakawa)和安(An)2012年的研究。①因此,多语言使用者在使用不同语言时,会关联不同的情感态度。这种差异可能与我们使用该语言的经历、使用该语言所能实现的目标,以及我们如何、为何学习该语言有关。
六、我们该如何理解个体情感和集体情感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情感和情绪既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个体可能会感到恐惧,而一个集体同样也可以。当足够多的人开始体验和表达同一种情感,并开始相互影响时,个体情感就会转变为集体情感。如果共同分享这种情感的人还按照这种情感来行动,那么,这种情感的力量就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集体情感可以在不同程度的意识上产生,从潜意识到意识。一旦集体情感形成,它就会以意识和潜意识的方式影响个体。集体情感与个体的情感和行动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既体现在改变情感上,也体现在维持情感上。集体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同类型的沟通产生的。集体情感可以自下而上地产生。有时,它们只是在面对面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并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我们可以将后一种情况称为“情感传染”——情感通过接触传播,例如谣言、情绪。多个人对某件事产生相似的反应,并影响其他人,这就是情绪感染——情感的流动和传播。集体情感也可以自上而下地产生,例如通过广告或国家政治宣传(内部的或外部的)。有时,集体情感是由外部媒体(如报纸、电影或书籍)引发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流行的情感都可能发生变化。例如,个人和社会可能会从恐惧转变为愤怒。这种情感变化可以是短期的(例如:受惊的群众、挑衅的群众、节日气氛、时尚变迁、政治集会),也可以是长期的(例如:政治倾向)。
七、集体情感的稳定性如何?
如前所述,集体情感可以相对保持稳定,也可以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长期稳定和短期稳定,以及长期变化和短期变化。长期的稳定和变化可以通过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来保持,也可以通过语言(词汇的语义场、隐喻、谚语)、忠诚和其他习俗来保持。以瑞典为例,关于勇气的说法有“lyckanstårdendjärvebi”(幸福支持勇敢者),而反对炫耀的说法则有“tommatunnorskramlamest”(空桶响声大)。集体情感也可能与中期的稳定和变化有关:瑞典关于礼仪、移民、中立性等政策的变化发生在2到10年的时间段内,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政治极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往往会对另一方产生偏见,对自己的一方产生幻想——这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短期的稳定和变化的例子有很多:突然出现的威胁,如一名持枪男子闯入聚会时现场的气氛变化,又如时尚变迁、政治倾向、政治集会、惊恐的群众、挑衅的群众或足球迷的热情等。所有这些变化都可能在几小时、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发生。很明显,长期和中期变化将会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影响跨文化交流,但短期变化的影响却更难预测。
八、集体情感是否存在不同的类型?
谈到集体情感,我们可能也会好奇:是否所有的情感都可以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呢?我们可能还会好奇,是否所有的情感都能以相同的程度与稳定和变化的时间速率相关联。例如,快乐、恐惧、悲伤、愤怒、自豪、喜悦、厌恶、好奇、惊讶,这些情感中,哪些可以是个体的?哪些可以是集体的?哪些是稳定的或变化的?哪些是长期的、中期的或者短期的?我的看法是,列表中的所有情感都可以是个体的或集体的,但对于集体的好奇和惊讶来说,长期的稳定或中期的稳定可能较为困难。
九、是否存在情感共同体?
“情感共同体”这一术语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它可以指一个共同体通过共同的情感(如忠诚、团结、群体利益或恐惧等)来维持和凝聚其成员,这些情感有助于保持共同体所依赖的凝聚力。这可能会导致诸如民族主义、地域主义或爱国主义等情感的出现,从而有助于维护共同体。另一方面,它可以指一个共同体维持某种特定情感的现象。在第二种情况下,重点是共同体维持一种情感,而不是像第一种情况那样,情感维持一个共同体。与第二种含义密切相关的是集体情感的长期稳定性问题,以及哪些情感可以被长期维持的问题。
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共同体是否能够维持某种集体情感?如果可以的话,又是哪些情感?我们能否想象快乐的共同体(文化)、友善的共同体(文化)、敌对的共同体(文化)、好奇的共同体(文化)、紧张/挫败的共同体(文化)、恐惧的共同体(文化)、夸张与反讽的共同体(文化)?如果可以的话,这意味着我们也应该能够谈论情感文化,例如快乐或悲伤的文化。由于这个问题可以启发大量的研究,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如果一个共同体能够维持积极的情感,那么这对跨文化交流和人类合作来说,就充满了希望。
十、结语:情感、态度与情绪是如何与跨文化交流相关的?
在本文中,我认为情感(情绪)会影响跨文化交流。根据斯宾诺莎对情绪的定义,情感会“增加或减少、促进或抑制”跨文化交流。我也认为,如果情感相似且友好,跨文化交流就会得到促进;反之,如果情感不同且不友好,跨文化交流就会受到阻碍。通过比较情感在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在爱情、友谊、合作、战争、冲突、竞争等情境中的作用,总的来说,我认为即使情感存在差异,但只要交流者能够意识到这些差异,跨文化交流也能得到促进。当交流者的情感相似且友好时,这种促进作用可能更加明显。基于情感在人类生活和交流中非常重要的假设,我讨论了一些关于其本质及其在交流和跨文化交流中所起作用的未解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也给出了一些有关答案的初步想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尚待解答,这也使得该领域成了一个有趣且重要的研究领域。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延斯·奥尔伍德,吴雨含.情感、情绪与跨文化交流相关的一些未解问题[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4(02):33-45.
作者简介
延斯·奥尔伍德(Jens Allwood),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电子邮箱:jens.allwood@ait.gu.se;
吴雨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2022201030036@w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