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健康传播、乡村传播、传播与社会、国际传播、智能传播五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偶像符号意义探析——以综艺节目〈种地吧·少年篇〉》为例》,作者:解芳、张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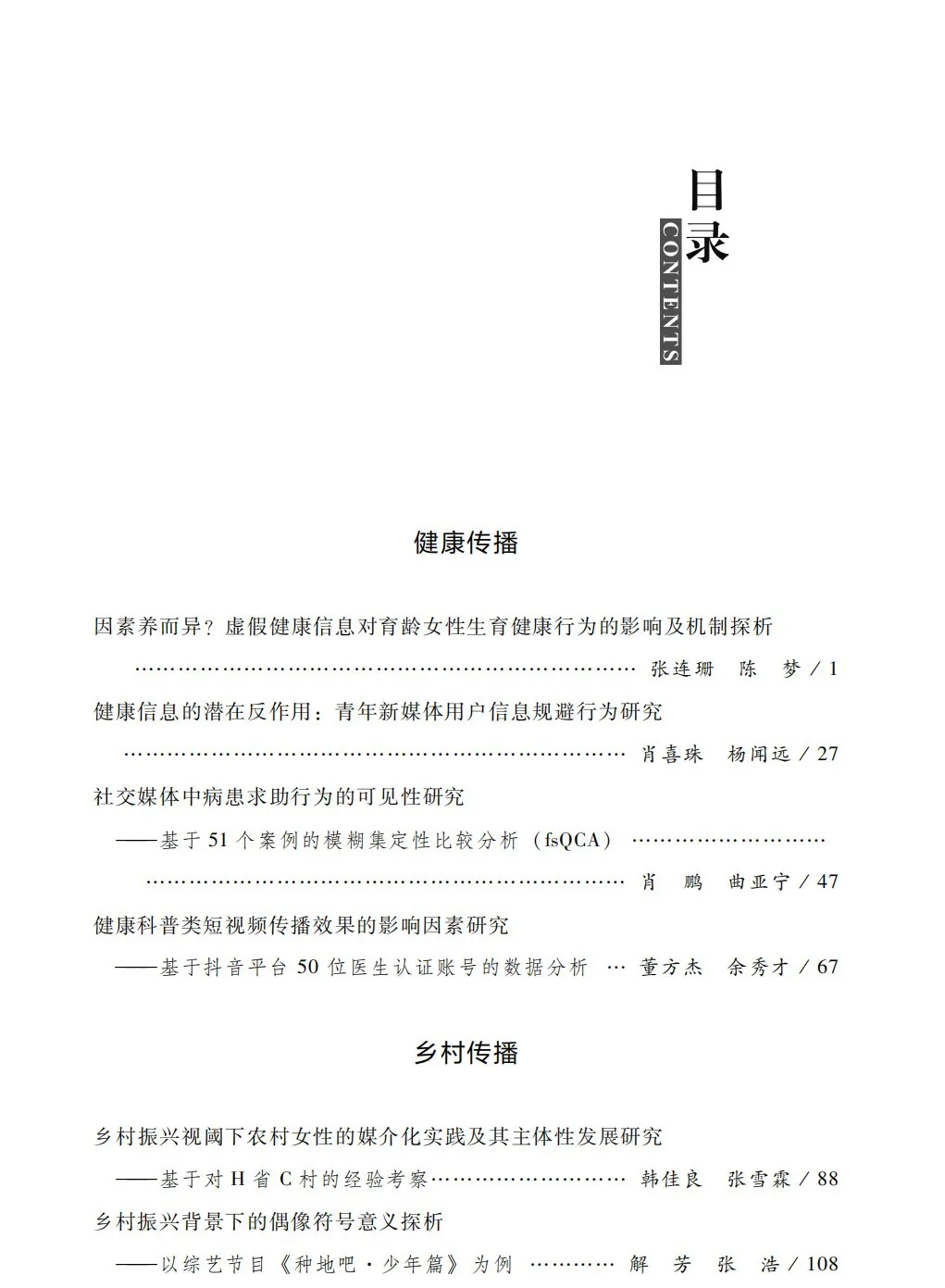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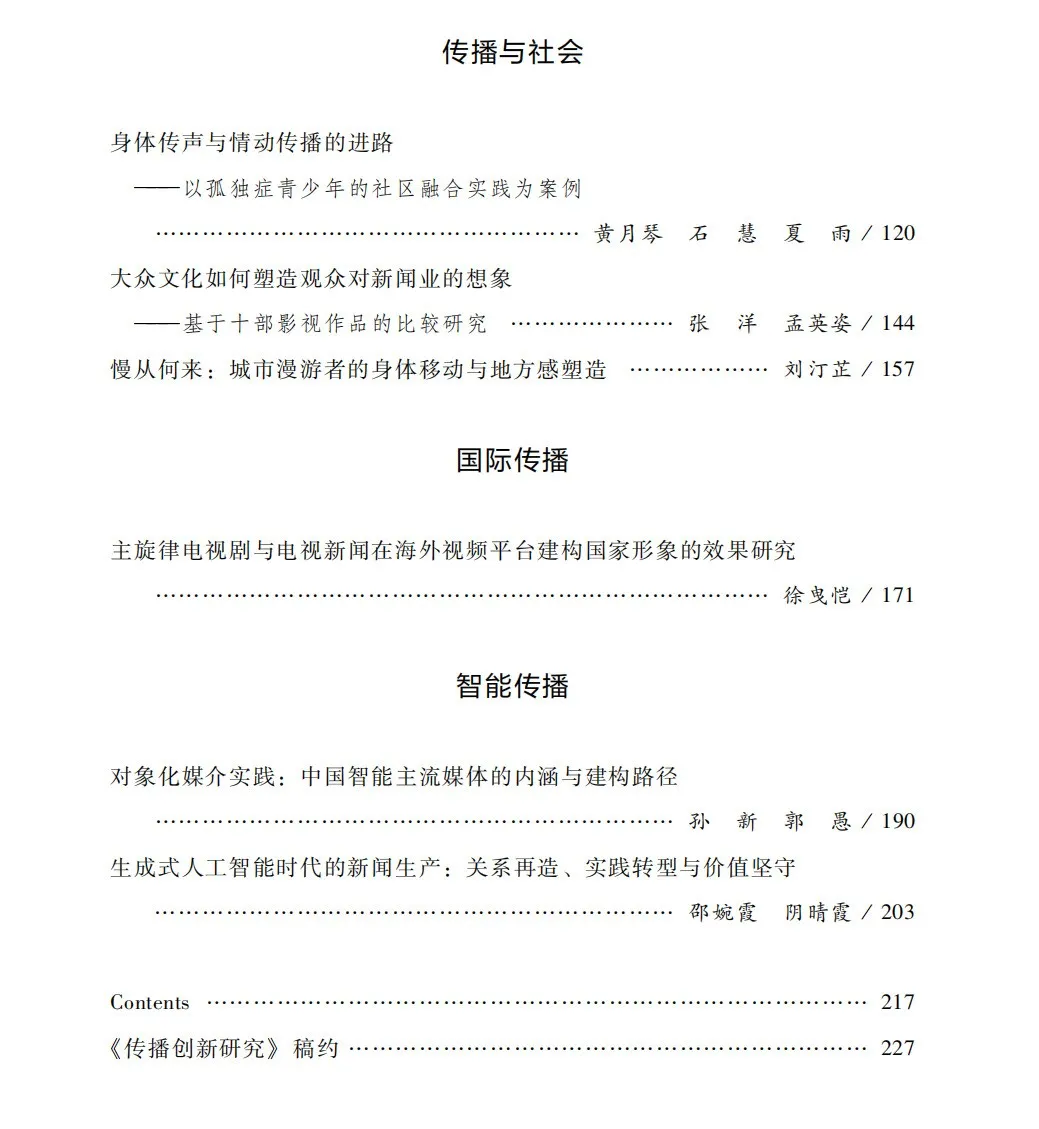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偶像符号意义探析
——以综艺节目《种地吧·少年篇》为例
解芳、张浩
摘要:乡村振兴被视为构建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涉农综艺节目则以其赋能乡村叙事的特性,不仅促进并宣扬了真实的农村生活,也深化了观众对乡村的关注。《种地吧·少年篇》这一涉农综艺节目以少年参与农业活动为叙事背景,开辟了综艺节目表现的新领域。本文借鉴符号学的理论,以参与该综艺节目的十位少年为案例,深入探讨涉农综艺节目中偶像意义滑动的符号机制,揭示其符号价值在当前社会中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符号;乡村振兴;少年;涉农综艺节目
一 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推动共同富裕进程的宏伟背景下,乡村主题成为文艺创作的焦点。在这一战略环境的影响下,综艺节目的叙事内容开始转型,掀起了以涉农题材为核心的热潮。截至2024年1月,共涌现出7档涉农类综艺节目。其中,《哈哈农夫》作为一档明星涉农真人秀备受瞩目,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了以《耕耘纪》为代表的素人涉农真人秀。涉农综艺节目强调对真实乡间生活的体验,在综艺节目的外衣下,蕴含着对生活本身的关注,满足了当下社会的情感需求。
于2023年初在爱奇艺独播的涉农综艺节目《种地吧·少年篇》(以下简称《种地吧》),一经播出便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新华网、光明网、国家广电总局等权威媒体和机构先后对其进行报道,还在观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豆瓣评分也一跃达到8.9分。节目的爆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涉农类真人秀综艺节目的蓬勃发展。由该综艺节目引发的收视热潮以及有关乡村文化等社会焦点议题的讨论,为本文提供了切实的研究基础。该综艺节目中的十位少年顺应节目组和社会需求,呈现不同于其他类型综艺节目的新形象特质,打破了传统的偶像符号意义。本文聚焦涉农综艺节目偶像符号意义的变迁历程,并关注新意义的生成对当下社会的实际影响。
二、偶像,作为符号的象征
早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便将科学划分为物理学、实践学和符号学(semeiotike),并将符号学视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两个世纪后,符号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从不同角度探索了符号学的研究方法,这标志着当代符号学的兴起。索绪尔从二元对立的角度解释了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存在,他认为,任何符号都由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构成。而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则超越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限制,提出了更为广泛的一般性理论。皮尔斯认为符号是多样的,并将符号划分为肖像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
皮尔斯认为象征符号是众多符号中的一种,“所谓象征符号是被符号的解释者如此理解或解释的符号”。他指出大多数语言符号属于象征符号,它们的符形和符指之间存在任意性,这与索绪尔的符号理论相呼应。
象征作为一种符号,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确立。他认为,“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然而,在单纯的符号中,意义与其表现之间的联系纯粹是随意拼凑的”。然而,我们认为,从符号学的角度深入探讨象征意义的生成过程发现,象征符号的意义生成是在一定框架内进行的,并且意义存在分层的情况。换言之,象征符号的意义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指出,符号意义是在内涵系统中产生的。“我们可以说,内涵系统是这样一个系统,它的表达层面本身由一个意指系统组成。”运用巴尔特的意义框架来解析象征符号,我们发现,直接意义层面是象征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初步结合,在自然或文化因素的指引下,直接意义成为内涵意义层面的能指,而随之而来的其他意义才构成了象征意义。
从对符号学的理解出发,偶像本身就是一种象征符号。李启军教授指出,“明星作为符号并非一般性符号,而是特殊的象征符号。它不是纯粹的抽象语言符号,而是具象的想象符号。它不是一般的形象符号,而是属于个体的偶像符号”。当我们接近不同的偶像时,他们会成为某些特定社群的代表,从而展现出不同的指向性。正如美国学者迪利(John Deely)在《符号学基础》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事物从符号开始,同时所有的符号可以反映事物。因此,偶像在社会中被赋予了新的寓意,代表不同群体的不同感知,最终转化为一种具有语义功能的象征符号。这表明偶像的意义都指向外部世界的某种事物,在构成自身幻想的同时也指称世界,最终使偶像成为具有语义功能的象征符号。
三、涉农综艺节目中偶像符号意义的滑动
一般来说,综艺节目的意义是由具体的情节内容所建构的。涉农综艺节目将少年体验乡村生活作为核心叙事,在满足大众对偶像群体追寻需要的同时,再现真实的中国乡村生活,传达出当下社会对乡村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注。
“偶像”作为媒介文本建构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贯穿节目叙事的始终,他们的意义是在这些特定的叙事文本之中产生的。偶像符号意义必须契合节目本身的定位与意图,而综艺节目内容的更迭影响其意义的生成,这也导致偶像由综艺节目而生成的意义与其之前已经形成的符号意义发生偏差,出现意义转向的现象。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中各类信息作为符号的伴随文本,对偶像符号意义的叠加起到关键性作用。偶像符号在综艺节目文本中的表意是社交媒体意义的基础,在互联网的多级传播的作用下,逐步衍生出新的偶像符号意义,影响大众对意义的解读,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符号的意义。
(一)涉农综艺节目叙事文本的表意
在当下娱乐主导综艺节目的时代,节目在选择嘉宾和主题时难免会呈现常规化的趋势。通常情况下,综艺节目会按照既定的偶像形象进行信息编码,以娱乐性、戏谑性、矛盾冲突和视觉吸引为主要原则。这种趋势导致偶像符号在综艺节目叙事中所呈现的意义不可避免地具有同质性。《种地吧》之所以成功引发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呈现了与传统综艺节目不同的叙事方式。在这档节目中,少年们不仅科普了农业知识,也展现了对农耕文化的敬畏之情。十位少年展示了当代年轻人“重新回归田间农活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而打破了“人们对农村的固有认知,完成了对农村形象的意识重建”。
作为一档涉农综艺节目,《种地吧》用情感叙事代替了传统的娱乐叙事,再现了“强国必先强民,农强方能国强”的深刻内涵。这样一来,综艺节目在向大众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履行了作为文本的职责。“文本不仅仅指自然语言写成的文字作品,任何一个被赋予了完整意义的客体都是文本。”综艺节目作为典型的符号文本,承载了偶像的多重象征。《种地吧》以十位少年在农村生活劳作为背景展开叙事,着重描绘他们在田间干农活中的具体场景,生动再现了农人们所处的真实的艰辛环境,打造勤劳者的形象。在节目中,十位少年参与水稻收割、排水渠建设、重达30吨的化肥搬运以及超过4000盆玫瑰的种植等一系列农耕活动,全面展现了农耕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动再现了他们从不稼不穑到逐步自力更生的生产历程。
在传统综艺节目中,满足大众娱乐需求是主要目标,然而,在对实际节目意义的研究中,综艺节目的叙事性常常被忽视。《种地吧》与快综艺节目不同,不仅注重收视率,而且从一开始就弱化了对十位少年身份的介绍,将大篇幅的叙事内容放在农作上,突出了节目的种地主题。导演杨长岭曾公开表示,整档节目是以中国农民的发展现状为最初意义导向制作的,这一首要条件决定了综艺节目叙事的走向。
基于这一定位,十位少年暂时放下原有的艺人身份,取而代之的是被赋予的农人身份。他们用200天的时间耕耘了142亩土地,以汗水和心血将“种地”变成新潮流。从皮肤白皙到被太阳晒得又黑又瘦,他们外貌的变化展现了一种踏实肯干的形象,与当下社会所传播的脚踏实地、干好一件事的正能量相吻合。十位少年将自己的年轻形象融入乡村农人的辛勤劳作形象中,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偶像形象。
在节目中,十位少年都取得了拖拉机和收割机驾照,并接受了系统的技能培训。随着节目的播出,他们学会了使用无人机和旋耕机,实现了科学农作,在技能更新的同时提高了效率,展示了现代农人的智能劳作。此外,他们创立了十个勤天(杭州)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财务、管理、销售等公司运营模式应用于农业领域,强调了中国现代农村从靠天吃饭到实现一体化农业生产与销售的转变。尤其在营销模式上,网络直播作为新兴方式备受十位少年青睐。在第38期的直播中,他们研究了直播带货,在首次直播中,竹笋仅上架一秒钟就被抢购一空。该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超过100万人次,同时在线人数最高时达72125人。进行第二场直播时,超过300万人次观看,限量售出1000盆玫瑰花。从智能种地到直播带货,十位少年不仅改变了传统农民形象,也赋予这一群体更多的可能性。
少年作为综艺节目叙事的表演者,在参与综艺节目的过程中对文本意义进行了深化,将有形的外在意义内化为无形的象征意义。他们的表意过程是在聚合轴和组合轴的动态关系中逐步显现的。组合轴决定了文本组成的方式,而“聚合轴的组成,是符号文本的每个成分背后的所有可比较,从而有可能被选择(有可能代替)的各种成分”。作为《种地吧》的意义呈现工具,少年们所产生的象征意义是双轴结合的结果。综艺节目将他们定位为农人,其外表、语言、举动等化为偶像符号意义表达的载体,在双轴的作用下,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执拗肯干的赵小童,统筹协调的蒋敦豪,温和善良的赵一博,经验丰富的李耕耘……这些不同的形象构建了多样化意义,呈现了中国当下农人形象的转变。
这种转变为偶像符号注入了新的意义。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自我呈现理论的角度来看,在社会交际中,人们总是能通过对不同的角色进行演绎来加深别人对自我的印象,逐渐形成一种特定的形象,而这种演绎过程就被称为“印象管理”或“自我呈现”。十位少年借助综艺节目文本实现了“自我呈现”。这种自我行为展现了少年塑造新农人形象的动态过程。一般来说,传统的农人群体是互联网时代的失语者,他们不善于借助现代化事物来进行自身的宣传。而十位少年作为新农人的代表,在新兴技术下不仅完成了农业宣传,也在满足城市人群对乡村人群想象的同时,让农人群体摆脱了之前的境地,获得了身份的认同感。
《种地吧》中的十位少年在综艺节目文本叙事的赋能情境下,从单纯节目中扮演的角色内化为新农人群体,在社会话语的影响下,建立了一种自我认同,激发了自身的权利意识,完成了自身形象的展示,也让社会大众打破了对偶像群体的刻板印象。这也激发了社会群体对这一特定群体的集体认同感。偶像符号意义滑向了新农人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意义随着文本叙事经过了一个渐变历程:偶像不再是大众的美好想象,在涉农综艺节目叙事文本中,少年在劳作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呈现,展现了作为坚韧踏实的劳动者、善于探索的学习者以及社会价值的宣传者等多元化的新农人形象。
(二)媒体平台助力偶像符号意义的叠加
偶像符号意义是在一定的规约性下形成的,并在文本的作用下进行表达。然而,“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如果将文本作为中心,那么伴随文本就是辅助信息接收者对于符号文本的理解。
就《种地吧》而言,节目本身为偶像符号的核心文本提供了场地,由节目引发的大众对于偶像符号的讨论也就成为其伴随文本诞生的场所。粉丝、大V、官方宣传以及其他明星等发布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都可以被视为偶像符号的伴随文本。伴随文本在综艺节目文本的基础上将偶像符号意义丰富化,以文字、视频、图像等不同的形式进行多渠道传播,以增加偶像符号意义。
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为十位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场地。以微博平台为例,直至2024年1月,节目的官方微博粉丝数量达到104.6万人,与节目刚结束时的粉丝数量相比,其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不仅如此,而且“十个勤天”作为少年们所成立公司的官方微博,在2024年1月的粉丝数量超过75万人。无论是“种地吧”还是“十个勤天”,其都成为节目的主流信息来源,在大V、其他明星以及粉丝的转发过程中完成了信息的二次传播。如果说官方微博面向节目的直接受众,那么,二次传播则是在其他账号的帮助下,让信息进入不同的粉丝群体。网络的评论与转发是无止境的,在大众参与帖子的建立、转发或者评论等过程中,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发出者,媒体与使用者之间建立了用于传递信息的话语平台,解构了偶像符号意义由经纪公司等少数人进行编码的时代,也为新的意义形成提供了范式。2023年6月12日,“#李耕耘#”凭借超高的人气和有趣的发文,冲上了微博热搜榜单第一。观众的参与让李耕耘的形象不断增加,其逐渐被贴上“糙汉”“嘴硬”“脾气倔”等标签。更有粉丝把李耕耘与榴莲结合,认为他是“外表有刺,内心柔软”的代表,李耕耘也从节目中新农人形象转变为当下认真踏实的年轻人的代表。由此,在经过不同群体的参与后,偶像符号意义从单线传播进入不同圈层中传播,也证实了鲍德里亚所说的“这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解放符号的统治,所有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弄符号”。
除了对帖子的转发和评论外,网络媒体的发展也为用户群体提供了观念思想输出的平台。大众将视频、图片重新进行剪辑制作,形成二次创作。以视频平台哔哩哔哩为例,截至2024年1月,二次创作的视频数量已超过1000个。二次创作对原始视频中的少年重新编码,对少年形象进一步传播。这些二创视频是特定群体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对主流文化的重组。不同题材的制作引发不同群体的高度共鸣,特别是为当下各种亚文化群体的发声提供了平台。在媒体平台的帮助下,视频的重新制作极大程度赋予群体之间交流互动的可能性。二创视频重新编码了少年的内在含义,偶像符号成为群体自我表达的方式,让其意义再一次得到转变。这时,伴随文本提供的语境使偶像符号原有的意义偏移,形成了新的意义。
大众在接受了综艺节目所表现的偶像符号后,依靠不同的网络平台进行快速传播,让更多的人成为节目的受众。这样一来,个体之间因同一综艺节目增加了联系,促进了网络互动。与此同时,二次创作增加了偶像符号的传播路径,偶像不再仅仅具备在综艺节目中展现出的乡村符号的意义,更转变为一种社群的认同和表达。从微博帖子到二创视频,偶像符号意义逐步扩大,成为各类年轻群体的象征。在偶像符号的重新解构中,各平台的发展带动了当下的伴随文本的产生,而伴随文本的参与和日渐偏重使意义具有多元性。因此,偶像符号意义不仅仅是对当下新农人形象的探索,更多的是对当下年轻人意识的再现。、
四、偶像符号价值的实现路径
《种地吧》通过将十位少年作为节目的卖点来吸引受众。作为偶像符号意义的接受者,大众在实现符号的价值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只有偶像获得大众的认同,才能被确立为符号,并使其意义得以表达,进而体现其符号价值。
作为符号消费的潜在群体,大众影响符号价值的实现。节目内容、制作形式、综艺宣传等成为诱使大众进行偶像符号消费的手段。在这一消费过程中,偶像符号意义从明显的形象走向社会本体,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
(一)受众认同:偶像符号意义的确定
偶像符号引发的偶像符号消费,映射了大众对自身心理认同的一种体现。偶像的表意过程也是偶像符号唤起受众认同的过程。为了探究由十位少年构成的符号文本所塑造的独特“Star Image”(明星形象),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节目受众进行调查。在这项调查中,共收集到628份有效问卷,并从受众对节目获取途径、少年通过节目与受众互动以及受众对偶像形象的印象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通过深入探讨受众是否能够通过偶像形象激发对农业的兴趣,确定综艺节目中的偶像符号意义在受众中的认同度。
经过研究发现,节目吸引观众的特定点与农业推广的有效性相关。这表明十位少年激发了观众对农业推广信息的更积极的态度。这也与十位少年在节目中展现的农业活动的魅力和表现有关。开播前,77.4%的观众并不了解他们,72.1%的观众认为该节目仅是为了炒作而设,且观众并不认为这些少年能够胜任农业工作。然而,随着节目播出,95.2%的观众对少年们的表现表示非常喜欢。调查结果显示,观众认为最吸引他们的是十位少年的卓越表现,占比达到52.5%。由于十位少年真实接地气的表现,观众与这些少年之间产生了共鸣,这大大激发了公众对农业的兴趣,唤起了他们深埋在血脉中的对土地的热爱。
在偶像效应的带动下,受众的观看频率居高不下。频繁观看使观众更容易接收、消化并对农业推广信息做出积极响应。数据显示,96.8%的观众表示已观看该综艺节目的50期正片。这为在节目中嵌入更多的农业推广元素提供了战略指导。观众对整体节目的积极看法转化为对农业推广的支持。据统计,99.4%的观众表示愿意将节目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观众愿意通过口碑传播推荐节目,这成为农业推广的有效渠道。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的口碑传播,可以扩大农业推广的受众范围,提高农业推广的影响力。
在对信息进行汇总后,综艺节目中的十位少年能改变受众对于农业的看法,对农业推广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观看综艺节目的过程中,在文化与情感双需求的影响下,受众肯定了偶像符号的价值,也形成了全新的对于乡村生活的一种想象。在此背景下,节目已不再局限于对现实乡村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借助影像传播的力量,加快对乡村文化的传播,助力农业发展。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维持社会共同经验的。”十位少年所构筑的叙事情境在这一空间中为受众提供了沉浸式体验。
(二)情感消费:偶像符号意义的变现
十位少年被符号文本赋权,并在粉丝的追捧下,逐步拥有了商业价值。这一价值诱导受众进行情感消费,让偶像符号价值向实际的物质资本进行演变,最终其得以变现。鲍德里亚曾提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们所进行的消费行为并不只是原有意义上的物品使用权,而是占有物品身后被文化工业体系所制造出来的各种符号的意义。”在鲍德里亚看来,符号消费从来不是对商品物质属性的消费,而是一种文化消费。他认为物成为符号,符号取得了至上的统治地位。
偶像符号在《种地吧》中的价值实现,本质上是一种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消费的再现。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中,年轻人被迫适应城市的喧嚣和紧张的工作生活环境。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情感流失的日益增加,致使个体在既定的社会框架中出现疲劳感,难以确立认同感。综艺节目的出现为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提供了一个寄托之所。《种地吧》以慢综艺节目的方式打破了当下对快综艺节目的审美疲劳,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建构更加贴近受众生活的偶像符号的路径。通过观看少年们的田间生活劳作,大众将其生活经历与少年们的挫折和成就相结合,并触发共鸣。节目选用的十位少年性格各异,这在丰富节目趣味性的同时,也能为不同受众群体带去不同的情感需求和属于自己的情感寄托。这种差异化的构建,有效推动了大众对于偶像符号的消费。消费社会的本质是一种符号消费,其中展现出的是一种差异化。差异化不仅存在于符号产品的编码过程中所赋予的符号消费者身份的特定意义,也是实现消费者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因此,在观看综艺节目的过程中,受众群体的情感被带动,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偶像符号成为弥补大众情绪的商品。
偶像符号的现实价值,不应仅仅局限在少年在外在形象上给人带来的一种感官性的视觉享受以及其本身所映射出的意义,更应该体现在特定叙事的作用下所展现的当下多元化的乡村生活环境以及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十位少年所展现出来的积极的生活态度。这种富有感染力的状态拉近了大众与十位少年的距离。
十位少年在综艺节目中以影像化的模式建构了一套全新的视听符号体系,他们不仅是符号意义的生产者,还满足了消费者对群体镜像的认同需求。抖音、微博、哔哩哔哩、小红书等不同平台所发布的相关信息,在增加了偶像符号信息的传播途径的同时,也对其符号意义进行强调、延伸和转化,由此激发观众对农耕田园生活的想象。在这个综艺节目用十位少年吸引当下社会的年轻观众的同时,也将“相信土地的力量”这种乡土情怀以及认真耕耘的价值观融入节目之中,唤醒了观众的情感期待。
节目记录了十位少年种小麦、养玫瑰花、种菜、养牲畜家禽、建设家园等过程,以少年本身的热度作为吸引大众的出发点,随着叙事的推进,突出的是乡村环境中的乡土文化符号。此时,偶像符号意义已经从人物单纯的才艺、外貌、气质等个人形象方面转变为一种代表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情感链接。这种情感的出现激发了观众内心深处的一种对回归乡村宁静的向往,并转化为一种认同感。无论是对房屋家园的基础设施的改造,还是在田间劳作的场景,都为观众营造了一种对自给自足的生活空间的想象,满足了观众情感上的真实需求,这也是《种地吧》热度不减的根本原因。
偶像符号意义引导并激发了大众的情感认同和归属,因此,当他们进行情感出售时就会有人进行情感消费,偶像价值的变现最终体现在了商品价值的交换上。十位少年结合目前流行的商品营销模式———直播带货和快闪集市,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增强了节目观众的参与感。在苦于蔬菜滞销的时候,由于粉丝对综艺节目的热爱,水培生菜得以走进杭州的商场。节目所带来的粉丝效应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的消费倾向。作为一档纪实性节目,观众在观看综艺节目的同时也对这些蔬菜、鱼、虾产生了情感。大众购买的不仅仅是食物的本身,其更多的是作为节目的参与者进行情感消费的构建。除了节目中的商品外,由少年代言的产品以及节目中衍生出的周边用品成为受众感性消费的结果。这在弱化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同时,更多地成为受众本身的情感表达。
可以说,《种地吧》打破了综艺节目以娱乐为主的模式,记录了真实的农村生活,以及农村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十位少年不仅是综艺节目叙事的核心,也是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对偶像话语权力的再现。正是凭借偶像符号的特殊性,十位少年在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的基础上,获得了一种认同感和参与感,由此实现了偶像符号消费。
五、结论
在当下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影响下,《种地吧》不仅仅作为一档涉农节目对国内目前综艺节目叙事进行一种全新的探索,更标志着社会对农人群体的关注。本文从符号学的视角系统地探讨了《种地吧》走红的原因。
本文从综艺节目本身的叙事内容出发,探究了偶像符号的形成过程;与此同时,顺应时代发展而生的各类社交媒体为大众提供了话语平台,完善了偶像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在偶像符号意义的基础之上,本文深入挖掘偶像符号价值的实现路径,发现作为符号意义的载体,偶像符号意义的表达必须得到受众的认可。作为资本市场的产物,综艺节目的本质是借助内容叙事来实现商业盈利,而情感消费成为偶像符号价值变现的最佳途径。十位少年在实际参与乡村建设和农业劳作的过程中,带动了偶像符号的情感消费。
作为传媒产业的一种表现形式,《种地吧》承担了振兴乡村的社会责任,并积极助力乡村文化传播。作为真人涉农综艺节目的代表,其为当前综艺节目注入了新的现实内涵和人文意义。因此,本文不仅从理论角度拓展了对偶像与乡村文化关系的认知,也为进一步探讨综艺节目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通过深入分析综艺节目的符号构建和传播模式,我们对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和文化传承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解。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解芳,张浩.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偶像符号意义探析——以综艺节目《种地吧·少年篇》为例[J].传播创新研究,2024(01):108-119+221.
作者简介
解芳,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校聘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传播符号学、大众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
张浩,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为影视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