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十一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背景转换与符码重组: 符号景观视域下的多重文化认同》,作者张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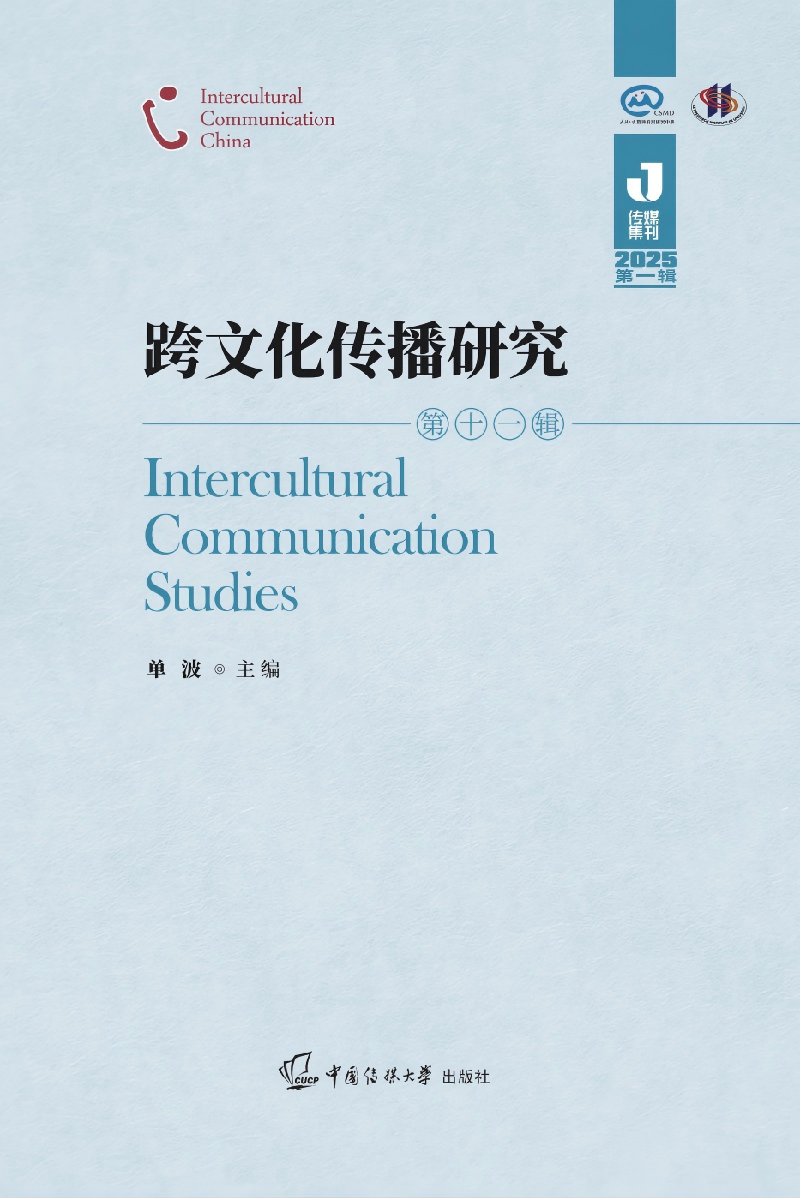
背景转换与符码重组:
符号景观视域下的多重文化认同
张兢
摘要:符号景观是指在场性视觉性图景。作为一种活的文化书写本,它与文化认同系统形成双向建构关系。它既作为文化认同的表征系统存在,又通过其符号语法形塑认同的生成路径。符号景观的在场性与视觉性特征构成文化解码的物质基础。在初始背景的限定下,符号景观通过双轴运作与语象合一机制完成编码,成为民族文化认同与地域文化认同的物化载体。符号景观的认同指向具有历时性动态特征。通过“背景转换”与“符码重组”两大机制,其文化认同指向发生转向:前者使符号景观脱离初始背景转向现代生活方式认同,后者通过国家符号的强势植入重构认同层级。两种转型机制共同揭示了符号景观的多重认同阐释力—在民族文化根基、现代性转型诉求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三重维度中,构建起文化认同的立体阐释框架。
关键词:符号景观;初始背景;背景转换;符码重组;多重文化认同
一、引论
新时代以来,文化认同问题再次凸显。与百年前那场急遽的文化认同危机中弥漫的文化自卑和文化焦虑感不同的是,新时代的文化认同就是重拾并强化失落的文化自信,涤荡影响民族感情“清纯度”的因素,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同一性”和“归属感”,重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而抵御来自外面的远处的“他者”的侵逼。新时代文化认同问题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带一路”倡议等话语紧密相关,业已汇聚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
然而,迄今为止,文化认同研究依然芜杂,充满争议。就像哈罗德·伊罗生(HaroldR.Isaacs)所说的,文化认同研究就像“雪人”(the snowman),大家都相信其存在,但是都无法确认其面相。或者像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的,围绕文化认同问题“一直存在着漫无限制的、不得要领的激烈争论”。虽然如此,两种颇具影响力但彼此针锋相对的学术立场依然清晰可见。一种是客观体质文化认同论。这种立场预设了某种“共同文化”的存在,主要表现为共同体质特征、共同语言、共同生活习惯等,文化认同的目标就是要在寻根式的追本溯源中,揭示“隐藏着的”文化身份以及“隐藏的历史”。另一种是主观认同论。这种立场将文化认同视为历时性植根于人们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想象。这种想象源自某种“根基性的情感联系”,或者源自资源(政治的和经济的)竞争与分配中的情感倾向。
上述两种学术立场,都建立在一个隐而不显的假设前提之上,即文化认同被视为对特定民族文化的内在归属和忠诚的体现。这一观点将文化认同视为个体对某一单一民族文化的共享情感和价值观的接受和追求,强化了对民族身份的确认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提升。这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对自身文化根源的追寻和讲述,以区别于“他者”,或者被用作抵制外来影响,甚至成为民族独立和文化保护的盾牌。这种将文化认同视为对单一民族文化的忠诚的观念,虽然在某些文化环境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并不适用于所有语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环境中。单一的民族认同理论往往导致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其结果是因为对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刻意彰显而导致文化的疏离、拒斥甚至文化对抗。
在国内文化认同研究中,费孝通先生的多重文化认同观被奉为圭臬,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在中华民族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由此,文化认同包含着三个层次,即中华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集团”(各民族之下包含的更低层次)。费先生的观点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响应。张汝伦将文化认同界定为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包括民族本质、国家的核心情感与象征,民族认同也规定了国家是什么、国家做什么和一种独特的国家使命感。韩震将文化认同视为一种“中介形式”,它一方面与族群认同有交叠部分,另一方面与国家认同有交叠部分,同时与全球认同有交叠内容。国家的文化认同必须大于族群的文化认同,族群文化认同不能超越或凌驾于国家文化认同之上。王沛、胡发稳将文化认同区分为本民族文化认同和主流(主体)文化认同两个层面,认为二者具有等效的生存价值。都永浩、左岫仙认为,文化认同包含两个层面,即国族的文化认同和族裔民族文化认同,其核心是国族的文化认同,族裔民族文化认同应受到尊重。文章进一步认为,国家文化认同必须来源于国家内部的各“民族”文化,但不能具体化,需要萃取和编织,否则会导致部分民族成员对国家文化认同的疏离。
多重文化认同观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回响。乔纳森·弗里德曼将文化认同概括为四个方面,即种族(Race)、现代族群(Modern Ethnicity)、传统族群(Traditional Ethnicity)、生活方式(Lifestyle)。黎巴嫩学者萨利姆·阿布认为,文化认同包括三个层面,即对民族集团文化遗产(语言、宗教或种族指标)的认同、对民族国家(由多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同质文化遗产的认同,以及对超民族整体的共同文化的认同。民族集团文化认同只有在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在当今这种原始部落是假设的)才可能形成一致。
综上所述,文化认同的多重性或者多重文化认同观应该成为新时代文化认同问题的恰当范式。问题在于,如何对文化认同的多重性展开研究?文化认同的多重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当然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展开讨论。从符号景观入手是一种新的尝试。本文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的观察试图表明,作为“活的文化书写本”的符号景观,是特定民族(族群)文化的历史凝结,它将富有意味的符号元素组合连接到一起,整体性表达着人们的某种情感和思想观念。这种情感和思想观念,不仅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来源,而且包含着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思想因子,具有无限扩展的认同潜势。在这一过程中,背景迁移与符码重组是文化认同潜势扩大的基本符号运作手段,文化认同的多重性得到了具象的生动的呈现。
一、符号景观与文化认同的双向建构
什么是符号景观?符号景观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关联?这是本文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景观”(spectacle)的本意是观看、被看,即一种被展现出来的视觉性图景。“被展现”就是符号再现。所有进入人类感知视界的公共性视觉图景,都应被纳入符号景观的范畴。符号景观既可以是现场的再现,也可以是缺席的呈现;既可以是真实的描绘,也可以是虚拟的构造;既可以存在于文本世界中,也可以活跃于现实之中。“在现代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spectacles)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一种表现。”德波所批判的,是那种缺席的、虚拟的、存在于文本世界的景观,这种景观的“积聚”,导致视觉性表现取代了现实存在。本文所关注的,不是德波所批判的符号景观,也不是被媒介呈现的景观,而是在场性视觉图景。作为“情感投射的载体”,符号景观客观上构筑了一个意义的空间,将生活在此的人们包裹在其中,成为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的构成部分,时时召唤着人们的认知与解读。这类符号景观以多模态的符号形式,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人类的情感认同与共同记忆,使得过去的文化传统在当代社会中得以生动呈现。
在场性强调了符号景观与物理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不可分割性。符号景观是书写于现场并再现于现场的视觉景观。一方面,符号景观的书写者总是置身于某个固定地点进行书写。这一地点不仅仅是书写者的符号书写场域,更是书写者安身立命的生活场域。书写场域与生活场域高度重叠。书写者在生活场域的种种感知和生命体验,通过符号书写铭刻在书写场域之中。生活空间、生命空间和书写空间通过“多重意识思维”被编织在一起。由于符号景观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它限制了私人化的符号表达,因此,书写者所书写的并非个人情感与生命体验,而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共同文化记忆和情感。否则,则会被擦除。另一方面,当符号景观书写完成后,“文本”并未离开产生它的书写场域,而是永恒地留存在书写场域中。因此,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其意义指向,必须回归到催生符号景观的物理空间和文化环境中。与此同时,符号景观并非单独向人们发出召唤。在每一个符号景观的背后,都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和传说,或者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事件。这些故事、传说和历史事件或者表达了某种情感,或者传递着一种人生哲理,或者宣扬着某种价值准则。这些叙事元素都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在此意义上,本文将符号景观称为“活的文化书写本”。
符号景观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整体性符号景观中产生的。因此,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符号景观:一种是主导性符号景观,另一种是整体性符号景观。在特定场所,符号景观与其他符号元素构建了一个整体性的符号景观。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本文将这种整体性的符号景观称为“背景”,将“背景”中占据视觉中心的符号景观称为主导性符号景观,将“背景”中的其他符号元素或者符号景观,称为主导性符号景观的“伴随文本”。主导性符号景观出现的最初场所,构成了其初始背景。初始背景中的主导性符号景观往往蕴含着其最初的文化认同指向。而主导性符号景观是可仿制、可移动的。它会从原始背景中被迁移到新的场所,由此产生了新的背景和新的伴随文本。随着背景转换和伴随文本更替,主导性符号景观的认同指向便会发生变化。本文所称的“背景转换”即就此而言。值得强调的是,主导性符号景观的可仿制性、可移动性,并未否定它的在场性。恰恰是场所或者背景的转换,透露着文化认同指向的改变。本文所称的“符码重组”则指向符号景观的另一面,即“背景”并未转换,而在背景中增加了新的符号元素。新增的符号元素往往具有强编码的特征,它与主导性符号景观构成了新的主导性符号景观,这一新的符号景观的认同指向更为鲜明。在以下的阐述中,如果不加特别说明,本文所说的“符号景观”,指的是主导性符号景观,即在“背景”(整体性符号景观)中占据视觉中心的符号景观。
由这种认识出发,便能发现符号景观与文化认同的内在关联。首先,符号景观作为文化认同的表征系统,具有多层级的文化阐释功能。萨义德在文化政治的维度指出:“那些能使个体与群体相连接,塑造群体身份感的共同思想和价值体系,往往通过符号系统获得具象表达。”此论表明,抽象的文化认同需要借助符号系统实现实体化存在。梅洛·庞蒂从现象学视角强调符号与思维的共生关系:“任何思想都来自言语并重返言语,符号系统构成了认识的拓扑学空间。”这种认知范式在文化地理学领域得到呼应,段义孚提出的“地方感”理论揭示,特定地域的符号景观通过场所精神的物化表述,持续形塑着群体的身份认知。
其次,符号实践对文化认同具有规训与重构的双重作用。福柯认为,符号系统的生产始终伴随着知识权力的渗透,“景观语法”的建构往往体现着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通过标志性建筑、纪念场馆等符号景观,系统性建构国民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
最后,文化认同的动态性决定了符号景观的流变特征。霍米·巴巴指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呈现去中心化特征,导致符号系统经历着持续的解码与再编码过程。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则为这种流变性提供了政治经济学解释:资本逻辑对城市空间的符号重构,加速了传统符号景观的置换与重组。这种动态过程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中,展现为符号景观对文化主体诉求的镜像式反射与能动性建构的统一。
这种互构过程在不同尺度空间呈现出差异化图景:在宏观层面,国家形象工程通过符号编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中观层面的城市更新项目中,历史建筑符号的存续往往成为文化认同争夺的焦点;微观层面日常空间的符号实践,则体现着民众对文化认同的能动性建构。这种多层级互动最终形成文化认同的动态拓扑结构,其流变轨迹通过符号景观的更迭得以显影。
二、初始背景:传统文化认同的视觉表达
符号景观是产生在特定物理空间的视觉性图景。要解释符号景观的文化认同取向,就要回到初始背景,从其形式结构和编码策略两个方面入手。
(一)初始背景对符号景观认同指向的限定性
符号景观的认同指向始终受制于初始背景的复杂限定性。这种限定性具体呈现为三重约束框架:社会文化语境的基础性规约、个体经验框架的选择性过滤以及权力结构的规范性形塑。三种力量形成的结构张力,构成了符号景观意义生产与接受的边界条件。进一步而言,符号景观是书写于特定空间的视觉性图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并非自然联结,而是文化契约的历史产物”。社会文化语境为符号景观的生成与解读提供了基础规则,也限制了文化认同的范围和指向性。书写者的具身化体验决定了主体对符号景观理解的深度与方向,个人经历与知识结构会筛选出符合自身认知的部分,忽略或排斥其他可能性。同时,权力结构通过规范符号景观的生产与传播过程,进一步塑造了符号景观的边界,使得某些特定意义被强化,而另一些则被边缘化。因此,在初始背景中,符号景观的文化认同指向并非完全开放,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约束与选择。
本文重点分析的“和睦四瑞”景观和“铜奔马”景观就是如此。“和睦四瑞”(雕塑)景观是在河西走廊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认同度的符号景观,它最初出现在藏传佛教寺庙中心广场上,庄重肃穆的佛教寺庙建筑群构成了它的“背景”。如果进行文本追溯,“和睦四瑞”故事早已记载在佛经寓言故事集《如意藤》之中,“和睦四瑞”(雕塑)景观是对这一寓言故事的视觉化呈现。这部产生于13世纪的故事集,以通俗化、趣味化的形式传播着藏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赫赫有名的“铜奔马”(也称马踏飞燕、马超龙雀等)出现的初始场景是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的将军墓葬中,它与其他的铜马、铜牛、斧车、轺车、辇车、小车以及武士俑和奴婢俑等组成了规模宏大的铜车马仪仗队,墓室、铜车马仪仗队以及墓室结构等,形成了“铜奔马”的背景。因此,无论是“和睦四瑞”(雕塑)、“铜奔马”还是其他的符号景观,其初始背景限定了其文化认同指向性。
(二)双轴运作:文化认同的形式化
所谓双轴运作,就是索绪尔所说的组合与聚合关系。所谓“组合”,即符号的线性排列,比如音素、词汇乃至语句在线性的语境中相互组合。每个符号在特定语境中被激活,与上下文环境相互作用,生成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意义.“聚合”则代表了符号的可选择性,它们共同存在于一个“潜在的记忆系列”中,等待被选取和激活,形成新的意义。罗曼·雅各布森将组合—聚合关系称为符号表意的“双轴运作”。他认为,聚合轴的功能是比较与选择,组合轴的功能是邻接黏合。比较与连接,是人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最基本的维度,也是任何文化得以维持并延续的二元。
以“和睦四瑞”为例。在聚合轴下,“和睦四瑞”由四只动物—大象、猴子、兔子和鹧鸪鸟构成。每一种动物形象都是在藏族文化记忆库中萃取提炼的结果。大象在藏族文化中不仅被视作智慧的象征,还与释迦牟尼佛的诞生故事相联系。猴子在藏族的起源神话中占据中心位置,猕猴与罗刹女的后代被认为是藏族人的祖先,表达了藏族人对自身起源的集体记忆。兔子代表了自我牺牲和慷慨的精神。鹧鸪鸟,作为智者和学者的象征,表达了对知识和智慧的尊重。四种动物还代表着藏族历史中的著名人物。大象代表着目犍连(以神通第一著称),猴子代表着舍利弗(以智慧第一著称),兔子代表着阿难陀(以多闻第一著称),鹧鸪鸟代表着佛陀。在组合轴下,“和睦四瑞”的动物排列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符号系统。大象、猴子、兔子和鹧鸪鸟的垂直排列,按照大小和力量的逻辑,构建了一种层次结构。然而,这样的排列组合表达着怎样的深层含义呢?图像本身并不能直接回答。
“铜奔马”也是如此,对于此马为何马、此鸟为何鸟,甚至如何命名这一符号景观,迄今依然存在着较大分歧。虽然如此,但是没有人会否认,此马与此鸟绝非随意选择的,它们是在历史文化记忆库中被精心选择出来的。同时,此马与此鸟的非常态组合,亦让人们产生无穷的想象。
(三)语象合一:认同指向的明确化
图像符号与语言文字符号均承载着表意的功能,但两者编码方式不同,亦各有其局限性。图像符号以其直观性见长,但对接受者的“前见”有着高度依赖。若接受者未曾通过语言文字对其内涵有“预先”的理解,图像符号的指向意义往往模糊不清,人们难以捕捉确切的“意图定点”,从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语言文字符号虽能系统且深入地传达意义,但因其抽象度高,提高了阐释者理解的门槛,从而导致理解出现障碍。对于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民众而言,这一点表现得比较突出。因此,多数符号景观采取了图像与文字相结合的编码方式,借助语象合一、图文互释的策略,使意义指向更加明确、直观、易于理解,从而暂时性地维持在一个理想的预设点上。
“和睦四瑞”就采用了这样的编码策略。多数“和睦四瑞”雕塑的底座上都刻有文字说明。比如,矗立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寺门前的“和睦四瑞”雕塑的底座上,有汉语和藏语文字说明。其汉语文字说明如下:
和睦四瑞是出自佛经的一个寓言故事。
很久以前,一方美丽的净土上生活着大象、猴子、兔子和鹧鸪鸟四只祥瑞的动物。一天,鹧鸪鸟从远方衔来一粒尼卓达树种,兔子把种子埋进了土地,猴子用树枝将其围了起来,大象用长鼻汲来泉水浇灌树苗。在它们的精心呵护中,小树苗终于长成了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参天大树。从此,它们栖居在树下,避雨乘凉,分享果实,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出行时,大象驮着猴子,猴子背着兔子,兔子头顶鹧鸪鸟。
在这一文字叙述中,大象、猴子、兔子和鹧鸪鸟合作培育出一棵象征生命与繁衍的尼卓达树。这一文字说明,明确揭示了生物多样性、生态共生以及团结协作的理念,即每种生物都有其独特价值并能为共同体作出贡献。值得说明的是,完整的“和睦四瑞”图,其左侧还有一棵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参天大树,这棵树被称为“尼卓达”(或“烈卓达”“卢树”等)。尼卓达树的茂盛,不仅见证了四种动物的辛勤努力,也成为它们共享的生存资源。
“铜奔马”则不同。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字说明,诸多问题悬而不决,争议此起彼伏。李学勤认为:“武威出土的铜奔马。是一件非常特殊的青铜器,它既不是一个实用的器物,同时它也不是一个专门为殉葬而制作的一种随葬品,它所象征的这种形象,就是大家都说的天马,也就是‘汗血马’。”这一观点虽然得到了一定范围的认可,但争议点依然不少。叶舒宪则试图从这一符号景观中发掘古人的生死观念:“古人不认为死亡就是人类生命的终点,死后的灵魂升天是获得永生的必要条件。车马随葬制度就是这样伴随着商代初用车马技术的现实而流行开来。直到汉代用墓葬画像石的雕刻车马出行升天形象出现,才取代用活马真车陪葬的礼俗。”
综上所述,我们将符号景观置于产生它的地理空间和背景中,便不难发现,符号景观中内含的“地方感”催生了地域的或者民族的情感依附和认知图式,这种文化认同本质上是民族文化认同或者地域文化认同。“和睦四瑞”以大象、猴子、兔子、鹧鸪鸟的和谐共处为视觉象征,传达出对和平、团结和共生的向往。这一符号景观,不仅体现了藏族人民对社会和谐的崇高追求,也彰显了他们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尊重与接纳。“和睦四瑞”所负载的价值观念,已深深植根于藏族的日常生活和仪式中,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来源。“铜奔马”因其出土地而闻名,成为武威乃至河西地区地域文化的象征。随着它自身影响力的日渐扩大,回返式强化了这种地域文化认同。
三、背景转换:从传统文化认同到现代文化认同
所谓“背景转换”,特指符号景观在时空维度中伴随社会文化变迁发生的语境重置过程。这种转换涉及物理场景的位移、空间场景的转变以及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等多个方面,其本质是符号景观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动态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认同(包括族群的和地域的)转向乔纳森·弗里德曼所说的现代生活方式认同:不同的文化群体被整合进了(通常具有等级性的)“马赛克式”的更大的总体之中。“被理想化”的现代生活风格的视觉化表达,构成了生活方式认同的主要内容。“和睦四瑞”和“马踏飞燕”作为典型案例,生动地展示了这一过程。
(一)背景转换:从宗教语境到世俗文化的演变
格尔茨指出:“宗教符号系统通过仪式化展演维持其神圣性,这种展演必须依托特定的文化剧场。”在初始背景中,“和睦四瑞”景观中往往嵌入特定的民族叙事框架,承载着超越世俗的精神价值,景观图像叙事强调僧团伦理秩序。当它进入城市广场、旅游景区和展览馆等现代公共空间时,它与现代城市的视觉景观相互融合。伴随文本从《毗奈耶经》转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释体系,语义重心转向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的世俗价值。“和睦四瑞”的雕塑作品常常与其他公共艺术装置共同构成一种独特的视觉景观。这种景观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还通过其象征意义传递出和谐共生的价值观,进而促进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马踏飞燕”的符号嬗变轨迹更具典型性。作为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青铜器,其原始语境中的“天马”意象承载着汉代“羽化登仙”的升天观念。1983年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后,该符号的伴随文本发生根本性转变:考古学话语让位于现代性话语,“速度”与“超越”的抽象理念取代了具体的丧葬文化内涵。无论是被用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是成为各类文创产品的设计灵感来源,“马踏飞燕”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跨时代的适应能力。
(二)生活化的表现形式:传统符号的现代诠释
除了空间场景的转变外,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也是文化认同扩展的重要途径。在现代生活中,“和睦四瑞”逐渐突破了传统艺术载体的限制,被广泛应用于挂毯、雕刻、十字绣、饰品甚至汽车挂件等实用器物的设计中。这种生活化的表现形式拉近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并借助传统符号景观表达现代生活方式的理解。挂毯和十字绣等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本身便是一种文化实践。制作者通过手工技艺将“和睦四瑞”的图样转化为日常生活用品,既保留了传统符号的艺术美感,又赋予其实际使用价值。与此同时,饰品和汽车挂件等小物件则进一步扩大了这一符号景观的受众范围。这些商品以其精致的设计和丰富的寓意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群体。他们通过购买和佩戴相关产品,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彰显了个人品位和身份认同。
“马踏飞燕”在现代文创领域的应用同样值得关注。近年来,随着西北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许多景区和商家围绕“马踏飞燕”开发了一系列特色文创产品。从精美的复刻版青铜雕塑到创意十足的钥匙扣和书签,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游客的购物需求,还通过其独特设计强化了“马踏飞燕”作为文化符号的记忆点。更重要的是,这些商品通过市场流通实现了文化符号的跨地域传播,使得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并了解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
(三)消费文化的流行趋势与文化认同的深化
消费文化的兴起为符号景观的意义扩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通过消费行为表达自我认同和价值观。因此,当“和睦四瑞”或“马踏飞燕”等传统符号被巧妙地融入商品设计时,它们便获得了全新的生命活力。例如,在西北地区的旅游市场上,带有“和睦四瑞”图案的挂饰和首饰备受青睐,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更因为它们能够唤起人们对和谐共生理念的共鸣。这种基于消费行为的文化认同,使得传统符号的意义得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得到传播和深化。
“符号的意义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每次阐释都是新的意义生产过程。”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加剧的当下,符号景观的背景转换呈现出加速态势。数字媒介创造的虚拟场景,使得传统符号面临“超语境化”挑战—抖音短视频中的“马踏飞燕”变身搞笑素材,元宇宙中的“和睦四瑞”成为数字藏品,这些新场景正在重塑文化认同的生成机制。
四、符码重组:国家认同的强势表达
2022年,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与十年前相比,以“和睦四瑞”雕塑为中心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寺景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十年前,“和睦四瑞”雕塑与金碧辉煌的天堂寺建筑群,整体性构成了引人注目的符号景观。十年后,在“和睦四瑞”雕塑正前方和天堂寺正殿前方,两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正殿前方的旗杆底座上,完整地刻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歌词、曲谱。旗杆左侧,树立着一块用汉语和藏语双语书写的“爱国爱教,团结和谐,发展进步,正信正行”的醒目标牌。环绕天堂寺一周的步行走道的路灯杆上,悬挂着火红的中国结,中国结的中心用黄底红字书写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国旗、国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国家符号的加入,使原来的符号景观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现象正是本文所提出的“符码重组”。“符码重组”特指在既定符号场域中植入具有强编码特征的国家符号,通过新旧符号的互文性联结重构意义网络,最终形成指向明确的国家认同表征体系。对此,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实践通过符号的重组实现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新空间形态必然伴随新的符号语法。”
(一)符码重组意味着文化认同的方向从民族文化认同转向国家认同
民族文化认同,作为对特定民族(族群)文化或身份的深厚情感和忠诚,正如哈罗德·伊罗生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类似于“姆庇之家”(House of Muumbi)的“原乡情感”(primordial affinities)。“和睦四瑞”景观所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民族文化认同,“铜奔马”则指向了地域文化认同。尽管民族和地域文化认同在特定民族和地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可能具有人群和地域的扩充潜势,但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和地域界限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核心在于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形成。这两种意识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是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以及共同应对外部挑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人们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这种共同体意识在不同文化群体中产生了“休戚相关性”的情感和行动忠诚,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便在这种情感和行动忠诚中得以体现。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往往被各种因素所遮蔽,导致国家认同的力量被削弱。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国家符号如国旗、国歌等被赋予重要的角色。国家符号的强势介入,不仅是对被遮蔽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召唤,也是对“我们是谁”和“我们不是谁”的明确宣示。有论者认为,“族群”的认同不能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国家的文化认同必须高于族群的文化认同。国家符号对符号景观的强势介入,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视觉化表达。它们通过强化国家认同的符号元素,来巩固和重申国家认同在多元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这种视觉化的表达方式,不仅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还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二)符码重组意味着对传统符号景观的吸纳与征用
文化认同的落脚点是国家认同。在构建国家认同过程中,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固然重要,国家共同文化建设也断不可废。国家共同文化就是中国各民族成员共同参与和创造的文化。塞缪尔·亨廷顿将国家共同文化称为“国家特性”,它超出人种特性、民族特性和宗教特性,深浅不一地被国家成员所共享。基于平等的“相互承认”以及在其中产生的“民族精神”,构成了国家共同文化的核心。
在构建国家共同文化的过程中,吸纳和征用传统符号景观是一个重要策略。传统符号景观不仅在视觉上凸显了民族的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强化了民族认同感。然而,这种认同并不单纯建立在外在的、可见的民族特征之上,如语言、习俗或体质特征等,这些特征在构成民族认同中仅起到了辅助作用,而非决定性因素。文化认同的核心在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同一性。应该看到,大多数传统符号景观内涵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与中华文化具有高度一致性。本文集中分析的“和睦四瑞”和“铜奔马”就是例证。“和睦四瑞”内涵的合作共享、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观念高度契合;它所包含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的伦理准则,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推崇的美好德行。“铜奔马”内涵的刚健进取、奋勇腾飞意向,与经济腾飞、民族振兴的时代精神高度契合。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对这类符号景观的接纳和征用,实际上是对其中共享文化基因的认同与肯定。
(三)符码重组意味着符号景观治理的出场
治理就是“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认同”。符号景观治理就是在符号景观构筑的意义空间,通过强化、改变或擦除某些符号元素,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国家认同。这意味着国家权力在公共空间中的象征性呈现与控制。
国旗、国歌等国家符号的强势介入,既是符号景观治理的肇端,也是具体的治理方式。国家符号在社会共享空间中的矗立,强化了民族国家的象征,同时塑造和再生产了国家认同的边界。符号景观治理还涉及对不利于国家认同的符号元素进行批判性审视,可能需要进行调整、重构,甚至消除那些削弱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统一性的象征。
在符号景观治理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挖掘、提炼有利于国家认同的符号元素和意义因子,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另一方面要涤除影响中华民族凝聚性和国家完整性的符号元素,对其进行改造、重组直至擦除。可以设想,符号景观治理或许是构建国家共同文化、实现国家认同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五、总结与讨论
在数字技术赋能的图文书写时代“在场性”作为符号景观的本质特征,呈现出德波所警示的“景观替代存在”的现代性悖论。这种本体论转向要求研究者必须穿透表象迷雾,沿着符号景观的生成轨迹—从原生语境的初始背景,经现代转型的背景转换,至国家叙事的符码重组—展开三重维度的考古学考察。通过现象学凝视与历史性回望的辩证方法,我们得以在特殊性中窥见普遍性,正如兰克方法论所给出的启示:“历史理解的真正路径,在于从具体现实向普遍法则的螺旋式上升。”
本研究虽在案例类型学的完备性与样本覆盖度上存在局限,但其理论建构具有双重学术价值:其一,通过建立“背景转换符码重组”的动态分析模型,突破了传统符号景观研究的静态范式;其二,提出的符号治理观直接对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在民族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方面,研究揭示了符号重组的双重实践路径—既需维系“各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库,又要创新“全民共享”的表征系统,这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可操作化的理论框架。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河西走廊民族互嵌型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符码体系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0BXW090)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参考
张兢.背景转换与符码重组:符号景观视域下的多重文化认同[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5,(01):153-170.
作者简介
张 兢,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