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十一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从“接触地带”到“参与地带”:博物馆如何进行跨文化合作? —评<参与时代的博物馆与人类学>》,作者周夏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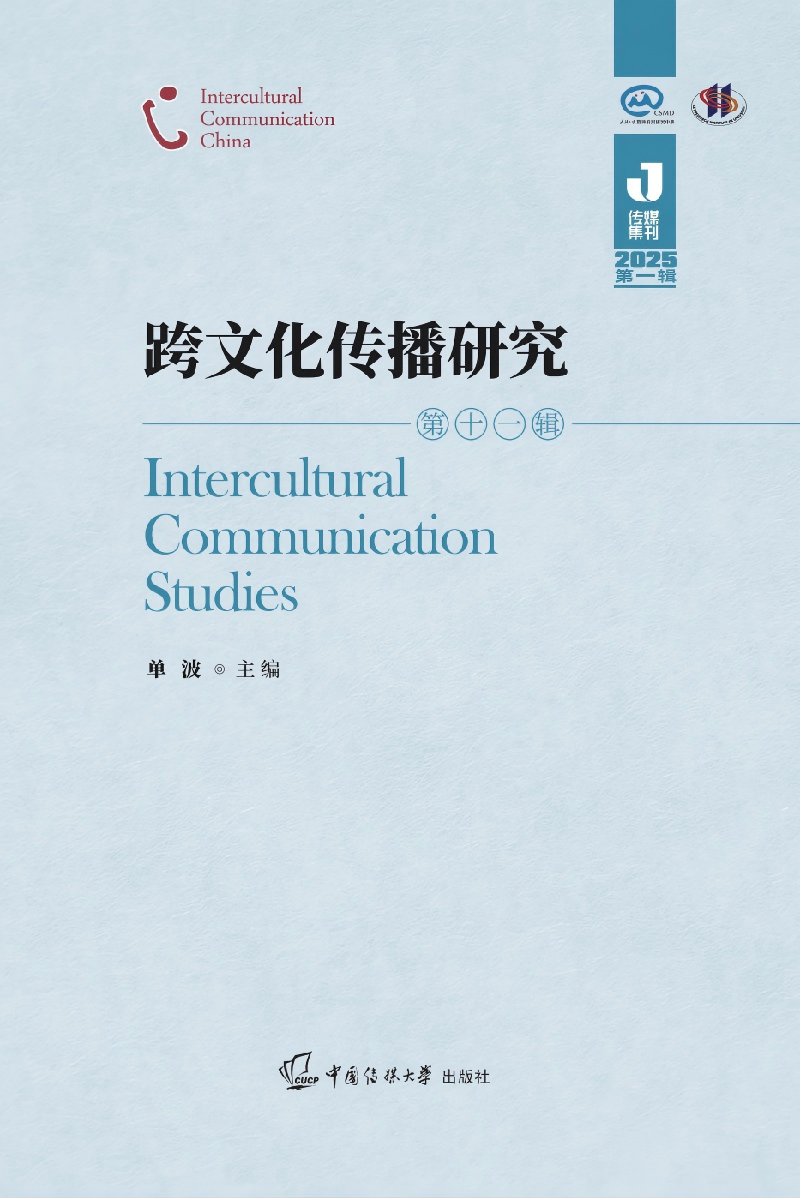
从“接触地带”到“参与地带”:博物馆如何进行跨文化合作? —评《参与时代的博物馆与人类学》
周夏宇
摘要:参与的时代也是一个融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博物馆学术、实践和专业工作者之间的真实的、可感知的界限已经因参与而消亡。对于博物馆民族志研究者来说,博物馆及其空间是探索收藏、展览和社会教育背后的内部过程的多维场域,除了对一般性博物馆工作的考察,博物馆与社区关系、文化生产以及消费的本质的研究外,原居民博物馆和非西方博物馆等亦被纳入视野。博物馆人类学对于物质性的回归促进了博物馆与本地社区的合作,扩大了人们对于如何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感知、阐释、评价和对待物品的理解。博物馆本土化可以激发更多的跨文化关系与跨文化能力,并且使人们意识到博物馆所代表的声音、观点与身份的多样化。
关键词:博物馆人类学;参与地带;跨文化合作;原居民
《参与时代的博物馆与人类学》(Museums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Age of Engagement)于2020年首次出版。作者克里斯蒂娜·克雷普斯(Christina F.Kreps)系美国丹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物馆人类学与博物馆遗产项目研究部主任。她长期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跨文化与比较研究,在荷兰、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地进行博物馆民族志研究。该书试图以博物馆人类学的视角回应当下多样性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新议题。基于作者过去30余年的研究与实践性工作,该书以美国、荷兰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博物馆为案例,聚焦于“参与时代”,探讨博物馆在殖民与后殖民语境下的公共角色。
整体而言,《参与时代的博物馆与人类学》将博物馆人类学放置在多元社会背景中考察,既有以美国为代表的移民国家,又有以荷兰为代表的去殖民化国家,以及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独立国家,兼具理论阐释与应用实践双重视角,同时又将研究者的思绪从田野转移回家中,去开拓“摇椅人类学”的新可能。
一、博物馆人类学的历史回溯
(一)博物馆与人类学的相遇
博物馆的产生源于人们交流与收藏的欲望。博物馆的英文表述“museum”与缪斯女神(Muse)有关。公元前290年,托勒密一世为缪斯女神建立了一座学习中心,叫作“museion”,意为“缪斯女神的神庙”,这是博物馆的雏形。中世纪以后,博物馆在西方社会中崛起,与之紧密相连的是民族国家的建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科技革命提出的“普及知识”的口号与私藏文物的风尚为博物馆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博物馆成为与百科全书一同出现的新事物。17世纪后半叶,英国的阿什莫林博物馆、伦敦塔皇家军械库等展馆纷纷建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博物馆。该时期的博物馆仅对少数精英和专家学者开放,强调展览物的私有性与排他性。18世纪后期,民主运动提倡平等观念,博物馆的公共性不断提升,逐渐面向大众开放。博物馆的内容逐渐从自我表达转向呈现差异化的他者。
早期的人类学以研究“异文化”为起点,研究者们尽可能地选取极为差异化的他者来反观自身。19世纪,摩尔根(Thomas H.Morgan)将古代社会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几个等级。在古典进化主义者看来,“他者”是蒙昧的、孤立的,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证明西方文化的先进性.19世纪末,以德国的格雷布内尔(F.Graebner)等人与英国的里弗斯(W.H.R.Rivers)等人为首的传播论派强调文化的传播与“借用”。他们认为,文化是交映生辉的。同一时间,距离遥远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同样的文化形式。在传播论者看来,“他者”没有那么落后,并且是可交流的。20世纪以来,文化相对主义开始取代文化等级观,试图“从本土视角”出发理解文化,将世界看作“多样文化的场所”,即一幅“文化拼图”。该观点认为,文化属于某地和某民族,具有独特性,能够被发现、描述、记录和展示。
博物馆与人类学的相遇是以美洲大陆和欧洲自19世纪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与殖民扩张为动力发展的结果。在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初,由于理论建构须依赖于对具有文化与历史价值的人造物的分析,博物馆与人类学的捆绑是十分紧密的。博物馆作为“制度性家园”(institutional homes),反映人类学对他者之物的热情,同时是面向公众传播人类学知识的重要媒介。美国知名人类学者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与玛格丽特·米德(Magaret Mead)都曾在博物馆工作。然而,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研究场域从博物馆转向大学,田野调查所获得的一手资料代替人造物,成为文化人类学者的灵感来源。对于很多学院派人类学家而言,博物馆逐渐沦为无人问津的仓库。到20世纪50年代,博物馆人类学者退居学科边缘的位置,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批判人类学学者受到殖民与后殖民语境的影响被“重新发现”,曾经各自为政的博物馆与应用人类学发展轨迹逐渐汇聚。博物馆人类学肇始于这一时期。博物馆人类学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即民族志,了解博物馆在社会中的作用、历史,以及进行文化生产、消费和行动的实践过程。然而,克雷普斯认为,被忽略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博物馆人类学争论与批判研究值得被重视。对此,她在本书中运用跨地区比较的方法,以丰富的案例回应了自己的关切。
20世纪90年代,两位知名博物馆人类学者迈克尔·埃姆斯(Michael Ames)与理查德·库尔因(Richard Kurin)指出,博物馆与人类学应该鼓励公共参与与应用实践。受到他们的启发,克雷普斯认为,博物馆与人类学的确应该革新视角,以应对“社会网络日益密切、公共参与度日渐提高、社群多样性逐渐提升”的参与化新时代。
(二)民族志博物馆
民族志博物馆的出现要早于博物馆人类学这一研究脉络的形成。广义而言,收藏民族志藏品的博物馆都可以被归入民族志博物馆的范畴。美国的民族志博物馆多为高等学校管理。由于其早期人类学历史多与进化论和自然史紧密相连,民族志藏品往往见于自然史博物馆—这也成为20世纪初学者们辩论的焦点。在欧洲,专门的民族志博物馆的历史更为悠久。近年来,许多民族志博物馆将自己重新定义为“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博物馆,如瑞典国家世界文化博物馆(Swedish National Museum of World Cultures)、德国的劳滕斯特劳赫-约斯特世界文化博物馆(Rautenstrauch-Joest Museum of World Cultures)等。这些博物馆用“世界”的概念向公众表明,民族志博物馆不再局限于展示遥远的“他者”,而是关注面向当代多元文化社会的每一个人。这正是一种“全球文化拼图”的视角。如此,民族志博物馆带有强烈的跨文化意味。在本书中,克雷普思关注的是人类学博物馆在去殖民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它作为一种跨国文化形式和跨文化旅行的媒介在不同的背景下如何被重新诠释。
(三)作为方法的博物馆民族志
博物馆民族志即在博物馆中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等方法,考察博物馆对于特定社会的作用、机构历史以及文化生产、消费和行动的实践与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埃姆斯指出,要在我们的后院做应用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需要将我们自己视为“博物馆原居民”(museum natives)进行观照,将我们的博物馆看作“文化区”(culture area)和“异国情调的新领域”(exotic new field)。除了在本文化中研究“博物馆原居民”外,相关研究也着眼于全球视角,将人类学博物馆作为殖民主义与去殖民化过程中的跨国文化形式与旅行机构,考察博物馆在跨越国别和社会文化环境时如何处理共性与差异的问题。从方法上看,置身于全球语境的博物馆民族志需要以混合方法实现,包括长期的、沉浸式的和多点民族志,跨越不同机构、项目和国家的短期民族志,以及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此外,博物馆民族志研究通常需要如劳拉·纳德尔(Laura Nader)所说的“向上研究”(studying up),在我们自己的社会机构与组织中行使权力和责任的过程。莎朗·麦克唐纳(Sharon Macdonald)认为,博物馆民族志研究也需要一种“化熟为生”(defamiliarsing the familiar)视角,来克服自身的文化预设,以新的方式呈现熟悉的异国情调。有研究者还将博物馆人类学与视觉人类学、符号学和物质文化研究等领域结合起来。
二、博物馆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与方法
博物馆与人类学的相遇源于多元文化主体的交流需要。这正是跨文化传播的要义。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不同文化主体如何相互理解和对话。这种“跨”可以是跨国别的、跨区域的、跨语言的、跨种族的。即,跨文化传播要探讨的是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的问题。理解他者,就是理解自我。
博物馆把跨文化传播研究从平面图翻转为立体多维的图景:除了诠释空间层面的跨国别与跨区域交流外,博物馆也呈现跨时间维度的主体间对话,甚至展示人与物的交流—基于实物展览是博物馆区别于其他大众媒介的重要特色。博物馆像一支万花筒,步入其中,我们与异域文化、祖先文化和物质文化同处一室,共同构成了一幅斑斓的、马赛克式的景观,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
(一)何谓“参与”(engagement)?
“参与”是《参与时代的博物馆与人类学》一书的关键概念。近年来,“参与”成为人类学与博物馆学研究与实践中的关键词。克雷普斯希望将“参与”的概念运用到不同语境下的表达中。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参与”被解释为行动,是一种超越的、超然的、非参与的体验者与研究者的科学姿态。对于应用人类学家来说,“参与”是关于创造更多途径来获取人类学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来赋予个人和社区产生变革的权力。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遗产工作可以被视为一种公民参与实践,包括使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解决问题、树立社会责任感,促进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的公平正义的实现等,其目标“是成为变革的积极参与者,不仅在社区工作。而且与社区一起工作,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在博物馆人类学中,参与在很大程度上采取合作的形式,与“源群体”(source peoples)或“原群体”(originating peoples)—博物馆藏品的原始生产者协同进行意义生产。合作博物馆学(collaborative museology)表现出对于主动参与社区实践的鲜明的自我意识,博物馆则是各种知识生产主体、专业人士、文化社群相会、协同参与并产生崭新的思维方式的空间。布莱奥尼·昂休(Bryony Onciul)在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的“接触区”(contact zone)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参与地带”(en- gagement zone)一说,以突出跨文化参与和公民主导的基层社区与博物馆的合作模式。
参与的时代也是一个融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学术、实践和专业工作者之间的真实的和可感知的界限已经因参与而消亡。
(二)博物馆本土化如何可能?
博物馆与土著社区的合作是当代博物馆人类学的基石。特别是一些移民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等)在博物馆藏品保护、借取与归还、展览、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合作重置了权力关系,这为更加平等的新型参与模式开辟了可能性。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与土著居民合作一直是人类学、民族学的标志。不过,早期的合作往往是在殖民主义、残酷的同化政策、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被胁迫的土著社区的背景下发生的。如今的许多合作致力于纠正这段历史,探讨其如何影响博物馆与土著社区之间的关系,并时刻对该问题保持警惕。
博物馆本土化可以激发更多的跨文化关系与跨文化能力,并且意识到博物馆所代表的声音、观点与身份的多样化。此外,博物馆需要承认原居民“适应、改造、修改和本土化博物馆学过程的多种实践”。对于非西方博物馆模式的识别、记录与批判性分析不仅对于比较博物馆学意义重大,对于西方博物馆学有关去殖民化进程的研究也十分重要。
(三)多点民族志与跨文化比较
该书通过多点民族志的方式收集来自欧洲、北美和亚洲等地的人类学博物馆的历史与现实材料,呈现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博物馆意义生产的行动实践。多点民族志不同于传统的浸入式民族志,后者需要在一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扎根一个地方,通过长期的参与式观察收集数据,探究一个社群或族群的“整个文化与生活方式”。多点民族志则倾向于更多地依赖于访谈,更类似于一种“预约式人类学”(anthropology by appointment)。多点民族志也被称为“流动的民族志”,其工作原理就像绘制地形图一样,较传统民族志更加细致。民族志研究者以某种形式的逻辑链条,将不同田野点串联起来,从而去追踪不同地点的思想、事物与群体,以及它们的联系。多点民族志需要运用人类学不太常用的跨文化比较法,作为研究、讨论、阐释和体验多样性的重要工具,比较法对于理解分异过程和“跨越差异的相遇效应”十分重要。
三、多元主体的博物馆跨文化参与实践
在《参与时代的博物馆与人类学》的第三章到第六章中,克雷普斯介绍了她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
(一)与土著社区合作:温故知新
在美国人类学史上,博物馆与应用人类学是两条相对独立的研究轨道。美国博物馆人类学的记载始于19世纪40年代。在这一时期,博物馆是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的中心,大量人种学、考古学与古生物学的收藏品被发现并被安置在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等博物馆中。19世纪后期,美国掀起了一阵收藏与研究原居民文化的浪潮,博物馆将这些文化进化过程以线性方式呈现—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文明”。博厄斯主张以文化相对主义代替文化进化论,他提出一种“部落式收藏”(tribal arrangement of collections),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生活群体” (life group)的展示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了物品的地方性和情境性意义。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博物馆公共实践的重点在于对公共教育和参观者的关注。这也衍生出了博物馆管理者的困境—博物馆人类学家对个人研究和收藏、策展的双重义务,以及对公众的教育义务三者之间的冲突。博厄斯讨论过这个问题,即大型公共博物馆需要平衡三个主要功能:健康娱乐、教育公众和传播科学知识,特别是如何平衡后两者的关系。博厄斯也关注到博物馆对于藏品的去语境化处理是否会损害历史的真实性的问题。
作者在前文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博物馆人类学的研究属于被忽视的部分,却十分重要。例如,1976年在密尔沃基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都市栖息地:城市内外”(The Urban Habitat:The City and Beyond)活动探讨了城市面积与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关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博物馆与土著社区合作策展,使当地土著社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展示他们的祖先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连续性。这些合作取得了一定成就,提升了原居民对于博物馆的参与度。这同样是北美地区的原居民抗争的结果。在这一时期,美国印第安人、加拿大第一民族以及其他原居民一直在抗议美国博物馆对印第安文化的刻板呈现,他们的原居民行动(native activism)不仅聚焦于变革与影响美国主流博物馆,还致力于建立新的部落博物馆与文化中心,以此重建社区身份,促进文化复兴。这些行动对美国人类学博物馆的影响持续至今。
通过与土著社区合作,美国博物馆人开始从研究土著,转向将自己作为土著来进行研究,在研究他者的风俗习惯时,也研究自己的异域风俗。这也是前文学者从“接触地带”扩展到“参与地带”的历史语境。与土著社区的合作并不会依照博物馆预设的那样进行,其结果有赖于博物馆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以及本土化实践行动。
(二)探究“第三世界”文化:保持博物馆主体性
尽管两个国家的人类学博物馆发展都归功于西方的殖民扩张历史,但荷兰作为曾经的老牌殖民帝国,其去殖民化过程与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是迥然不同的。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荷兰国家民族志博物馆展开田野调研,以考察荷兰的人类学博物馆如何呈现非西方文化和鼓励公众的跨文化理解,荷兰的博物馆对殖民遗产影响的批判性思考,以及这种思考是如何与全球殖民与去殖民化进程相联系的。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博物馆主体性”(museum subjectivity)的概念至关重要。它指的是该博物馆机构的自我意识,以及它与周围世界的互动关系。该概念提示我们,博物馆并非独立于周围世界,而是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人类学博物馆需要着眼全球,去诚实地、共情地诠释非西方文化。
从17世纪早期开始,荷兰人开始通过东印度公司控制东印度群岛以及如今的印度尼西亚的领土,到1800年左右,荷兰正式开启在东西印度群岛的政治殖民时代。19世纪后期,随着剥削殖民的加剧,荷兰对殖民地历史文化的知识需求不断增加。荷兰人开始在殖民地建立人类学博物馆,聘请人类学家研究当地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尼西亚等国纷纷宣布独立,荷兰被迫放弃对其殖民地的控制,荷兰人离开殖民地,去殖民化时代由此开始,这一过程体现在荷兰的博物馆中。荷兰博物馆中出现的非西方文化藏品主要来自科学研究、军事考察、商业贸易、经济开发和殖民地传教等活动。20世纪中期以来,荷兰的人类学博物馆开始了去殖民化过程,主要包括批判性地反思荷兰的殖民历史,并重新定位其目的。人类学博物馆并不是专家学者与上层精英的专属,而应该成为社会公众获得娱乐与知识的场所。公众在博物馆中可以了解外国人的习俗、宗教和生活方式,感受自己的族群、民族与文化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对“第三世界”的关注是荷兰民族志博物馆的特色。
热带博物馆(Tropen museum)是阿姆斯特丹最大的民族志博物馆。其前身是哈勒姆的殖民地博物馆(Koloniaal Museum),1824年由荷兰贸易协会成立。博物馆展出了荷兰殖民时期的人工制品与原材料。1910年,殖民地博物馆转移到阿姆斯特丹,与殖民地研究所合并,向荷兰公众传递殖民地的“伟大成就”。博物馆将土著居民的文化表现为“原始”的,传递着“殖民主义为殖民地带来进步和文明”的观念。除了展示异国情调外,热带博物馆也讲述荷兰国内“少数族群”的生存困境,如移民的社会融合与福利等问题。热带博物馆避免在博物馆中呈现传统人类学博物馆中常见的“原始”和“外来”族群的刻板印象,而是讲述当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博物馆展览中所呈现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强烈依赖性使其受到“新殖民主义”的指控与批判。如何客观地讲述“他者”成为难解的问题。为了追求客观性,博物馆只能尽可能多地展示异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
1831年,内科学与民族志学者菲利普·弗朗兹·冯·西博尔德(Philip Franz von Siebold)向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建议,请求建立民族志博物馆,“通过陌生的、排斥的他者来了解自我”。皇家民族志博物馆(Rijks Ethnografisch Museum)成立于1837年,早期收藏的藏品包括西博尔德在19世纪20—30年代驻扎在日本长崎海岸的荷兰贸易站时收集的约5000件藏品。19世纪后期,该博物馆开始呈现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西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物品,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不断扩大展品的范围,展出来自太平洋、非洲、美洲、西伯利亚和北极等地的藏品。20世纪30年代,该博物馆搬到莱顿并重新开放,更名为荷兰国家民族志博物馆。该博物馆的去殖民化过程比热带博物馆的相应过程更加温和,学术研究与公共教育意味更加强烈。该博物馆利用许多临时展览扭转沉闷古旧的形象,通过跨文化比较、文化变迁与文化适应等方式展示本文化与异文化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荷兰国家民族志博物馆经历了私有化改造,其展览团队从完全由专业人士主导转变为博物馆与目标群体合作的组合形式。其展览通过将不同地区与国家的文化以互动和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强调全球的人类迁徙,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接触如何成为文化创新的关键动力。
(三)博物馆摩擦:跨文化合作的挑战
18世纪,荷兰和其他欧洲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西方式博物馆,在殖民历史时期主要为殖民利益服务。1945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后,博物馆开始协助去殖民化和国家建设的进程。在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博物馆不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的精英机构,而是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帮助提高公众的历史与文化意识。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作者进入印度尼西亚进行田野调查的时期,博物馆在当地还是相对较新的事物,当地并没有太多人具有博物馆意识。在作者调研的博物馆中,巴兰加博物馆(Museum Balanga)作为一家省级博物馆,集中展现地区文化与历史,促进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与文化融合。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由数百个民族组成的群岛国家,在这种具有高度文化异质性的国家建构多元统一的民族文化价值具有一定挑战性。该博物馆推广国家民族文化理念的方式之一是举办名为“群岛世界观”(wawasan nusantara)的巡回展览。该展览通过对比不同省份的文化形式,将民族文化建构为地方与区域文化的综合体。
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化浪潮开始影响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实践。然而,如何应对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殖民国家与独立国家的权力博弈关系则是新的议题。有研究者将其称作“博物馆摩擦”(museum frictions):“博物馆作为一套多元的、动态的实践、过程与互动的概念系统,呈现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尽管巴兰加博物馆在促进跨文化展示方面做出很多努力,但更多的现象反映了巴兰加博物馆并没有很好地融入当地社区。博物馆经常空空荡荡,缺乏活力。这是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表面上看来,巴兰加博物馆与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博物馆的功能基本一致,但该博物馆在处理地方文化时尽可能尊重本地风俗,与当地社区合作紧密。通过对当地社区居民的调查,克雷普斯发现,社区居民普遍不太理解博物馆的工作,认为其没有代表真正的本地文化。未来,博物馆会寻求如何提升公众博物馆意识,从而促进社会参与。
四、结语与反思:对“参与地带”的思考
《参与时代的博物馆与人类学》通过多点民族志的方式收集来自欧洲、北美和亚洲等地的人类学博物馆的历史与现实材料,呈现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博物馆意义生产的行动实践,并对人类学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完成从“田野”到“书斋”的视角转换。作者运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案例展示了博物馆与人类学是如何分离,又是如何再次相向而行的。尽管不同案例国家的政治体制、历史变迁与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它们的博物馆在致力于呈现多元文化、应对全球化趋势、呈现地方性知识和努力寻求与当地社区合作等方面存在相当程度的共性。这对于当今时代的全球博物馆如何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这一问题十分重要。
该书提出的一些“参与”的案例为博物馆跨文化传播注入新的活力。例如,美国博物馆的案例表明,通过与当地社区合作,我们可以探索出将自身作为他者的研究视角。去重新学习本文化的未知部分,生产出新的意义。荷兰的博物馆通过呈现第三世界的风貌人情,去批判地思考殖民遗产,尝试将博物馆作为社会系统的一环,共情地讲述他者的故事。印度尼西亚的博物馆作为去殖民化抗争的产物,在更为复杂的权力博弈中重新诠释民族文化。与此同时,这些博物馆还肩负培养社会公众博物馆意识的任务。
该书所强调的“参与”更多的是一种人类学式的参与,即博物馆如何与当地社区紧密联系,作者在不同田野点的民族志重点皆由此展开。不过,“参与”的内涵需要拓展。从主体来看,除了与当地社区合作,博物馆观众也是重要的“参与”者。观众是博物馆意义的共同生产者,而非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博物馆的角色不再是简单的“影响者”,甚至是“强迫者”,而应当让观众主动进行批判性思考,与博物馆协商差异与偏见的理解与呈现形式。在这种视野下,博物馆正从一种相对固定的文本(旨在说服或改变有偏见的个人)转向为建构性的资源(支持和促进无偏见的叙述)。从社会情境来看,该书完成于2020年,正是YouTube、TikT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发展较为繁荣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全民参与、个体化博物馆叙事的考察是该书未涉及的视角。美国博物学家妮娜·西蒙(Nina Simon)于2010年提出“参与式博物馆”(participant museum)的概念,将博物馆定义为观众能够围绕其内容进行创作、分享并与他人交流的场所。在博物馆的参与主体中,公众(特别是博物馆观众)也是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主动来到博物馆,并且积极地进行博物馆叙事。他们有的是本地居民,有的是远道而来的背包客,他们来自多元文化背景,不同的主体面对同样的博物馆会生产出不一样的意义。
此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对于革新博物馆表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技术是如何参与博物馆的行动实践的呢?它对于促进(或阻碍)多元主体的参与和跨文化偏见的形成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可以被纳入研究的视角。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博物馆跨文化传播研究”(24FXWB041)阶段性成果。
引用参考
周夏宇.从“接触地带”到“参与地带”:博物馆如何进行跨文化合作?——评《参与时代的博物馆与人类学》[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5,(01):245-258.
作者简介
周夏宇,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研究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