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6日上午,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芮必峰教授应邀发表讲座《斯蒂格勒和他的<技术与时间>》。讲座由中心研究员吴世文教授主持,包括武汉大学法学院张万洪教授及其团队在内的近40位师生参加讲座。
斯蒂格勒其人其书
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2020),法国当代技术哲学家。汉译著作有《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南京课程》等。
斯蒂格勒天生不安分。高中时就在外面打工。20岁买下一家餐厅,后来又开了一家酒吧。警察在酒吧里面抓了人,要他指证,他不干,警察封了酒吧。为了报复,他持械抢劫银行,抢到第四家时被抓,判了5年,1978年到1983年,26岁到31岁,他在狱中度过。他每天花十几个小时自学哲学,还不断给德里达写信,感动了德里达,收他为弟子。1993年,41岁的斯蒂格勒在德里达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主题是《技术与时间》。2020年8月6日,斯蒂格勒因抑郁症自杀身亡。(参阅:贝尔纳·斯蒂格勒:思想的行者)

图1:芮必峰教授讲座中
人是技术动物,技术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技术与时间》第一卷题为《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爱比米修斯负责赋予每种动物以良好的本能,但轮到人类的时候,什么也没剩下来。普罗米修斯为了弥补他的过失,盗取圣火给人类。这意味着,人生来有缺陷,只得运用代具(替代性器具)弥补。代具影响人的生命的本质,构成人类进化的现实。
相对于由遗传基因决定的“种系生成”,在技术中生成的人的存在可称为“后种系生成”。代具性的人随着技术发展而变化。芮必峰教授以媒介来解释:从使用程控电话到携带移动手机,人的属性也在发生变化;同时,报纸、广播、电视也只有在时间流中才生成为媒介,形成居间转化的效果。
人与技术是耦合关系,芮必峰教授以莫比乌斯环隐喻这种关系,两者互为主客,互相发明。从“人的技术”和“技术的人”两个角度观察,人与技术双向运动、交错反射,差异性和相关性彼此包含(可称为“相关差异”)。技术或文化成为自然本性之外的人的第二起源。技术作为一种“外移的过程”,就是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
从“本原的缺失”到“义肢增补”,人的历史由此被想象为延异和增补的历史,主体存在义肢化,其主体性可能以“镜像伪主体”“大写的伪历史”形式存在。芮必峰教授指出,这种批判有助于我们反思数字化、算法化社会的人的境况。
第三持存
《技术与时间》第二卷题为《迷失方向》。斯蒂格勒的解释是,正因人类是人工性和技术性的,所以无法完全在自身中寻求意义,而要到自己制造、发明的义肢中找。这意味着,人是自由的,但又注定漂泊,造成“本原的失向”。19世纪后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使人们在飞速变化的世界迷失方向。
“迷失方向的原初性”就在于,从无方向的处境出发,人们不断寻求着技术坐标定位,建立新坐标并寻找新方向。技术发展打破社会先前的平衡,使人们寻求生成新平衡:社会生成不断适应新的技术生成。总之,失去的方向只有在借助代具通达“已经在此”才能(重新)找到。
在此,斯蒂格勒提出第三持存的概念。以听音乐为例,对音乐的感知是第一持存(感知的心理持存),第一持存与故去经验融合的新想象,构成第二持存(记忆的心理持存)。为增补人的先天不足而产生的外在于人的物性记忆载体,构成第三持存,如留声机和唱片。第三持存改变了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的总体性构境,成为此在进入历史的前提。芮必峰教授补充说,霸王别姬或者马嵬之变我们都没经历过,只有事后记忆被技术物保存了下来,才成为历史。
第三持存是延异、脱域、去与境化的。例如,文字在传播过程中延异,每一次阅读都使之再与境化,重构文本,在时空转换中增补文本。可以说,文字的出现使具体与境发生脱离和中断;历史和知识总是事后重构。芮必峰教授由此引申:媒介的完全“透明”也是不可能的。
人的“存在之痛”
基于工业技术带来的可复制性、可引用性和可重复性,第三持存“工业批量生成”。记忆成了工业原材料,并数字化为流水线产品,突出的趋势是,在场性、与境化崩溃,生命的独特性消失。在工业时间里,人失去真实生命构序的时间,形成人的“存在之痛”。这是《技术与时间》第三卷《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的主题。
如果先天综合判断是理性认识的基础,那么外置的第三持存所附着的“时间客体新工业”,或者说数字化生存方式,已经动摇先前主要依靠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的“综合判断”方式。意识的个性化受到时间客体的工业化生产的阻碍,个体意识汇入数字工业和数字化资本主义洪流,自我落入了“用户归档”的网络制度,生成为“思想的无产阶级”。个性化的丧失导致了普遍的人生苦痛,但而今已无人能够完全逃脱。
“第三持存”造成了不同时间性和空间性。芮必峰教授举例说,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同时收看一场体育比赛,几亿人的意识流在平台时间流中重叠,这在网络时代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在第三持存支配下,第二持存(想象)在第一持存(感知)中启动了遴选过程,而第三持存被百千万意识同时遴选、“调控”和“接受”。第三持存使意识物质化,意识群体变成“观众工业”并构筑起一个广袤的世界级意识市场。这朝向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待引申出一种媒介批判学。
《技术与时间》的媒介学启示
芮必峰教授从三个方面谈论《技术与时间》对媒介学的启示。
其一,反思媒介工具论。媒介不是外在于人的工具,而是人的存在方式。媒介是我们通达对象的界面,是我们与世界共有的皮肤,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感知和意义。
其二,人的媒介性。与其说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如说媒介是人的改变,或者说,媒介是人的延异,创造了人的与技术相交织的生存。
其三,从媒介对象到媒介现象。与其把媒介视为外在的客观对象,不如视为与我们共生共在的现象。例如,新闻在实践中生成,没有超越具体传播经验和交往情境的本质的新闻对象,只有显现在经验和情境中的新闻现象。可以区分技术媒介、非技术媒介、类媒介等媒介类型,以便具体地展开经验研究。

图2:讲座现场
讨论
李龙腾(武汉大学博士生):媒介的内涵从社会沟通的“中介机构”或“中间物”,延展为人与自然的整体的“调解”。两种“媒介”有何差别?人与自然的整体的“调解”在媒介学上有什么意义?
芮必峰:应当扩展对“传播”的理解。原始思维提示,万事万物相互渗透、联系。人与天地万物交流。人在农业革命中驯化动植物后,不再和动植物交流,而是以自己的目的驱使它们。人在工业革命中试图控制自然的力量,变得高高在上。人在启蒙和宗教革命中抛弃了信仰,不再与神交流。人的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发展到极端。人如何恢复与天地万物的交流,是如今交流的困惑所在。
张万洪(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我们研究残障领域的人权法。过去,人们根据身体残缺程度将人分为正常和残疾。现在,人们更倾向认为,残障并非个人问题,而是外部障碍问题。比如,坐轮椅的人没法上楼,是因为没有修建电梯、坡道。人人都需要辅具生存,包括眼镜也是常见辅具。在此,人是代具性动物的观点很有启发。因此,可以从无障碍环境建设出发,重新思考空间、时间和障碍的关系,可以说,每个人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经历障碍期,包括孕妇或推婴儿车的父母、打篮球摔伤的学生、身体不便的老人。
顾兴正(武汉大学博士后):数字化时代的媒介环境带来更密集的信息流动,更频繁甚至强制性的交流,这种交流也是存在之痛,是否存在“减速”的可能?
芮必峰:斯蒂格勒的看法是,技术打破先前平衡的同时,人类需要在实践中寻求新的平衡,但这种寻找,也往往是依托于技术。技术发展带来存在之痛,也需要用技术发展来止痛。
肖劲草(武汉大学编辑):如果说第三持存改变“先天综合判断”中“综合”的方式,那么先天、形式是如何参与第三持存的建构的?如果不从人的视角出发,万物互联、万物皆媒是否区别于关于物质世界的科学研究?
芮必峰:斯蒂格勒指出,意识的代具化过程越来越成为意识的个性化过程的障碍,个体意识的先天、形式的部分和外部的第三持存相互结合、相互改变。思考万物皆媒和把所有物都纳入传播研究是两件事,问题意识在于,从以人为中心的传播关系转向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之间整体性的传播关系。

图3:讨论现场(左上:张万洪;右上:肖劲草;左下:顾兴正;右下:李龙腾)
单波(中心主任):人们的技术批判似乎是恋物癖式的,在直指新技术带来“存在之痛”的同时,又坚定地拥抱技术化的世界,无可避免的技术化命运成为集体无意识。在这一处境下的反思性话语中,人与技术共生的观念流行,凸显技术物的自主性,人类中心主义得到更多批判,尽管人终究无法完全摆脱人的视角。实际上,这些批判性的概念和理论的意义在于,使得人自身处在了不断开放自我的过程中,使自己沉浸于人与万物之间的传播关系之中,而对于这些关系的破坏损害着人类自身的存在。从这一视角出发,可能会和斯蒂格勒的技术批判之间形成关系性的理解。

图4:单波老师与芮必峰老师交流
吴世文(中心研究员):第三持存的概念很有启发性,这种物性载体中的记忆和文化记忆、记忆之场等研究可以关联起来。从时间角度研究媒介,从媒介的角度研究时间,也是芮教授讲座的一个重要线索。这些都有待师生持续的关注与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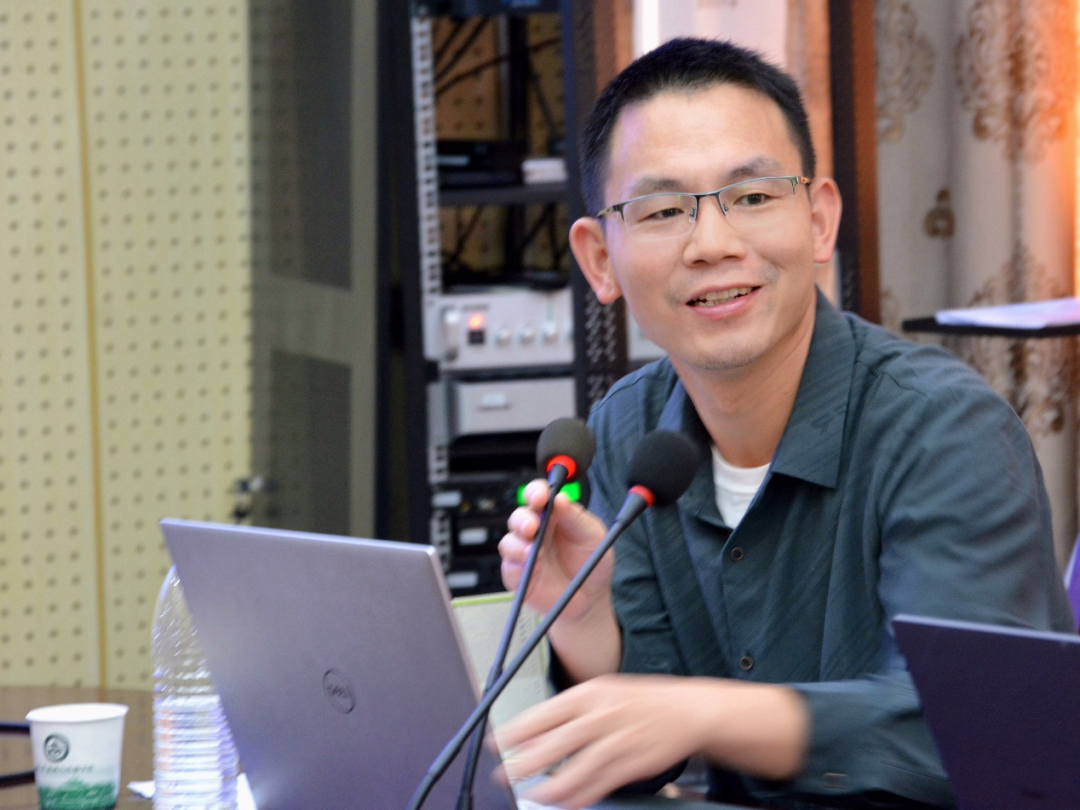
图5:吴世文教授主持讲座并做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