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十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面对他者之痛:战争报道的数字化战场之辩——唐纳德·马西森(Donald Matheson)访谈录》,作者辛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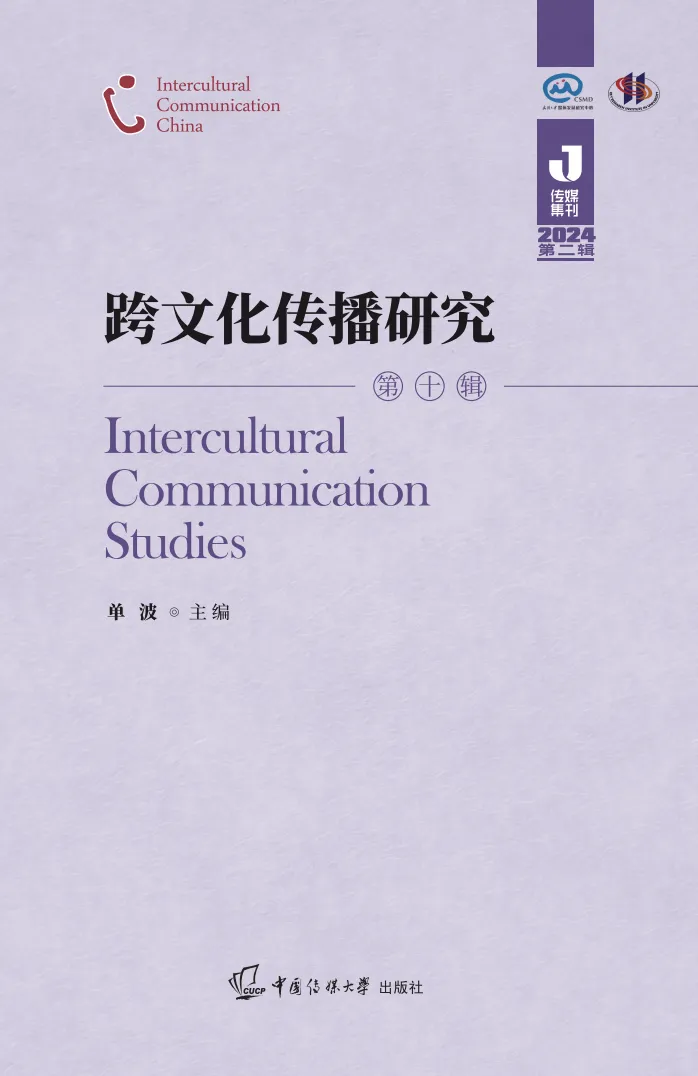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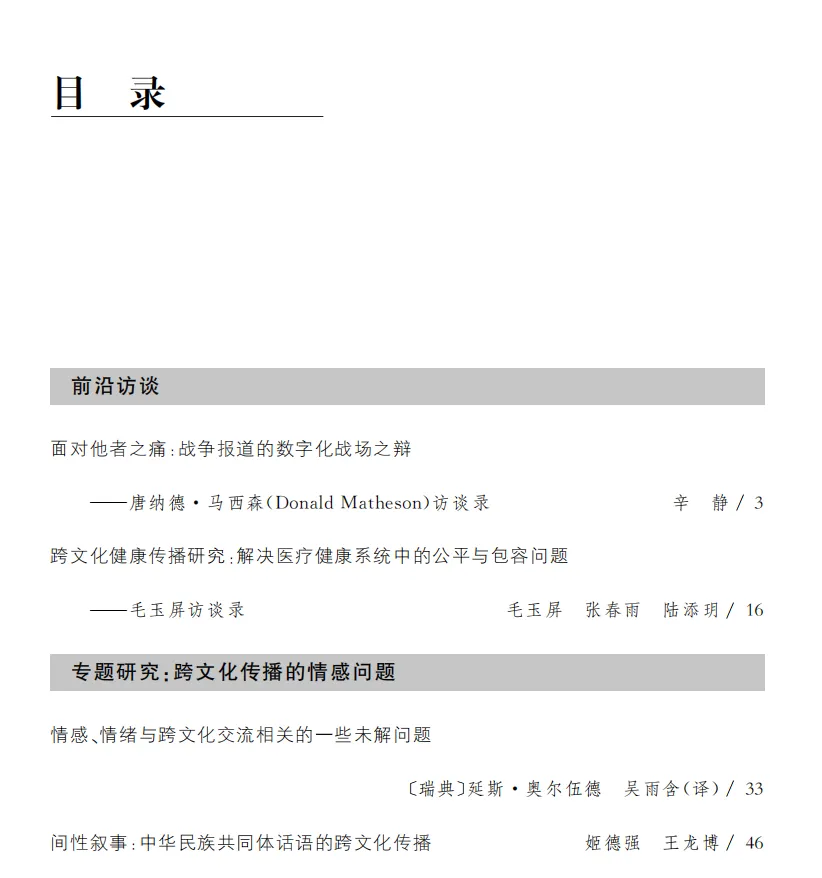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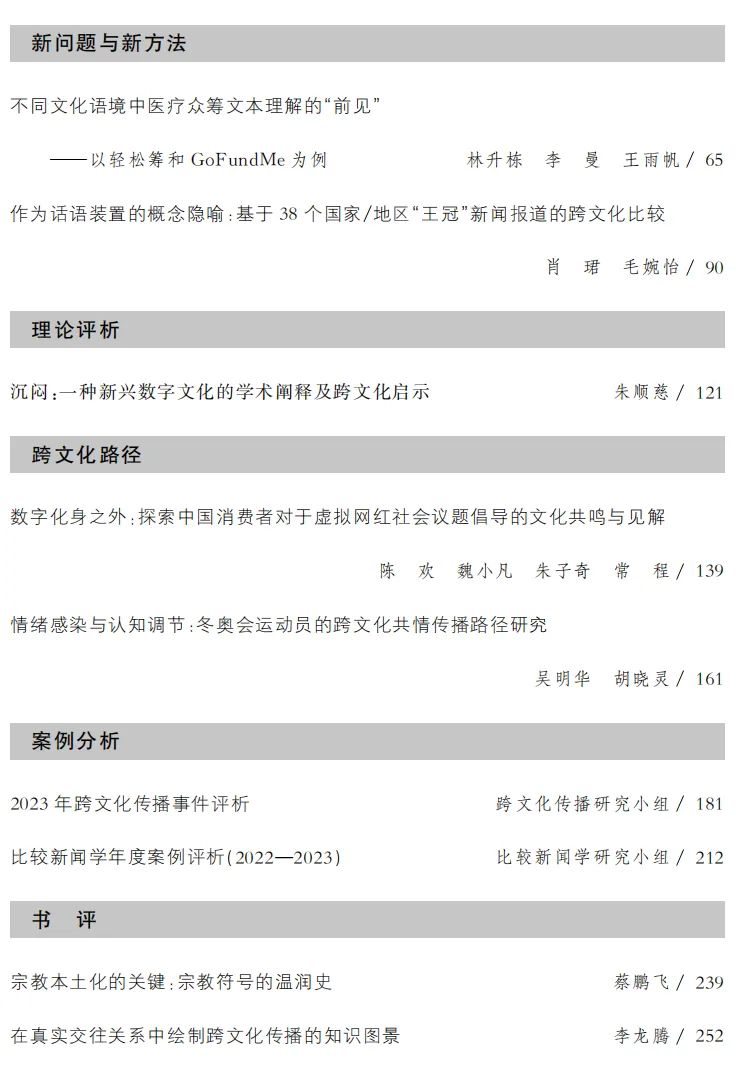
面对他者之痛:战争报道的数字化战场之辩——唐纳德·马西森(Donald Matheson)访谈录
辛静
摘要:在冲突频发、国际局势复杂动荡的当下,战争报道成为国际新闻的焦点领域,亦充当着新闻业的“试金石”。面对他者之痛,面对数字化战场中报道他者的重重障碍,新闻记者如何化阻力为动力,如何帮助公众倾听、理解,甚或与不幸的他者共情,是本文的主要关切。不断革新的数字媒介、根植于全球社会肌理中的文化差异、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等因素,深刻影响着战争报道中关于“我们和他们”的构型(configurations)。识别和挑战这些已被修辞合法化的构型,在日常新闻实践中培养对跨文化群体的敏感性和与之对话的能力,以及培育共享价值观的多重表达方式,是推动善待他者、“慷慨好客”(hospitality)的跨文化传播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战争报道;数字化战争;他者之痛;跨文化传播
对话者简介

唐纳德·马西森(Donald Matheson)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媒介与传播学教授。他著有《媒介话语》(Media Discourses,Open University Press,2005)和《数字化战争报道》(Digital War Reporting,Polity Press,2009,与Stuart Allan合著),并主编多部新闻传播学著作。他是学术期刊《伦理空间:国际传播伦理学刊》(Ethical Spa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Ethics)的编辑,曾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传播协会(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主席。他的研究专长为采用定性或语料库辅助的话语分析方法研究新闻实践、社交媒体中的公共传播和传播伦理。他目前主持的科研项目主题包括围绕生物安全的传播实践和追踪针对穆斯林社群的种族主义问题。
辛静(以下简称辛):在冲突频发、国际局势复杂动荡的当下,战争报道成为国际新闻的焦点领域,亦充当着新闻业的“试金石”。作为战争新闻的研究专家,您发表了多篇关于战争报道的学术论文,并著有《数字化战争报道》一书,是何种契机或缘由让您开始专注这一领域的研究?
唐纳德·马西森(以下简称马西森):我在21世纪初开始研究媒体和战争,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首先,传播在战争期间非常重要,但在采访受限,以及宣传和其他尝试形塑公众认知的情况下,传播面临困境。作为数字化背景下的新闻研究者,我对新闻人推翻或者绕过其中一些限制方面的潜力感兴趣。同时,我想了解战争期间新闻业的变化。尽管压力重重,但战争期间对新闻的需求尤为迫切和高涨,而且新闻业的诸多创新,无论是技术的还是故事叙述方式的,都在彼时出现。
其次,我还对数字媒体中全球化形式的公民社会的产生方式感兴趣,当然没有前者那么强烈。在21世纪初期,一些地方建立了跨国网络,可以越过国家控制共享信息,从而让政府或其他参战者难以滥用权力或在不被广泛知晓的情况下夺人性命。这样的全球化公民社会有一定能力让强国担负责任。但这种力量在之后的几年里已经减弱,或许是因为在美国主导的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暴行之后,以西方为中心的人权话语已丧失了大部分道德力量,还部分由于被社交媒体主导的互联网上的政治更为易怒、更具操纵性。
辛:在您研究的这些战争案例中,文化的差异和误解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冲突的发生或者冲突的加剧?
马西森:文化差异植根于全球社会的肌理之中,不同程度地形塑着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于诸如战争起因、正义性、伤亡情况、目标及手段等战争复杂面貌的认知差异。这些差异在数字平台传播时极易被夸张、放大、扭曲、简化和碎片化,进而引发情绪化的偏见和对抗,例如我近年来研究的仇恨言论(hate speech),这些都为冲突的加剧或者难以调和提供温床。
我认为,误解的产生并不局限于文化差异,还往往源于信息不对称、翻译错误、语境缺失、刻意误导等多种因素。当然,还有数字化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信息茧房”、即时发布和视听媒介刺激等的推波助澜。我要指出的是,当我研究战争报道时,文化差异在一些案例中并不是主导性框架。例如,我认为美国主导入侵伊拉克并不是因为对阿拉伯文化存在误解,而是由于资源和区域权力的问题。文化差异是附属性的问题。
辛:我了解当您研究战争报道时,文化差异不是主要的框架。但您是否认为文化议题是战争研究中没有被充分重视或者说被疏于分析的重要问题?在我看来,仅仅关注资源和权力的争夺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往往都集中在精英和政治人物身上。关于这一问题,我想与您进一步探讨。
马西森:感谢你的回应。是的,我并不是说文化层面不重要,而是在一些个案,如入侵伊拉克案例中不是主要原因(less causative)。但是,来自美国国内的支持是由于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以及对被杀伊拉克人的去人性化,这在美国民众复仇的欲望之下变得很容易。但参与美国联军的大多数其他国家并没有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例如,在英国,就有很多人反对这场战争)。我认为,交战国之所以能获得某种公众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许多社会中,当“我们的”士兵正在参战时,反对战争在文化上是不可接受的(culturally unacceptable)。这就限制了很多记者的报道。我在《数字化战争报道》一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战争报道的修辞(包括话语的和图像的)使“我们和他们”的某些构型(configurations of “us and them”)合法化,人们必须识别和挑战这些构型。
当记者等文化中介(cultural intermediaries)将他人的死亡或痛苦归类为无关紧要的事时,文化层面对于挑战这些中介而言就显得至关重要。25年来,西方普遍存在妖魔化伊斯兰教的现象,尤其是在美国,或许还有法国。乌克兰的冲突在文化上引起了西方受众的共鸣,而叙利亚、苏丹或西巴布亚的冲突则不然。其后果是某些群体的痛苦备受关注,政客们被迫做出回应;而某些群体的痛苦则完全被忽视,似乎未曾发生。
辛:您所说的对“不幸他者”的选择性关注似乎可以从波兰学者莉莉·科利拉奇(Lilie Chouliaraki)所论述的西方观看他者之痛的角度进行进一步阐发。“西方新闻报道具有把苦难等级化的力量,即根据不同地区及人类生活的等级,将苦难分成三六九等”,这在后人道主义时代,成为西方世界凝聚社会团结(solidarity)的手段。“不幸的他者”很不幸地再次沦为被观看的对象、被介入和参与的对象,以及被忽视的对象。您如何看待西方世界中的这种“我们”与“远方他者”的跨文化关系?
马西森:在科利拉奇看来,西方其实是看不到他者的,只是看到了自己,只是在自恋的镜像结构中自我感动、自我赋权,用人道主义的传播结构上演苦难戏剧,利用人类的脆弱性景观来动员广泛的西方公众。阿伦特认为,脆弱性是一种人权,却被极权主义的民族国家所使用,从而产生“非人化”问题。也就是说,人性被选择性调用,以便与某些群体交际和联合,从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我们”和“远方的他们”。
辛:科利拉奇曾经列举了作为“讽刺的旁观者”(ironic spectators)的诸多案例,并指出救灾被转化为西方公众自我娱乐、自我确认的派对,以及面对他者、他处灾难时的自我团结,这不是信念而是选择,不是愿景而是生活方式,不是他人而是自己。那么,新闻人到底能如何突围呢?
马西森:我对她作品的解读是,她在评价作为讽刺的旁观者的风险。她认为新闻人将我们召唤到了不同的观众角色之中。一方面,商业化的媒介体系让我们持续专注于频道或在订阅的资源中不断滑动;另一方面,新闻人可以找到一个有意义的视角来讲述故事,而不拘泥于某些逻辑方式。我认为科利拉奇的论述有助于让我们反思是什么新闻使我们暂停或不再滚动鼠标,而开始聚焦。我注意到我的新闻学的学生想写作让人们停下来关注的新闻,这些故事是关于边缘人群,或者挑战我们日常现实的人的。这对于我和我的一些学生来说虽然是相当理想化的,但我发现这有助于思考我们应该对战争报道提出什么要求,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新闻实践中培养对跨文化群体的敏感性和与之对话的能力。
辛:您在著述中探讨了战地记者报道他者的诸多困难,比如访问受限、信源偏向、语言和文化障碍、道德和伦理困境、政治干预等,这样看来,新闻媒体在战争新闻中对他者的报道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主流媒体而言,存在破局之道吗?
马西森:我倾向于将之视为一种张力(tension):许多记者都有驱动力去打破对他们的限制,以及尽可能摒弃我们前面探讨的苦难戏剧。那些报道当代战争的、我熟悉的英美传统记者,往往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对权力持怀疑态度、雄心勃勃、富有竞争力。在纸质新闻业经济被社交媒体公司的力量破坏之前,也就是西方媒体较为宽裕时,许多记者采用数字工具在冲突地区进行报道,采访更广泛的信源,并在形式上不断尝试和突破。我们看到了一些创新项目,比如克里斯·奥尔布里顿(Chris Allbritton)的独立报道。他带着网络粉丝为他购买的卫星电话,从土耳其徒步翻山进入库尔德斯坦,以非常独立的方式进行报道。他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更多的是关于普通伊拉克人的故事,而不是战争推动者的框架化故事。
然而,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社交媒体将新闻业从公共辩论中剥离出来。社交媒体中众声喧哗,出现许多相互竞争和相互矛盾的声音,新闻媒体在努力核查事实,并将其融入报道中。因此,战地记者现在不那么重要了。与此同时,西方新闻业已经失去了其作为独立观察者的文化地位,这导致记者在每次冲突中被杀害或被监禁的人数不断上升。在加沙,以色列政府没有被追究杀害记者的责任(据记录,在冲突开始的18个月内,总共有100名记者死亡)。因此,战地记者已被卷入信息战。这或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记者将自己定位为独立观察员是20世纪中后期的一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有在西方对全球媒体的新殖民主义控制下才有可能。但他们成为被杀害或被监禁的目标却是新鲜事。
辛:您在著述中经常比较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对于同一战争的报道,您似乎倾向于认为自媒体、公民记者、独立记者等具有更大潜力来打破政治和文化的界限,让战争面貌更接近客观和真实。不知道我的这一理解是否准确?在今天,您依旧持此观点吗?
马西森:正如撰写 We the Media 的丹·吉尔默(Dan Gillmor)和其他人所描述的那样,自媒体是已经过去的时期的产物。那是一个批判性思考者转向使用数字工具的时代。现在,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自称独立的声音。在战争时期,政治行动者会提供其中一些声音。与此同时,记者可能会发现像X(原Twitter)这样的地方充满了对他们的暴力批评,导致他们纷纷从这些互动媒体中撤离。疫情期间,许多记者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记者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建立良好的联系和网络,而不是声称为了保证讲真话要具有彻底的独立性,因为这种说法已经变得难以为继。记者的目标可以是帮助受众与冲突地区的士兵和平民建立联系,并被视为混乱战争中的可靠指南。这凸显了记者的情感工作,要求公众予以关心和关切,这一点在战争报道中一直存在,但在研究中却不太突出。例如,我认为关于苏丹敌对军阀之间的战争的优质新闻报道建立了关怀的结构框架,使人们超越曾经看待苏丹的无知、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与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建立联系。从真正人道主义的视角出发去报道遥远他者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极具挑战性。
辛:在全球矛盾冲突频发的当下,众多受众,尤其是非冲突国的人们似乎只是“偶遇”难民新闻,比如3岁的叙利亚男童在海滩上的照片、奥运会上的难民代表团等。您认为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受难者的低曝光率?这样的境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马西森:我不是难民报道方面的专家,我住在新西兰,这里没有受到非官方移民潮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看到的是强权国家拒绝承认全球化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影响,以及那些破坏稳定地缘政治的行动所造成的影响。难民流动主要是由于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现在巴勒斯坦的战争。强权国以及这些国家的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对此负有很大责任。在中国、德国或澳大利亚鲜有讨论难民逃离绝望生活的报道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几乎没有政治增效。好的新闻报道会讲述这些故事,但这种报道很少。与此同时,诸如联合国等通过长期措施应对贫困和不稳定的国际机构组织,由于全球强国将其边缘化而失去了力量。改变全球强权政治需要大量的新闻报道。
再如我现在脑海中浮现的罗兴亚人的例子,他们被描述为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无论是在地缘政治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罗兴亚群体都难以引发广泛的报道兴趣,除了一个镇压型的亚洲政府外,罗兴亚群体没有其他的叙事意义。罗兴亚人是穆斯林,但完全不符合西方伊斯兰政治的脚本。因此,他们的故事缺乏简单明了的意义,编辑们很难证明自己对于他们的关注是合理的。现有100万左右的罗兴亚人,大部分在孟加拉国,他们是无国籍的、不受欢迎的、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的。我想要看到更多针对这一群体的新闻报道,但同时我也能从意义生产层面理解西方新闻媒体忽视他们的原因。中国媒体或许对于这个群体有着不同的报道。
辛:您所说的让我联想到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话语:“旁观另一个国家发生的灾难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体验”,“有些人的痛苦比其他人的痛苦更能引起观众的内在兴趣(假设痛苦被认为是有观众的)”。您能进一步谈谈对此的看法吗?
马西森:桑塔格说的当然依旧适用。当观众和讲述故事的人都不存在关心和关怀的关系时,战争和虐待他人的事情就非常难以沟通。不过,我不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人的痛苦是可以被讲述的。正如我们前面提及的科利拉奇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将苦难政治化(politicize the suffering),从培育公众而不仅仅是受众的意义上讲,我们需要围绕全球正义建立全球化的关怀结构和共同价值观。当然,这是困难而抽象的。一个加沙儿童正在挨饿,而几千米外的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却拥有充足的食物,我们距离理解这样的图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缩短这种距离是新闻业的使命,也是我们作为学者通过批判所能尽到的部分职责。我想起了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和他勇敢的编辑们在1979年通过纪录片向英国观众讲述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种族大屠杀的故事——直到他把这个问题公之于众,观众才开始关注。
辛:能结合战争语境谈谈您对新闻记者作为灾难的旁观者的思考吗?
马西森:在我看来,这是电视带给我们的一种现象,部分原因是电视将大众聚集在一起。网络中的受众更为分散,更有可能直接面对现实,或许不太容易被基于国家的框架所定义。这对于镜头如何声称记录真实是有影响的。网络媒体中的新闻文本,作为现实的证据比作为所发生的事情的权威描述更具可读性。
辛:不断革新的数字媒介,比如监控录像、无人机视频等是否有助于让人们“看见”边缘人群以及遥远的他者?
马西森:我们身边现在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视频媒介,以至于我不再像15年前那样乐观。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令人不安和不舒服的事物往往没有市场。如果像我这样研究冲突的媒介学者都不得不强迫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观看加沙人的视频,那么也不能指望数字媒体能够弥合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权力所造成的鸿沟。这需要新闻界和民间社会组织能够过滤、核查事实,并解释部分视频内容。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采访始终受到限制,并且受到那些不希望我们看到战争影响和对人民控制的势力的限制。
辛:您似乎对视频媒介帮助人们“看见”遥远他者不那么乐观,那么人工智能呢?被称为具有“魔法”的ChatGPT等AI模型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动您前面谈及的“优质新闻”(good journalism)的生产和传播,以及帮助我们与遥远他者建立“联系”(connections)?
马西森:我一直对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和搜索式人工智能(search AI)的成就感到惊讶,同时,我也应该以更审慎的态度来看待它们的“魔法”。一方面,这些工具依赖于现有的数据,因此它们无疑会再现用于训练这些模型的源头的偏见和文化分歧。另一方面,我想知道人类生成的文本(human-generated text)是否很快会受到重视,即人们试图在其中与他人交流。人工智能可能会产生一种讽刺的效果,它展现了曾被宣称只有人类才拥有的价值观,如真实、关系和关怀,以及更大的文化力量。当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媒体时,与我们有联系的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故事就会发挥宝贵作用。
辛:也就是说您还是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潜力。那么,您是否接触过一些关于战争的新闻游戏?对这类以真实战争事件为游戏背景,能让玩家通过角色扮演体验战争的媒介产品,您有何评价?
马西森: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认为这种类型的游戏鼓励我们体验不真实的场景,而且没有后果。我们更倾向于通过以真实方式讲述真实故事并建立真实关系的方式来学习。我想知道,将游戏在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与游戏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混为一谈是否也是一个错误。也就是说,我认为游戏对改变政治没有多大作用。但我确实同意,我们不能依赖45年前对皮尔格这样的人有效的方式来讲述关于权力的新闻。我发现社交媒体上的短视频是一种强大的模式,尤其是当它们是原始的、主观的和情绪化的时候,因为它们将我们与经验联系起来。当这些强大的媒体模式被诸如专业记者或其他公众人物等强化和组织起来时,我们需要警惕社交媒体是由以盈利为导向的公司运营的,而这些公司几乎鲜有道德基础。
辛:我理解您对于将灾难变成游戏这种以娱乐为导向的媒体形式的担忧。但或许对于数字原住民、青年一代来说,游戏是较能触达和打动他们的媒介形态。诸如BBC、《卫报》等主流媒体依托真实难民故事制作了感受逃亡之旅和战乱之苦的新闻游戏。您能否谈谈主流媒体制作战争类新闻游戏的动机和成效呢?
马西森:新闻游戏的媒介逻辑可能适用于年轻一代的用户。我可以看到叙事文本,比如你提到的那些互动游戏,它们是帮助人们理解冲突局势的媒介。在互动方面,我发现的最有力的例子是半岛电视台的一部关于黎巴嫩难民营的互动纪录片《生活暂停》(Life On Hold),通过影片中的互动,我们可以探索不同的叙利亚青年人的故事。对我来说,它的力量在于视频中人们发出的声音,而不是“玩家”对他们的叙事探索。所以我更看重的是这些文本让我们更接近他人的经历,而不是文本创造了替代性体验。
辛:数字图像和影像的广泛传播往往能引发更为强烈的舆论反应。这种颇具威力的传播方式日益成为战争的工具或武器,成为权力争夺的焦点,您的著述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在批判对于数字图像的操控。而您刚刚提到的例子是较为积极的。在您的观察中,是否还有通过影像的广泛传播缓和冲突、减少误解,甚至达成理解和共情的案例?
马西森:关于这一点有很多辩论。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国际新闻,特别是战时新闻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主要影响作用,被称为“CNN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图像是强有力的——当政治运动强有力地利用它们时;当人道主义政治强大而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薄弱时;当图像中的人和观看者之间建立情感联系时。
也就是说,强大与否是需要人们去放大这些图像的。因此,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使我们的公共结构(public structures)发挥作用,而不是寄希望于影像技术发挥功效。媒体上有很多罗兴亚人在缅甸受苦受难的影像,几年前还有很多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受苦受难的影像,但这些影像的存在并没有减轻他们的苦难。
辛:那么举例而言,被凝固汽油弹袭击后惊慌逃跑的越南女孩的新闻图片被认为是美国反越战运动的导火索,改变了战争进程。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引发了人们的共情?
马西森:那张著名的越战女孩新闻图片非常直接而震撼地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无情,引起了人们对生命的怜悯,对生存、安全等基本需求的共鸣。美国宣称的生命至上、尊重人权等价值观与战争对平民的摧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强烈的视觉冲击成为共情的催化剂,点燃了早已积累的反战情绪。有些评论会将之视为新闻的力量,称其为无冕之王的高光时刻;还有些则会谨慎地声称是媒体主动曝光此照片,会认为这是美国统治精英内部关于战争本身存在政治对立的结果。
究竟是新闻的力量还是权力的游戏,这一问题在当下似乎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你会发现,现在很难再重新看到这张照片,它已成为标志性的(iconic)符号,也因此失去了一些真实性(realness)。但我想知道这照片的力量是否与它让人们面对他人的痛苦时刻有关。如果你把目光移开,你就会把目光从真实的人们的痛苦或死亡中移开,所以这些照片能够消除人们的偏见(dismantle people’s deflections)。
辛:您一如既往地坚持着批判性思维方式,在您研究了这么多战争报道案例之后,您对新闻业的未来持何种态度?能否举例说说您的一些独特发现?
马西森:是的,我一直强调政治化的世界主义(politicized cosmopolitanism),但我仍然对新闻业的力量持乐观态度,因为我相信记者具有帮助人们相互理解的能力。这种能力起起落落,因为新闻业并不是独立的权力来源。但我仍然看到许多人寻求新闻工具,并改造这些工具,以引起人们对不公正现象的关注。举个例子,我所在大学的一名博士生Wensislaus Fatubun是西巴布亚的活动家,他培训人们通过手机、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些小故事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们以乐观和正义感为基础,同时揭露了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但要做到这一点,它们需要经过审核,并且需要制作精良的视频。在全球差异中培育共享价值观的多重表达方式,这也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有益尝试。当新闻业将讲述真实故事的技能与对正义的承诺结合在一起时,它就具有一定的力量。
辛:谈到跨文化传播的有益尝试,您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这一概念?我们应该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西森:我赞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享”(shared)一词的对话推动力(dialogic impulse),以及“共同体”(community)一词对建设美好共同未来的社群主义关注。但我对由此产生的“一个共同体”(a community)持谨慎态度,因为我们将永远留在由不同的价值观塑造的不同的社群中,重要的是不要忽视其他社群,如果那样的话,就只是强加了对世界的另一套理解而已。
在如何推动方面,对我来说,所需的关键要素是更好地倾听。例如,BBC在其最佳状态下扮演的角色是,倾听那些在公共讨论中没有被听到的人的声音,并利用其强大的力量帮助他们被听到(我所说的是“处于最佳状态”时,因为它依旧是在政治约束下运作)。
但是在当今的全球范围内,数字技术在增进对差异的理解方面收效甚微。社交媒体的结构更像是个体自我表达的管道(a say-you-tube),而不是一个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对集体利益的承诺基础上的团结和关怀的网络。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下,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强大,它们总在告诉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想要什么。
所以我的总体看法是,我们需要怀有远大的抱负,但通过研究那些讲述冲突故事的人,我们能学到的还包括对目标保持谨慎和谦逊这一点。
辛:您所说的让我联想到法国学者探讨的“共通体”(Communauté)概念,它包含着差异性和多元性,强调更广泛、更包容的联系和共享。您能谈谈对此概念的理解吗?
马西森:“共通体”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概念,试图为现实社会中的冲突和分裂提供解决方案。我的疑问则是如何实现这一概念。这也让我想到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论述:“如果一个人能够拥有、掌握和了解另一个人,那么也就否定了那个人的他者性。”(If one could possess, grasp, and know the other, it would not be other.)只有当公共媒体认识到这种差距,即人们可以在与他人见面时通过倾听和关心他人来填补间隙,他们才能在产生理解方面取得最大的成就。罗杰·希尔维斯通(Roger Silverstone)曾使用“慷慨好客”(hospitality)一词来形容采取这种做法的媒体,这个词在许多文化传统中都有共鸣。在冲突时期,也就是这场讨论开始的地方,要做好客是困难重重的,而更重要的则是公共空间不能成为暴力的延伸。我们距离实现“共通体”,以及实现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社群主义愿景(communitarian vision)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常生活视域下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与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BXW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用参考
辛静.面对他者之痛:战争报道的数字化战场之辩——唐纳德·马西森(Donald Matheson)访谈录[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4(02):3-15.
作者简介
辛静,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电子邮箱:6755142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