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十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作为通道的河西走廊》,作者冉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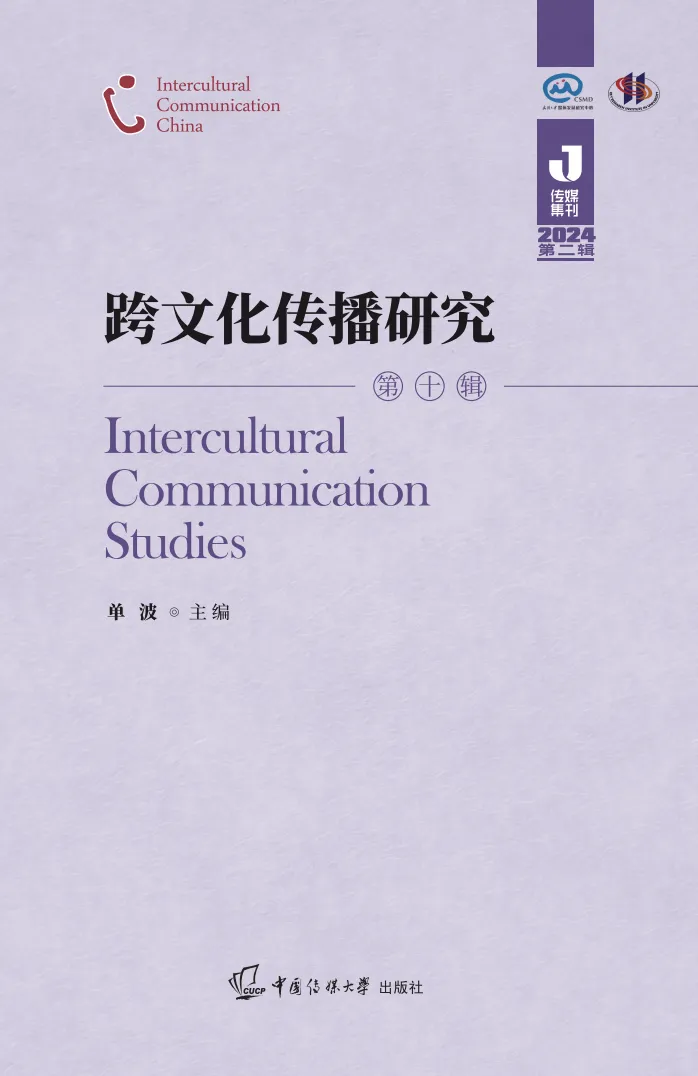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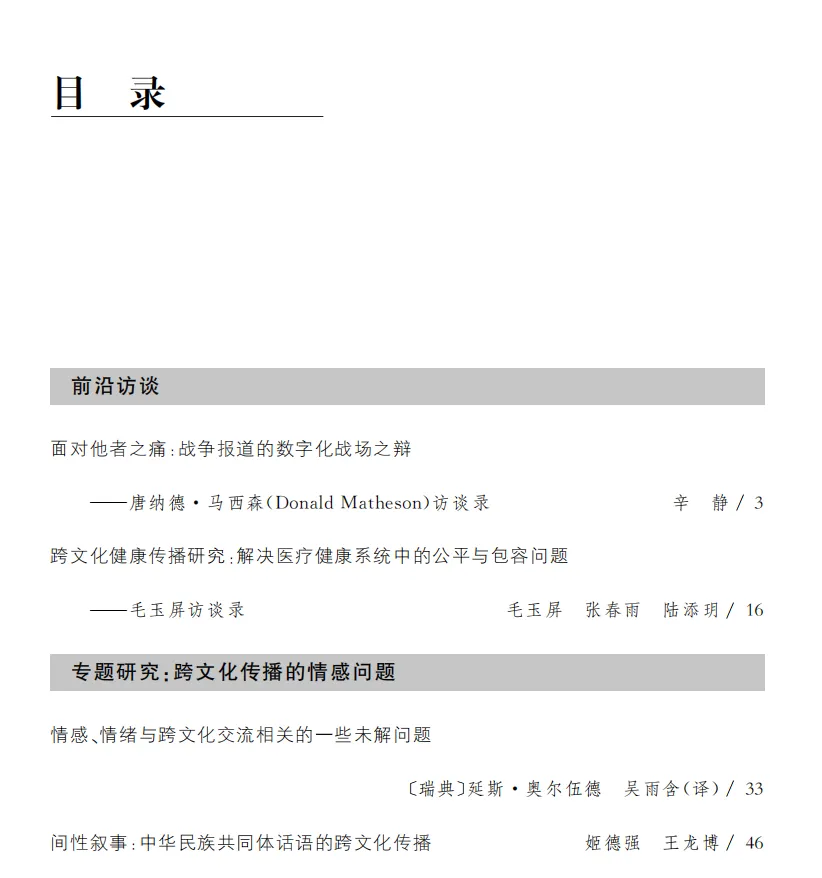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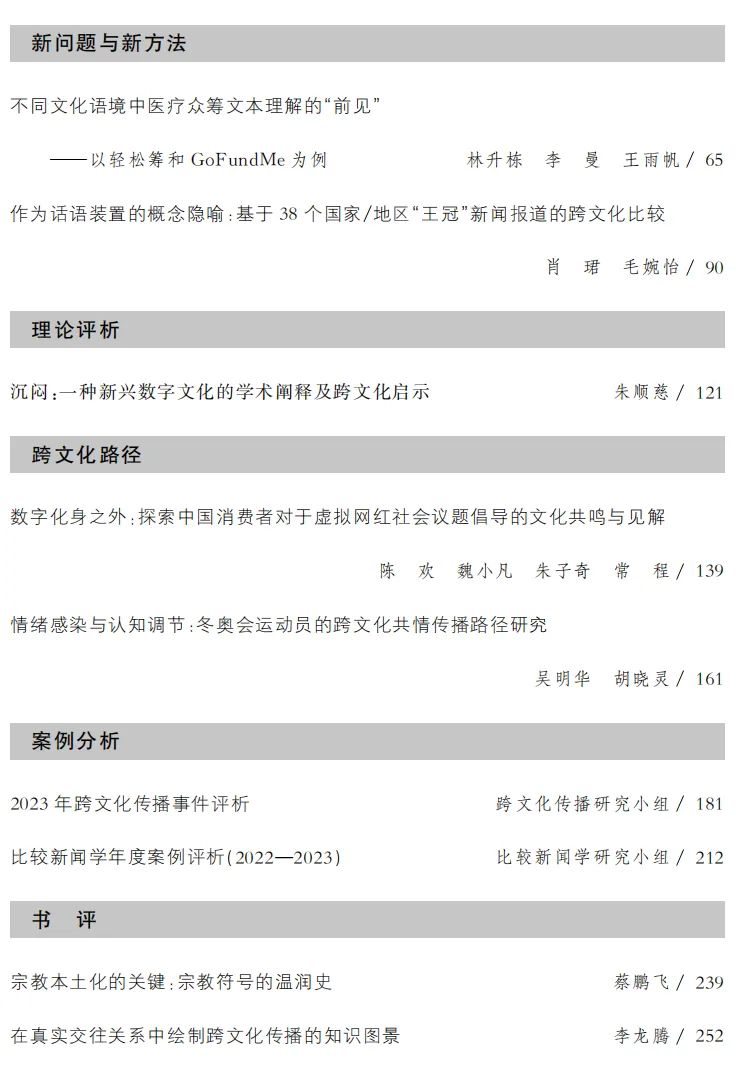
作为通道的河西走廊
冉华
“走廊”“通道”首先都是具有地理属性的概念,强调自然形成,通常指连接两个或更多区域的狭长地带,也表征着不同地理单元之间的界限。不过,在社会人类学提供的解释框架里,“走廊”“通道”中物品、资源和人的流动必然会衍生出新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空间,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互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敦煌之所以成为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唯一端口,也是因为它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一端是塔里木盆地、瓦罕走廊、楚河河谷,西去波斯、阿拉伯、罗马,另一端则经河西走廊越六盘山直抵关中大平原。东西方的交往就这样沿着一条大走廊延展开来,而敦煌则完美处于这个大走廊的中心。于是,敦煌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熔炉:多个民族聚集,多种宗教信仰共存。距今大约1600年前的南朝史学家刘昭也曾用“华戎所交一都会”来概括敦煌的特征。交者,俱也,合也,共也。可以想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形色色、无限丰富的管道将“华”和“戎”汇集到了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在形塑敦煌这一文化接触地带的历史逻辑中,河西走廊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尤为值得关注,它为我们理解敦煌的大而盛提供了一种“接触区”的多元视野。
作为实体通道的地理存在,河西走廊具备一种先天性的比较优势,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说就是资源禀赋。其因位于黄河以西,狭长且直形如走廊,故名河西走廊。它恰好处于中国西部西出东进、南来北往的十字路口,是中原通向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这就注定河西走廊必然要成为东西方交流史上的黄金通道。当然,古代东西方交往并不只是通过河西走廊这条路线,考古资料显示,欧亚草原是最早沟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最晚在公元前2000年,我国中原地区已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史前时期的先民们遗留下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足迹,这也被视为草原丝绸之路的渊源。但显然,河西走廊这个农业区的丝绸之路才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交通路线。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指的正是这条从长安洛阳出发,沿河西走廊向西经过中亚,直至地中海的商贸交往通道。
不必讳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总是关乎一个民族的宏图大志。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目标是联合大月氏抗衡强大的匈奴以维护中原政权,而那些绝非中原所能见的西域风物也开阔了汉帝国的视野。汉武帝决心打通河西走廊这条咽喉要道以保障中原与西域的畅通往来。自此,河西走廊开始担负起经略西域的地缘政治使命。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的绿洲、丰富的光照资源和优质的冲积平原土壤,让这个狭长的区域逐渐发展出了依赖灌溉农业生存的农耕文明。尽管连接东西方交往的通道不止河西走廊,但作为农业区的河西走廊不仅为人员来往提供了充分的安全性保障,而且使得沿途商贸的常态性交易成为可能。《汉书·匈奴传》用一句“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写尽了当时河西走廊的繁茂与丰饶。
人类的交流确实具有行为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带来了文明和文化的流动与散布。但在早期社会发展中,这种流动与散布并非毫无阻隔,自然环境、政治制度、思想观念都是影响交流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河西四郡的设置代表着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为敦煌和河西走廊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度性支持。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甜水井附近一处名叫“悬泉置”的古代邮驿遗址被清理发掘,出土了大量有文字记载的简牍,更新了中国考古记录。古时邮驿因其“通远迩于一脉,继往来以无穷”而被称为“国之血脉”,作为河西要道上一处集传递律令、上报军情、接待宾客为一体的综合组织机构,悬泉置见证了中原王朝对边远地区的有效管辖。当然,我们不能偏狭地认为郡县制只是为正统的儒家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支持。自汉武帝开始推行“列四郡据两关”、移民实边和屯田政策以来,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治理逐步减少了政治动荡对文化交流的影响,经济的繁荣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中原文明的影响力才得以越过乌鞘岭远及西域大漠深处。
显而易见,即便是在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对河西走廊的利用也绝不止于一种物质性的空间。作为具有学术原创意义的研究,“走廊视角”是费孝通先生从微观的社区研究转向宏观民族区域历史思考的结果,强调对“人”的迁徙流动与文化间交互接触的关注,强调“走廊”本身所蕴含的一种流动特性和关系结构。基于这一理论认知,可以说“河西”是地理的界定,而“走廊”则升华为一个具有人文意涵的符号,是一种具有黏合作用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空间。走廊提供了不同地理板块之间的连接,同时又因为这种连接带来的文化交际和互动关系进而呈现出“过渡性”或者“中间性”的特征。
尽管文化的定义是复杂多样的,但关于文化的结构性、流动性特质的判断却是一致的。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的意义价值与生活方式,文化是积淀的结果,“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同时,文化又具有在历史与空间中流动的特质,即所谓“行走的文化”。在某个特定时期,如发生战争或自然灾害时,这些紧急情况的出现都会带来人群的流动,也就相应地形成了文化的流通。河西走廊一直地处“四大文化圈”之间,当周边地区发生非常态的社会危机时,河西走廊便成为一个危机缓冲地带、一种减压阀的存在。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汉族流寓河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经过汉帝国300余年的经营,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成为一个将中原农业带和天山以南农业区连接起来的新兴农业带。它不仅为穷途的魏晋名士提供了躲避战乱的生息之地,也使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在河西地区得以延续,河西走廊儒学之风盛行也就此成为历史上西域地区一个特殊的文化记忆。1944年,陈寅恪先生出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在探求隋唐文化源头时发现了“凉州因子”“河西遗传”。孤悬天末的凉州转移保存了中原学术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怠危之际的避难所。先生发现这一史实时,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际,这一跨越千年的回响真是令人感慨。
依据文化适应性和传播性理论,文明文化的结构性与流动性倾向受地质条件的影响非常之大。“具有一定空间距离的不同区域的内生型文化要素积累到特定阶段,将形成复杂性高级文化层,并出现溢出效应和磁石效应。”当两种文化重叠时,人类文明就会在交汇与重叠之中孕育起来,因为“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随着人类纪定居文明和车船文明的发展突破,地质环境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也许人类纪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性概念,但人文地理学、社会人类学及相关学科在帮助我们建立关于文明和文化深层逻辑的分析框架时仍具有启发意义。考古学家童恩正关于“我国从东北至西南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阐释也彰显了这一价值。他说,如果站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纵目祖国大地,就会发现一北一南两列山峰及其邻近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这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勾勒出“最初的中国”,河西走廊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边界基本重合。受其启发,牛津大学考古学家罗恩教授继而提出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人文地理学概念——美丽的“中国弧”。她认为古代中国与欧亚草原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它拥有自己独特的面貌,正是这个美丽的中国弧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因此,对于这个区域的关注是理解中西方交流的关键所在,敦煌与河西走廊恰好处于这个美丽的弧线上。
如果我们超越自然地理层面去界定河西走廊,就会发现走廊的廊道形态并非只取决于山川走势的地理特征,也不再是一种静态的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地质地貌,而是动态的社会与文化关系网络。我们正是基于这一维度去理解河西走廊这个置身于不同民族、文明边界的文化“隙地”,理解河西走廊对敦煌这个文化接触地带的形塑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接触、互动形成了特定的廊道区域,走廊不仅代表着不同地形之间的过渡,也意味着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汇聚和嵌合,意味着多元耦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是不同文化和文明板块之间构建文化交流空间廊道的核心驱动力,是一种巨大的跨文明融合的能力,敦煌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因此被造就。“何以敦煌”,对这一宏大深邃命题的解读还是季羡林先生概括得最是精要:“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文明体量让中华文明呈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中华文明能成为唯一不间断的文明,并非一种文化的侥幸,实为历史的必然。
行文至此,忽然记起多年前那个四月的黄昏,我第一次来到敦煌。因是淡季没有直航,我们在戈壁公路上驱车六个小时。不同于草长莺飞的南方,沿途只是大漠孤烟的一派苍凉和冷寂。远远望见市区灯火,突然想到那些时空隧道深处的先民们,依凭着沙漠之舟经年累月地跋涉于西域。当他们踏着暮色走进这座千佛艺术之都时,也有与我一样的莫名的感动吧。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冉华.作为通道的河西走廊[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4(02):1-5.
作者简介
冉华,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