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十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比较新闻学年度案例评析(2022—2023)》,作者比较新闻学研究小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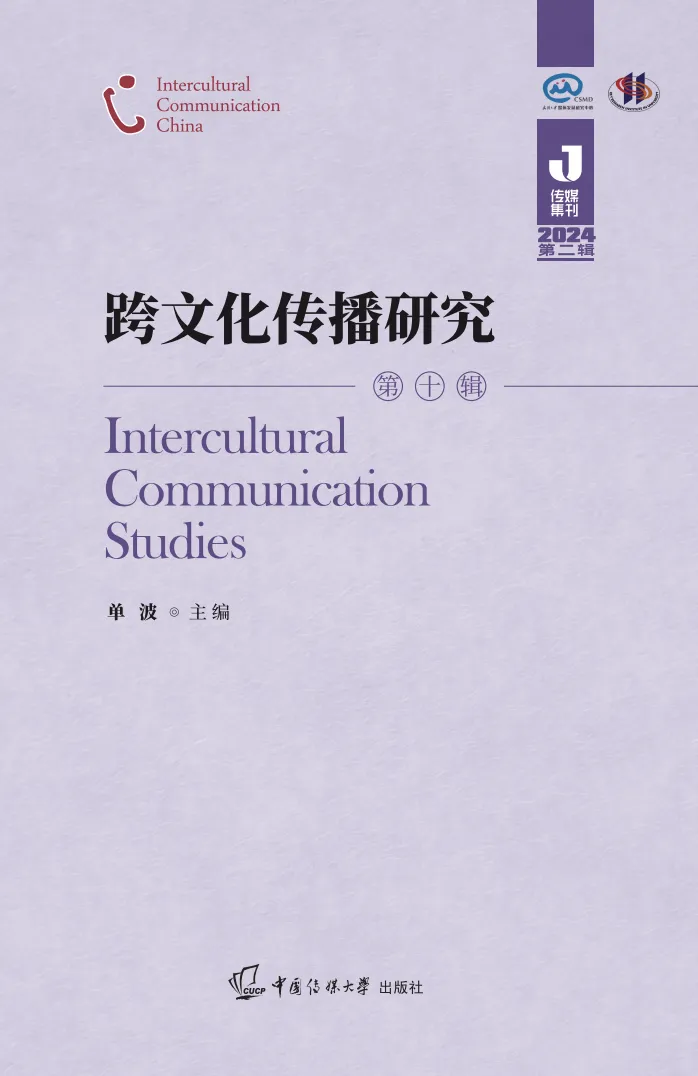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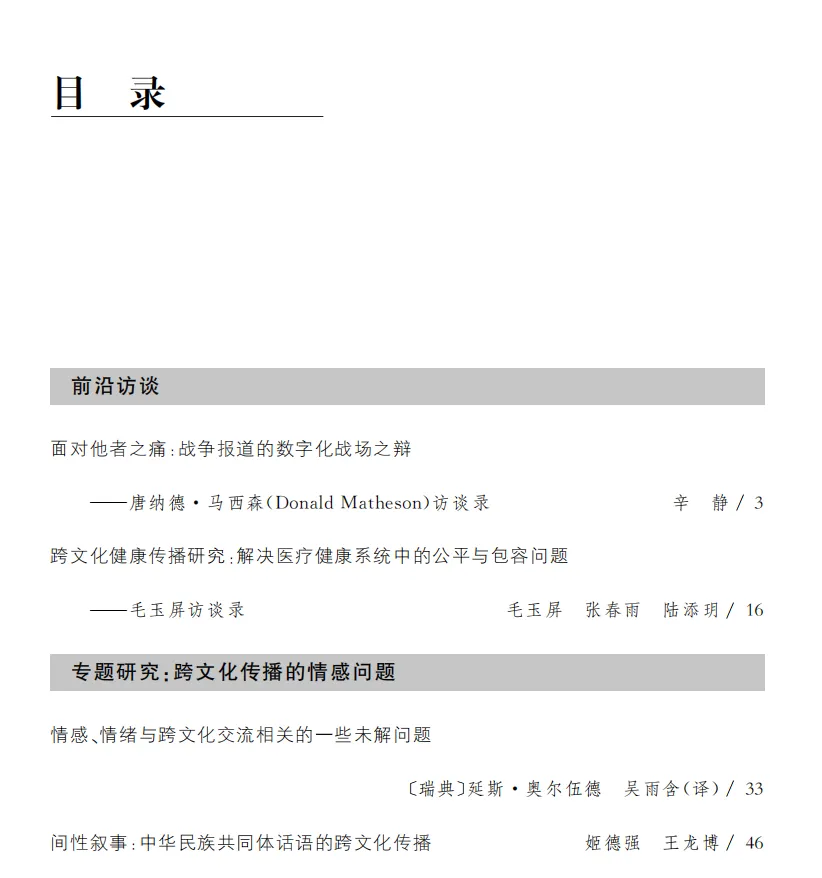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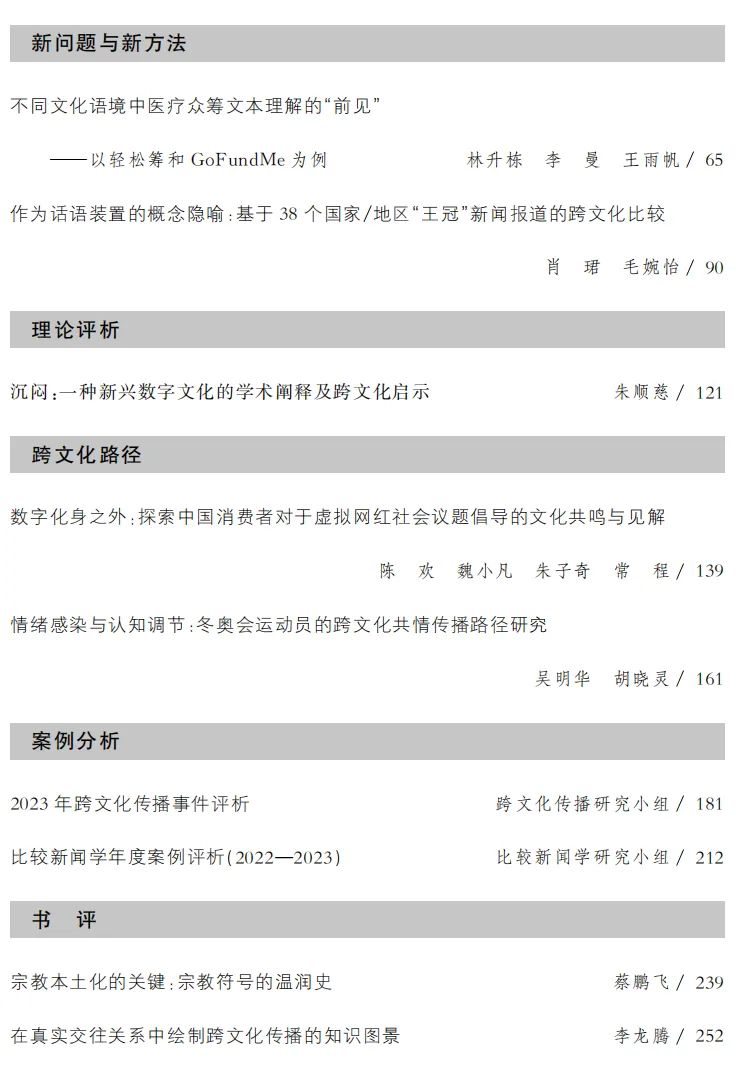
比较新闻学年度案例评析(2022—2023)
比较新闻学研究小组
摘要:本文从2023年发表于英文期刊中的数百份比较新闻学研究中选取10个典型性案例进行评析,以窥探该领域最新进展和前沿趋势。总的来说,它们分别从新闻媒体与所处的背景、新闻媒体及从业者与平台的关系、另类媒体、新闻读者和用户对媒体与记者的评价及反应四大领域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案例1、2分别从新闻媒体所处的新闻场域和民粹主义背景来分析其差异及相似点。案例3、4则从媒体平台角度考察记者在不同媒体平台展现出的差异化新闻角色,以及记者对不同科技公司的媒体监督。案例5、6主要以另类媒体为中心,考察它们在呈现事实和用户感知中与主流媒体的异同。案例7、8、9则主要考察读者和用户的新闻信任、对新闻推荐系统的评价、作者性别对用户评价的影响。最后,案例10侧重分析记者应对网络暴力的结构性难题。总的来说,相较于往年,比较新闻学研究在议题上仍然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态势,但是宏观层面上对新闻制度和文化的比较分析进一步弱化,更加侧重于考察微观层面上与用户的互动。
关键词:比较新闻学;新闻媒体;语境化;平台;另类媒体;用户评价
案例1: 世界新闻场域的同构性
以《关于电视》(On Television and Journalism)为重要节点之一,布尔迪厄的新闻场域(media field)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科,启发了新闻生产、新闻场域的自主性、记者社会资本的转化等一系列研究。作者Jan Fredrik Hovden在《英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到处皆同?以新闻业为例探讨国家社会场域的结构同源性》正是基于以上内容,讨论了一个尚未被充分讨论的面向:新闻场域的同构性(homology)。
既有的研究经常讨论某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场域之间的斗争关系,或者一个场域内部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而场域的同构性重申了一个主题:社会结构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即使不同背景的行动者的意图大相径庭,场域内部和场域之间的联系也仍旧能展现出相似的倾向(如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合法化)。这种同构性强化了跨领域的冲突特质,也进一步促进了场域比较的可能。但是一直以来,同构性因其分析适用于法国及西方世界的现实而受到普遍性的质疑,布尔迪厄本人也对“系统之间的比较”的操作性有所怀疑,因此尤其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本文提出一种“逆向比较”(reverse approach)的思路,来为不同结构/系统之间的比较提供一种可能性。通过记者自身的职业认同、角色感知、自主性调节等指标,来反向定位其所处国家的新闻场域的特质。这种主观感知与客观结构的互补既能够展现出新闻领域内部的异质性和动态性,也没有忽视结构与能动性互相塑造的社会基本规律。
研究使用了Worlds of Journalism在2013—2016年第二阶段收集的来自全世界67个国家的新闻记者的数据(n=27567),研究者从中选择了21个问题作为主要的活动变量,然后将新闻记者的社会特征、性别、从业资历、职位等信息作为附加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场域理论正是受空间属性启发而来的一种理论想象,作者恰当地使用了多重对应分析(MCA)这一方法将定性数据降维成平面上的散点,来直观地体现不同国家新闻场域中力量的主要分布和结构,从而推断资本的分布情况。
在研究的第一部分,作者呈现了“市场压力”和“政治影响”两个指标,它们主要影响了各国记者衡量自己职业受到的约束和要求。作者发现,记者们在“政治影响”的轴线上的分布,基本对应了所在国在世界上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水平的排名(例如在政治自由度较高的国家,记者更可能强调他们在促进政治参与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为了深入了解国家差异以外的场域特点,在第二部分,研究者控制了国家因素,发现记者个人对自身职业的认知决定了他们在政治经济的坐标系中的位置。纳入附加变量后,可以发现在衡量这些指标的时候,不同职业特征或者社会背景的人处于不同的场域,并且这些特质在记者所处的场域中展现出了一定的趋同性(例如具备更高学历、在全国性报纸工作的记者更关注政治与社会相关的新闻)。那么,各国新闻界是否都共享这样的场域结构?在第三部分中,文章进行了更深入的类特定分析(CSA),根据不同新闻文化类型将样本国家分为监控型(monitorial)、倡导型(advocative)、发展型(developmental)、合作型(collaborative)四个类别,发现不同新闻文化之间有显著差异(例如合作型文化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审查制度的影响,监督型文化的国家则反之)。最后,文章对四种类型文化各自进行的场域分析,揭示了各国新闻场域核心的结构性特征依旧存在,且都在围绕着“资历”(seniority)和“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来构建普遍规律,但是在不同文化场域内的强度和形式不同。
案例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了贡献: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再次支持了布尔迪厄场域同构性的基本观点,拓展了其应用范围;其次,回应了一直以来对“缺少非西方场域比较”的批评,借助世界范围的调查数据让差异显著的国家之间的新闻场域也有了比较的空间。但局限性也同样明显:本文的基本假设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感知可以推断周围环境的特质。这虽然赋予比较场域分析一定的可行性,但仍只是一种可信度较高的假设。同时,多重对应分析虽清晰地展现了不同场域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种描述性方法,无法在统计上对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行确认。此外,即便可比性是成立的,数据是否真的勾勒了不同国家场域的基本结构仍有待进一步考察,由于缺少历史背景信息和指标普遍性的检验,得出的场域同构性结论会比实际情况更加同质化。(李若溪)
案例2:威权—民粹主义背景下媒体所有权网络(media ownership networks)的概念化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土壤,而威权—民粹主义则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变形,其将人民中心主义、反精英主义与专制主义结合起来,进而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而媒体与威权-民粹主义之间有何联系?传统观点认为一切民粹主义运动都严重依赖与媒体的共谋,但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体传播渠道何以加深民粹主义话语这一路径上。过往民粹主义的主流研究往往将民粹主义视作可量度的指标。如利用问卷进行数据收集,设置政治意识形态、阴谋心态等变量,将民粹主义态度描绘成量表以分析其影响 ;或是将民粹主义观念划分为三个维度,进而对民粹主义影响下的个人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弗里德曼认为,民粹主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解决媒体集中所有权问题的政策失败的回应。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媒体(权力)集中对国家民主程度有负面影响。所以关注媒体所有权便成为民粹主义研究的新思路,“民主分配原则”意味着公共话语中权力的分散。与之相对,媒体所有权的集中不可避免地导致民主的丧失,较少的多样性可能营造一个受控制的“回音室”。
因此,当下媒体所有权被认为是威权—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因素,高度商业化市场中的媒体集中度有助于提升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知名度,并扩大民粹主义新闻内容的规模与影响。但媒体所有权涉及诸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研究者很难将其作为自变量孤立研究。所以将媒体所有权置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是研究的关键。作者应用了一个模型以分析描述媒体所有权的结构。作者根据民粹主义统治程度与相对历史地理文化两个标准,选取了两个民粹主义持续高度控制的案例(匈牙利、土耳其),以及两个民粹主义政府控制较少、间歇性发挥影响的案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
论文选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法(SNA),通过对奥地利、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四国2000年、2010年、2020年全国受众范围/平均年受众市场份额达到3%的印刷、在线与电视新闻媒体机构进行尽可能标准化的媒体-受众测量,多角度追踪公司的所有权结构直至确定所有者,其数据通过商业登记、经济档案等国家数据库收集。运用标准网络可视化技术,作者计算了结构网络特征中的最常见测量值,包括媒体数量、媒体规模、边缘参与者数量、网络密度、特征向量集中化数值。 如果新闻媒体所有权结构高度集中,并且在给定的媒体环境中边缘化外围所有者,则有利于强化核心参与者的信息强度。
研究发现,直至2020年,四国的特征向量中心化水平都比近几十年高得多。虽然在线媒体的进入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现有结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已经呈现了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从媒体发展情况来看,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媒体连接数量大幅增加,斯洛文尼亚与土耳其的增长则相对有限。所有国家的特征向量集中化数值于2010—2020年都保持上升,而边缘节点数量持续下降,都共同指向了“掩盖反对声音”的现象。但论文对图表的解释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文章结构分析图显示,2010年是四国媒体所有权变化的重要节点,四国的特征向量中心化数值全部在这一年开始迅速上升,意味着“核心-外围”的结构程度愈发加深。但本研究并非结合案例或经验材料对其进行深度的原因阐述。在斯洛文尼亚,核心扩张与外围不平等趋势先下降后上升,可能暗示了核心-外围结构的强劲增长超过了在线资源扩张的结果。 私人媒体与在线资源数量增加,导致媒体渠道整体更多样化,但是在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三国的网络密度却更小,这本身存在矛盾。文章因此得出结论,高度集中的媒体所有权使得经济、政治精英间联系增强,从而提升了“监督”水平,影响了私人媒体资源与政策之间的联系。 作者经过社会网络分析发现,以上四国的媒体所有权结构已经为威权—民粹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事实证明,即便是土耳其、匈牙利这样的极端案例,其媒体所有权也并未完全地被政治集中控制。具体体现为,网络结构的组成部分并未减少,从所有权角度考量,仍有部分媒体独立于政府之外。而这一现象也吻合现代威权主义的特征,即“竞争性威权主义” 。
国家并不彻底废除民主公共领域,从而营造一种民主竞争的假象。允许一些批评声音存在,将其保持在足够声称媒体自由的程度,最终不会脱离政府对媒体景观的控制。
然而,该论文同样存在不足,首先是文章选取案例可比性的问题,奥地利、斯洛文尼亚通常被认为是年轻的民主国家,将其置于民粹主义讨论范畴下缺乏充分的论据,需要再补充经验材料。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观察媒体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进而得出了适宜民粹主义发展的结构,但媒体所有权集中是一种全球趋势,不能仅仅关注呈现结果,更应该侧重于发掘其背后复杂的驱动因素。同时,本文关注的所有权是法律意义上的正式法人关系,而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关系也对民粹主义话语存在重要影响,例如政治关系、家庭关系、情感关系等,也需要进一步的定性研究来揭示媒体所有者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类型及其后果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开发能够在政治利益渗透的多层次和跨媒体信息环境中检查媒体所有权的创新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是推动这一议程的一个有前途的工具。(仲阳)
案例3:政治制度差异下网络新闻角色表现跨平台比较研究
关于数字技术如何影响新闻生产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对冲突的新闻价值观的早期研究上,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数字化转型对新闻编辑室实践的影响,但当下关于媒介差异的跨平台比较研究较为缺乏,关于平台在新闻生产中所扮演角色(以下简称为“新闻角色”)的既有研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结果 :其一为通用主义,认为跨媒体平台的新闻角色表现是趋同的;其二则为特殊主义,认为记者会根据不同平台采取不同的新闻采集、筛选和呈现方式。
目前,尚未有学者分析网络环境中的新闻角色表现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跨平台差异是否因新闻编辑室文化而有所不同。本研究提出研究问题:(1)与各国其他平台相比,新闻角色(journalistic roles)在网络上的表现如何?(2)不同国家的平台与新闻角色的表现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趋同? 本研究针对2020年37个自由、部分自由和非民主国家的102家报纸、96个电视新闻节目、74个广播新闻节目和93个新闻网站的148474条新闻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
研究参照Mellado 对新闻角色的操作化方式,根据新闻业和权力的关系、新闻声音在故事中的存在以及记者向受众报道的方式三个维度,将新闻角色分为六类:监督角色(看门狗)、忠诚促进者、干预主义角色、服务角色、信息娱乐角色和公民角色。同时,本文将新闻编辑室融合作为关键变量,分为完全融合、跨媒体和孤立平台三个层次进行内容分析。
研究发现,部分新闻角色在网络媒体中的表现相较于传统媒体存在差异,与网络平台相比,干预主义角色、服务角色、信息娱乐角色和公民角色更受电视、广播、报纸平台的影响。平台与新闻角色表现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这种关系受到国家层面的影响。具体而言,第一,网络新闻的服务角色与信息娱乐角色相较于其他平台更突出,而监督角色和公民角色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s)得分与其他平台趋于一致,干预主义角色和忠诚角色的因子得分排名较低,表明网络媒体并不更倾向于表现记者观点或政治激进主义。第二,干预主义角色、信息娱乐角色和公民角色在电视新闻中比在网络新闻中明显,广播提供的信息娱乐功能和报纸提供的服务功能相较于网络新闻更少,而报纸与电视的监督角色和忠诚角色并不存在跨国间的显著差异。第三,自由国家的记者相较于部分自由和非民主国家而言更多地呈现干预角色,忠诚角色只在政治不自由的国家存在,网络新闻行使忠诚角色差异显著,公民角色的表现主要在广播和电视新闻中更高,多数国家的在线新闻相较于广播更多地呈现出服务角色。其他角色并不存在跨国和跨平台的显著差异。
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为分析标准化实践如何塑造(或不塑造)新闻中的不同角色表现提供了参考,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以各平台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分的排序作为衡量新闻角色表现差异的依据,存在过于重视排名而忽视因子得分的情况,例如,研究认为网络媒体的监督角色表现显著低于报纸和电视,但就数值而言,各平台监督角色的因子得分十分相近。此外,研究结论以政治制度作为依据、对描述性研究结果进行解释,一方面忽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因缺乏影响机制研究,难以进行更详细的对比分析和对跨国差异的解释,在研究结论部分存在过度阐释的情况。(李怡峰)
案例4: 美国和德国媒体对科技巨头的监督角色比较
A. Schwinges等学者撰写的《大科技时代的监督者角色——美国和德国的新闻媒体如何让大科技公司承担责任》一文,研究了大型科技公司(如Meta、微软、亚马逊、苹果和Alphabet)在美国和德国主流媒体中的监督角色,探讨了两国媒体对科技巨头的报道差异。
大型科技公司,如亚马逊、苹果、Meta等的服务和产品构成了当下数字社会基础设施的核心,但它们快速的扩张和发展也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各种威胁和挑战,如权力垄断和制度规范漏洞。灰色不法之地的存在让公众越来越意识到政府、科技行业和社会监管规范的重要性。而媒体作为“看门狗”,如何对大型科技公司发挥批判性监管作用,这一议题值得人们深思。
具体来说,作者选取了美国和德国四家主流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今日美国》(USA TODAY),德国的《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和《世界报》(Die Welt)(2000—2021年),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对920篇报道大型科技公司的印刷新闻进行了纵向定量内容分析。“Big tech”(大型科技公司)是指科技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公司Meta、微软、亚马逊、苹果和Alphabet(Google)。作者选择这五家公司,是因为它们的规模和资金相当,可以控制数字监管的话语。
文章从跨时间、跨国家和跨政治倾向的角度比较了两国媒体监督者角色的异同。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虽然科技巨头在两国新闻报道中的相对可见度很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比例都略有上升。媒体监督者的角色也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凸显。这一时间模式表明,媒体报道往往会受到孤立事件和新闻价值的驱动,而非持续稳定地对科技巨头进行监管报道。
其次,作者比较美国和德国的媒体报道发现,相比德国媒体对科技巨头的关注程度,大型科技公司在美国获得了更多关注。这说明它们对美国国家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并且美国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公司的消息来源。更进一步可以得出,媒体报道并非由监督者的角色主动驱动,而是受新闻因素的影响。
根据监督的强度、监督的声音和事件的来源,过往研究者将媒体监督者的角色分为脱离型和干预型。脱离型角色是指记者以一种相对被动的立场对权力机构进行监督 。这种监督更多是通过反映现实情况、引用消息来源来批评公司或政府,而不是直接进行深入调查或积极干预。干预型媒体监督则是指媒体在履行其监督职能时,不仅报道事实和提出批评,还通过深入调查、积极追问和持续关注,对监督对象产生直接影响,以推动问题解决或制度改革。在跨国比较中,美国媒体以脱离型监督者为主,而德国新闻机构扮演着干预性更强的监督者角色。作为对抗性更强的监督新闻的代表 ,德国记者越来越积极地要求问责。而这也与德国的社会背景相符,作为欧洲科技监管的先行者之一,德国媒体的报道实践与政府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议程相一致。
最后,从政治倾向上看,大型科技公司在中右倾新闻媒体中的可见度明显更高。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在美国和右倾新闻机构中,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报道更加引人注目。
总而言之,这一研究首次展示了媒体的监督作用如何体现在不同的新闻动态实践中。对新闻媒体有关科技巨头报道的比较分析表明,媒体“看门狗”的角色是通过一系列受环境影响的动态实践来实现的。在制定问责议程的道路上,媒体主要扮演的是一种脱离的监督者角色,将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批判性审查留给消息来源。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消息来源的增加可以表明媒体对大科技公司的监督功能日益完善。此外,这种监督者的角色越来越多地通过一种更具干预性的取向来实现,也就是说,记者们更多地自己发出声音,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批判性监督。 更进一步,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对印刷新闻的研究结果与对其他类型媒体新闻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此外,除了作者已经选取的企业、政治和监管机构的消息来源,也可以将其他非精英来源(如公众或利益集团)纳入评价标准,来探究记者与其的互动,以及记者如何用它们来削弱舆论力量。(仲昱洁)
案例5: (去)合法化真相主张的差异实践
在当下的数字媒体生态中,事实和真相主张越来越受到另类阐述的影响。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如何合法化自身的真相主张、如何去合法化他者的真相主张,另类媒体的真相主张建构是否为虚假信息提供温床、破坏主流秩序,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思考。在《进入真相并行的信息时代?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合法化与去合法化真相主张的定性分析》一文中,学者迈克尔·哈梅尔斯(Michael Hameleers)和尼卢·耶克塔(Nilou Yekta)研究了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在报道COVID-19新闻时如何建构真相主张。
本文作者将真相主张视为媒体平台在传播行为中可以强调的话语建构,其目的是向受众发出值得信赖的信号。合法化和去合法化真相主张的方式有很多,本文主要研究专家知识和(经验)证据两种。本文研究问题如下:(1)在另类媒体平台上和主流媒体平台上,如何利用专家知识来证实真相主张?(2)另类媒体平台和主流媒体平台怎样利用(经验)证据证实真相主张?(3)在另类媒体平台上和主流媒体平台上,专家知识如何被用来否定真相主张?(4)另类媒体平台和主流媒体平台怎样利用(经验)证据否定真相主张?
本文作者认为,美国的极化程度更高、民众对媒体和政治的信任度较低,荷兰则极化程度更低、民众对媒体和政治的信任度较高。借用学者埃达·汉普雷希特(Edda Humprecht)的虚假信息抵御能力框架,美、荷两国在抵御虚假信息威胁方面代表不同的体系,这也许会为(去)合法化真相主张提供不同的话语机会结构。
本文抽取两国中两个相对流行的主流媒体、两个另类媒体作为样本——主要选择右翼媒体,分别与一家左翼媒体进行比较,且另外分析了荷兰的一家左翼另类媒体。初始样本为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2月1日之间、每个媒体的各25篇“最受欢迎”的COVID-19相关文章,经作者验证后确认达到理论饱和,并最终从中选出35篇文章进行编码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作者采用扎根理论,进行三级编码和定性分析。
研究发现,无论在另类媒体还是主流媒体中,专家知识对于合法化和去合法化真相主张都发挥着核心作用,但两类媒体的使用方式却有很大差别。所有的主流媒体在合法化真相主张时,都会引用详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专家知识和证据。左翼和右翼另类媒体的言论则存在显著差异:左翼媒体偶尔如主流媒体一般,但右翼媒体无一例外地仅仅引用部分证据,并且笼统地宣称“具有普遍的”专家知识。去合法化叙事的风格和语言有很大差异。在另类媒体中,专家来源被指责故意传播虚假或欺骗性信息;在主流媒体中,专家知识和(经验)证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有时会受到质疑,但批评并不注重个人攻击。而且,主流媒体的去合法化真相主张大多以单独的事实核查或揭露主张的形式出现,但左翼之外的另类媒体去合法化真相主张则通过“明确指责主流(媒体和政治精英)歪曲事实、蓄意制造虚假现实”来实现。另外,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所有的另类媒体都对主流如何处理病毒表达了明确的反体制观点,发表了民粹主义的去合法化论调。此类论调“寄生”在主流论调之上,是对主流媒体文章中专家知识和(经验)证据的“改造”,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从根本上与主流真相主张不同的另类民粹主义认识论。本文作者亦探讨了最极端的另类媒体——荷兰的右翼另类媒体Niburu, 它的去合法化叙事明显沿袭了民粹主义阴谋家的风格:指责主流媒体捏造证据,向人民掩盖真相。这类极端另类媒体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制造了大量的虚假信息、假新闻、恐慌情绪。
相比于以往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另类媒体的(去)合法化做法的灵活性——它们可以依靠另类的反知识工具,也可以借助于主流的建构真相主张的工具。本文支持了过往研究中有关另类媒体“以反对主流秩序和主流媒体为特征”“建构反知识”“支持民粹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同时提出了新的观点:另类媒体并没有系统性地偏离表明新闻质量的惯例和常规,它们也引用专家知识和(经验)证据进行真相主张。本文作者提出了三个核心维度:另类媒体与主流现实的距离或对传统现实的支持,另类媒体对主流在人民中误导、欺骗或投下阴谋的意图的严重性的解释,另类媒体为了合法化另类真实主张而使用的修辞工具。通过三个维度,可以定位不同的另类媒体与反事实叙事。这种概念化或许有助于未来探索跨语境、跨平台和跨问题的真实性、相对性和灵活性。
这一研究的发现和结论也存在不足。例如,本研究只关注COVID-19背景下的真相主张,发现的(去)合法化叙事是否能够推论到更多极化问题上,仍有待商榷。其次,本文重点在于描述真相主张如何在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上被合法化和去合法化,没有判断各平台的实际虚假信息程度,没有将这些(去)合法化叙事和平台实际虚假信息程度联系起来。此外,本文依然沿袭过往研究,另类媒体样本选择仍旧集中在右翼,实际上左翼另类媒体可能也使用去合法化叙事和反建制视角,且本文没有进一步探讨左翼另类媒体和主流媒体的叙事为何具有相似性。(高雨琪)
案例6: 媒体碎片化和极化如何对用户认知“另类媒体”产生影响
近年来,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已成为部分新闻用户的重要信息来源 。基于当前另类媒体与主流媒体相互融合的趋势,以二分法(dichotomy)的方式将“另类媒体”视为“主流媒体”对立面的定义过于简单化;媒体使用者对“媒体”拥有与媒体机构不同看法的这一事实,使得定义另类媒体更加复杂 。
Desiree Steppat, Laia Castro以及Frank Esser在《新闻用户对不同国家“另类媒体”的感知存在差异:媒体碎片化和极化如何影响用户感知》一文中,通过构建另类媒体的分类谱系,对处于不同媒介体系的五个国家的新闻用户认知另类媒体的差异情况及影响因素等问题展开了具体分析。
具体而言,该研究意在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不同媒体环境中的用户认为哪些媒体属于另类媒体的问题,二是媒体碎片化和极化是否模糊了用户对主流媒体与另类媒体感知的问题。研究者采用网络在线调查问卷收集数据,根据4种媒介体制选择丹麦、意大利、波兰、美国和瑞士5个国家,依据各国18至79岁人口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的统计数据进行配额抽样(quota sampling),共抽取12676名受访者,询问其是否认为自己属于另类媒体的使用者,并要求自认为是另类媒体用户的参与者提供至多3个另类媒体的名称。根据收集到的媒体类型,作者构建了从“主流媒体”到“另类媒体”的媒体使用类型分类谱系,即将用户对另类媒体的感知作为因变量。自变量测量方面,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媒体碎片化和极化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另类新闻的使用频率或程度 ,因此作者对媒体碎片化指数(由新闻媒体市场规模、非共享新闻用户比例、非公共广播服务受众比例组成)和媒体极化指数(由政治平行性和受众极化组成)进行测量,并计算出5个变量的平均得分,用更高的分数表示更高的媒体碎片化和极化水平。
研究结果显示,新闻用户对另类媒体的定义覆盖了主流媒体、自称另类新闻的媒体、社交媒体等8种类型,他们对“另类媒体”的感知差异受到媒体环境特征的影响。相较于丹麦和瑞士,在意大利、波兰和美国3个媒体碎片化和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公众更倾向于视自己为另类媒体使用者,频繁使用另类媒体获取政治信息。虽然用户提及的另类媒体来源呈现多样化,但处于更加碎片化和极化环境中的用户更偏好将主流媒体机构识别为另类新闻媒体,该现象在美国尤为明显。这表明在政治信息环境中,媒体的碎片化和极化让用户感知另类与主流媒体在类型谱系中趋同融合的程度更高。
研究丰富了“另类媒体”研究的受众比较视角,对媒体环境的结构特征,如碎片化和极化,以及对于理解公众如何感知和接触另类媒体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首先,作者没有说明选择两个民主法团主义媒介体制国家,而其他三种媒介体制各选择一国的原因。其次,该研究也具有当前大样本研究的通病,即结论停留在描述性分析层面,针对美国民众更偏好将主流媒体机构识别为另类媒体这一现象,即便给出了“媒体碎片化和极化程度较高的环境有利于另类媒体的发展,因此一些传统媒体采纳了另类媒体的特征”的猜测,对人口特征的关注仍尚浅,且总体上仍缺乏对深层原因更加规范的探讨。另外,在时间维度的比较上,研究选择了静态时间点进行调查,无法展现用户对另类媒体认知的动态变化。未来,研究者可以深入探究个人层面的因素对另类媒体使用的影响。(王忆)
案例7:对民主的信任和态度在虚假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对六个民主国家的比较分析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虚假信息的传播势头增强,党派媒体通过反精英叙事和阴谋论等替代性理论来解释大流行的原因 。操纵发布虚假信息的团体策略性地应用数字媒体环境故意欺骗民众。信任是虚假信息危机的核心,公民对发布可靠信息的新闻机构的信任可以成为抵御虚假信息的盾牌。为了进一步了解为什么虚假信息传播得如此之快,Edda Humprecht的文章《对民主的信任和态度在虚假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对六个民主国家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对新闻媒体、政治行动者和机构的信任以及对民主的态度如何影响公民与虚假信息互动的意愿。鉴于社交平台上虚假信息的普遍存在 ,公民在社交平台上充当虚假信息传播的推动者 ,研究从跨国角度考察了公民对虚假文章点赞、分享或评论的意图。
研究使用Respondi调查公司2020年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以同样方法收集的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n=7006),调查了人们对虚假信息(喜欢、分享或评论)的反应和传播意愿、对民主的态度以及对新闻媒体和政治行为者的信任。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作者以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对政治的信任和对民主的态度作为自变量,以在社交媒体上进一步传播虚假信息的意愿(如点赞、分享或评论)作为因变量,提出了三组关系假设。在数据定量分析部分,作者以方差分析(ANOVA)揭示了主要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国家差异,并对每个国家进行了具有聚类稳健性标准误差(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的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分析因变量喜欢、分享或评论虚假信息的意愿和自变量信任与民主态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对于虚假信息传播起从属作用,但对社交媒体新闻的信任与传播虚假信息的意愿有很强的关系。2020年,对政府高度信任的美国和英国公民更愿意传播虚假信息,而在法国和比利时,信任反对党领导人的公民更有可能这样做。此外,对民主感到满意的公民似乎不太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但美国民众除外。 研究有两个重要的发现。第一,除比利时外,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与虚假信息的传播无关。这一发现与先前的研究结论不同,可能是因为受到以下因素影响:首先,单维定量技术的使用可能导致对媒体信任的理解并不完整。媒体信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必须在不同的层面进行研究 。研究在衡量媒体信任时区分了对一般新闻媒体的信任、个人自己使用的新闻媒体和对记者的信任,但并不理解“受访者所说的媒体信任是什么意思,也不清楚媒体信任在他们对社交媒体信息的评估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
这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定性研究,以获得更深入的见解。其次,研究数据可能受到大流行的影响。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是在2020年4月和5月收集的,当时研究包括的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了封锁,与大流行相关的虚假信息正在广泛传播 。Serrano-Puche等人在2021年10月进行的定性研究显示,大流行期间的信息超载、媒体政治倾向的两极分化以及吸引受众的新闻诱饵泛滥等问题让受众在搜索新闻时转向各种来源来平衡新闻项目。根据对10个欧洲国家的调查,Hameleers等人得出结论,对虚假信息有更强感知的用户更有可能在社交网络和另类非传统媒体上消费新闻 。这可能导致对媒体的信任并不足以让人们抵抗虚假信息,对社交媒体新闻的信任对分享、点赞或评论虚假信息的意愿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传播虚假信息时,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所起的作用不如对政治行动者的信任和对民主的态度重要。这一发现与先前的研究保持一致,但跨国的比较视野揭示了不同政治形势下公众对政治家和机构的信任,以及民主态度与分享虚假信息意愿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英国和美国,对约翰逊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均为保守派)有高度信任的公民更愿意传播虚假信息,而在法国和比利时,对反对党政治家有高度信任的公民更有可能这样做。信任某些政治行为者的个人似乎更倾向于传播他们认为符合这些政治行为者观点和价值观的虚假信息,分享虚假信息可以被视为一种由党派偏见驱动的政治参与形式 。对民主的低满意度与传播虚假信息意愿的关联也可以在这种背景下解释。拒绝民主价值观会导致对传统信息来源缺乏信任——这一空白可能会被更容易受到虚假信息影响的其他信息来源所填补。这可能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破坏民主和公众做出知情决定的能力。
一些因素可能影响了这项研究的结果。首先,信息环境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独特的机会结构 ,研究结果不太可能适用于其他国家。其次,本研究关注对媒体、社交媒体和政客的信任与传播虚假信息的意愿之间的关系。但是,本研究却忽略了在此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其他因素,如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内容的普遍意愿。最后,研究者在测试传播虚假信息意愿的过程中向参与者展示了关于COVID-19、移民和气候变化等两极分化话题的虚假文章,这些文章可以引发受访者的强烈情绪。但是,由于情绪和认知反应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尚昕怡)
案例8: 国际比较视野下用户对新闻推荐系统透明度和控制权的渴望研究
社交平台使用的迅速增长使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接触个性化的信息空间。其中,新闻推荐系统(以下简称NRS)在赋予用户广泛信息来源的同时,也阻碍了多样化观念的形成与传播,特别是影响着网络治理结构和群体价值认知。因此,算法的透明度和用户控制作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设计理念被广泛讨论。
Mitova和Blassnig等人撰写的《探索新闻推荐系统中用户对透明度和控制的渴望:一项五国研究》,通过研究个人特征与对NRS透明度和用户控制权的渴望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荷兰、瑞士、美国、英国和波兰五国的差异,考察了算法层面的顶层设计与用户层面的人权自由。
在评价用户对NRS的具体态度和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程度,以及国家层面民主模式、监管环境、文化价值观、人工智能技术接触机会、高知名度算法事件的比较差异后,作者提出了三个开放的研究问题:媒体信任与对NRS透明度和用户控制权的渴望有什么关系?各国对NRS透明度和用户控制权的渴望有何不同?个人层面的特征与国家NRS透明度和控制权渴望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何不同?在数据分析部分,基于横断面调查,作者通过一家国际市场研究公司在荷兰、瑞士、波兰、英国和美国招募了5079名受访者,他们被要求做有关NRS的自我判断报告以及评估每个国家的最多9家新闻机构。 研究结果显示,所有五个国家的用户普遍需要更高透明度,甚至需要更高控制权,其中荷兰用户对二者的渴望程度均为最高,英国用户对透明度的渴望最低,瑞士用户对控制权的渴望最低。 具体而言,该研究在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有两类重要发现:个人层面上,用户对在线收集数据更为关注,对NRS有更多隐私顾虑以及对算法有更多了解的用户渴望拥有更高的透明度和控制权,但特别依赖个性化服务的年轻人对新闻网站的透明度和控制权的渴望较低 。
此外,一般的媒体信任与这种渴望并无明显关联,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环境,如算法系统应用的具体领域。无论在哪个平台上,新闻消费频率较高的用户都更关注与NRS有关的信息,并渴望有机会影响算法新闻的提供与服务。国家层面上,研究者推测由于荷兰发生过算法丑闻的大规模公共辩论事件,其公民会以更加批判的态度考量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设计理念,因此荷兰在透明度和控制权方面的渴望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且媒体信任仅在荷兰有助于提高NRS透明度。瑞士作为样本中唯一的直接民主国家,经常化的民主参与渠道可能会降低用户对控制权的渴望,所以在控制权渴望方面,瑞士要低于其他四个民主国家。波兰对NRS透明度和控制权的渴望程度与坚持自由传统的英国和美国相似,表明波兰的媒体系统与美国和英国的具有共同特征,进而产生了相似的媒体消费文化。但总体而言,不同国家用户在透明度和控制权渴望方面的差异较小,某种层面上说明,这些NRS的规范性特征得到了民主国家公民平等和普遍的评价。
研究不仅关注了个体的新闻消费观念以及对NRS的积极性评价与负面影响的顾虑,还将整体环境因素作为影响纳入个体层面的考虑。这些研究发现可以被应用于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理念设计,满足用户、新闻机构的需求和更广泛的社会期待。未来可以增加对用户行为互动以及非西方民主国家的研究。(杨琪媛)
案例9: 作者性别和情感规范如何影响读者对性别平等报道的评价
内容创作者的性别对受众的影响研究共同发现,性别是一种线索,是影响文章评价的认知捷径 。但是,尽管性别被视作与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期望和刻板印象密切相关,实证研究结果既支持也反对文章评价中的性别署名偏差。既有研究证实读者对男性作者的评价比对女性作者的更积极,也有研究发现在政治、个人网页和产品评论中,性别署名对女性作者的评价没有负面影响 。因此更重要的研究关切是,在什么情况下对女性作者的网络偏见依然存在。
在此基础上,学者Leyla Dogruel、 Sven Joeckel和Claudia Wilhelm发表了《署名偏见是一个过时议题吗?作者性别和情感规范对于评估性别平等报道的影响》一文,首先研究了性别平等的特定议题中,性别在多大程度上容易产生署名偏见效应,还进一步探究了社会对性别情感表达的期望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这种性别署名偏差的强度和方向。
研究采用了两项连续实验研究的结果,这两项研究分别操纵了性别署名和情绪规范描述,并将读者性别作为一个准实验因素。研究1于2018年春季在德国选取了493名参与者进行纸笔调查,通过对新闻文章的作者性别和情绪规范进行操纵,来探究这些因素对读者对新闻文章的阅读意向的影响。作者使用了2(作者性别:男/女)×2(情绪规范:有/无)的双因素设计,并将读者的性别作为一个额外的准实验因素。研究采用了75字左右的文章预览作为刺激材料,要求参与者评估他们继续阅读完整文章的可能性。但是,研究1的结果既没有发现性别署名的显著主效应(RQ1),也没有观察到读者性别、作者性别和情感准则规定对继续阅读兴趣的交互影响(RQ2)。
考虑到1的结果和局限性,研究2在研究1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增加了一些控制措施:(1)为了解释情绪规范对男性、女性的区别影响,增加了女性愤怒的场景;(2)增加归因可信度作为变量;(3)在署名中加入一男一女的照片,让性别差异更明显;(4)测试当男性、女性分别违反性别情感规范,即男性感到羞耻和女性表达愤怒时,会对读者产生什么影响。研究2通过在线平台招募了1216名参与者。结果显示,性别署名偏差是一种微弱但显著的影响,即参与者更倾向于继续阅读男性作者的文章,同时,女性作者的可信度略高。而情感规范产生的影响,可能会因对象(男性与女性)和情感类型(羞愧与愤怒)的不同而不同。
最终,研究发现,首先,性别署名偏见依然存在,但取决于内容和背景特征。研究在性别平等领域显示出了性别署名偏见,并且发现了图片刺激对偏见的影响。即使女性作者批评男性性骚扰,单单是女性署名也不会引发对女性作者的偏见;然而,当此类文章配有肖像图片时,负面偏见就更有可能出现。其次,研究认识到可信度与性别之间的矛盾关系。男性通常被认为比女性更可信,这是由于对男性在能力和专业知识方面的性别刻板印象。然而当涉及有利于女性专业知识的话题时,如性别平等,女性则被认为更可信。最后,研究指出,在文章中规定情感规范会影响读者对文章的可信度和阅读意向。不同的情感规范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与所涉及的具体情感有关。研究推测,“允许”女性表达愤怒的情感规范远比男性承认羞耻更容易被接受。此外,研究还发现女性读者比男性读者更认可女性违反情感规范的行为,表明读者的性别可能影响其对情感规范的态度。
总的来说,研究揭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发现:当女性撰写有关性别平等的文章以提高所有性别的能见度,并为包容、团结和社会变革提供一个平台时,她们仍可能被视为此类主题的可信作者。但就阅读意向而言,这可能仍不足以消除对她们的偏见,修正对男女记者的署名偏见任重道远。 另外,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未能控制读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所呈现的情绪规范。其次,由于参与者在同一问卷中接触到了两个不同的刺激物,“Shame: Men”和“Anger: Women”,可能存在溢出效应或学习效应,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此外,研究的样本可能存在特定特征,如年龄、教育水平等,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推广。(顾靓楠)
案例10: 记者应对网络暴力时面临的结构性障碍
数字技术的发展要求新闻媒体更多地通过线上渠道与受众接触,导致记者被迫面临日益严重的网络暴力,不同身份的新闻记者所面临的暴力是不成比例的 。新闻编辑室中的性别机制加剧了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结构性不利地位 。
《“我多希望它们成为我的后盾,但它们没有”——解决针对记者的性别化网络暴力的结构性障碍》一文运用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说明记者所在工作组织的内部障碍导致她们无法通过组织应对来源于外部的网络暴力,整体的新闻自由环境影响了记者对这些障碍的感知。
具体而言,作者提出两个研究问题:记者所处的内部工作环境如何成为解决性别化网络暴力的阻碍?在不同的新闻自由情境中,媒体组织内部如何感知这些障碍?为解决上述问题,作者通过两轮访谈和多次参与式观察进行数据收集,先后与12位国际新闻组织代表和15位来自英国或印度的记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研究采用主题分析的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编码,最终确定了记者的工作环境中存在的限制解决性别化网络暴力的三个因素,以及新闻自由条件对这一情况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媒体组织之所以无法充分支持遭受性别化网络暴力的记者,是因为不平等制度下存在结构性障碍,包括支持资源分配不平等、媒体内部的“强硬文化”和记者工作的不稳定性,而来自英国和印度的案例的主要区别在于记者对暴力威胁的强度感知不同。首先,为记者提供支持意味着媒体组织需要消耗密集的资源,承担经济压力。等级制度下底层记者更难获得支持资源,且下级记者还会面临组织内部上级的额外压力。其次,行业内存在的“强硬文化”(tough-it-out)实质将处于特权地位的性别规范强加于整个记者群体。作者在此处特别强调了复合弱者身份产生的影响,例如,英国的受访者强调少数族裔的种族身份导致的更为恶劣的情况,而印度受访者则强调宗教背景下低种姓女记者处于更低的地位。最后,记者的高工作压力、高灵活度和工作的高度个体化共同导致了行业内部的不稳定性,限制了记者向新闻编辑室提出支持请求的能力。与现有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作者进一步提出,在不利的新闻自由环境中,暴力本身构成了记者的不稳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过比较发现,不利的线下新闻自由环境削弱了记者对于线上威胁的感知。相较于英国,虽然印度的新闻自由环境更为不利,新闻媒体面临更大的制度压力,印度记者在现实和网络中面临的威胁更为严重,但是她们对于线上暴力带来威胁的感知更弱,这可能会导致印度记者暴露于更加不利的网络环境中。
这一研究关注到交叉身份下边缘群体的脆弱性,将新闻记者身份与性别、种族、宗教等其他身份结合开展研究,并发展了Acker提出的不平等机制(inequality regimes)的概念,将外部的网络暴力与新闻编辑室内部的控制与遵从机制视为同类的结构性压力。该文深入解释了现有研究提出的媒体组织不能为遭受网络暴力的记者提供充分支持的原因,丰富了对制度结构和媒体暴力的跨国比较研究。
遗憾的是,该研究在比较案例的选取合理性和对比深度方面存在一定缺陷。文章仅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数据,确定了英国和印度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异同,而没有探索不同身份背景的受访者对所在国新闻自由的感知,以进一步分析这如何影响她们对结构性障碍的感知。同时,作者没有详细论述英国和印度记者在不同的新闻自由环境下产生的不同的感知为何最终指向了相同的结构性障碍。研究者未来可以选择更为合理的比较框架,以去中心化的分析视角进一步探索不同新闻自由环境下记者面临的结构化障碍的异同点。(刘文清)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传播场域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1YJC860002)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参考
单波,曹皓,李若溪,等.比较新闻学年度案例评析(2022—2023)[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4,(02):212-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