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十一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从生活传承维度进入乡村文化活动:一种方法论反思》,作者李红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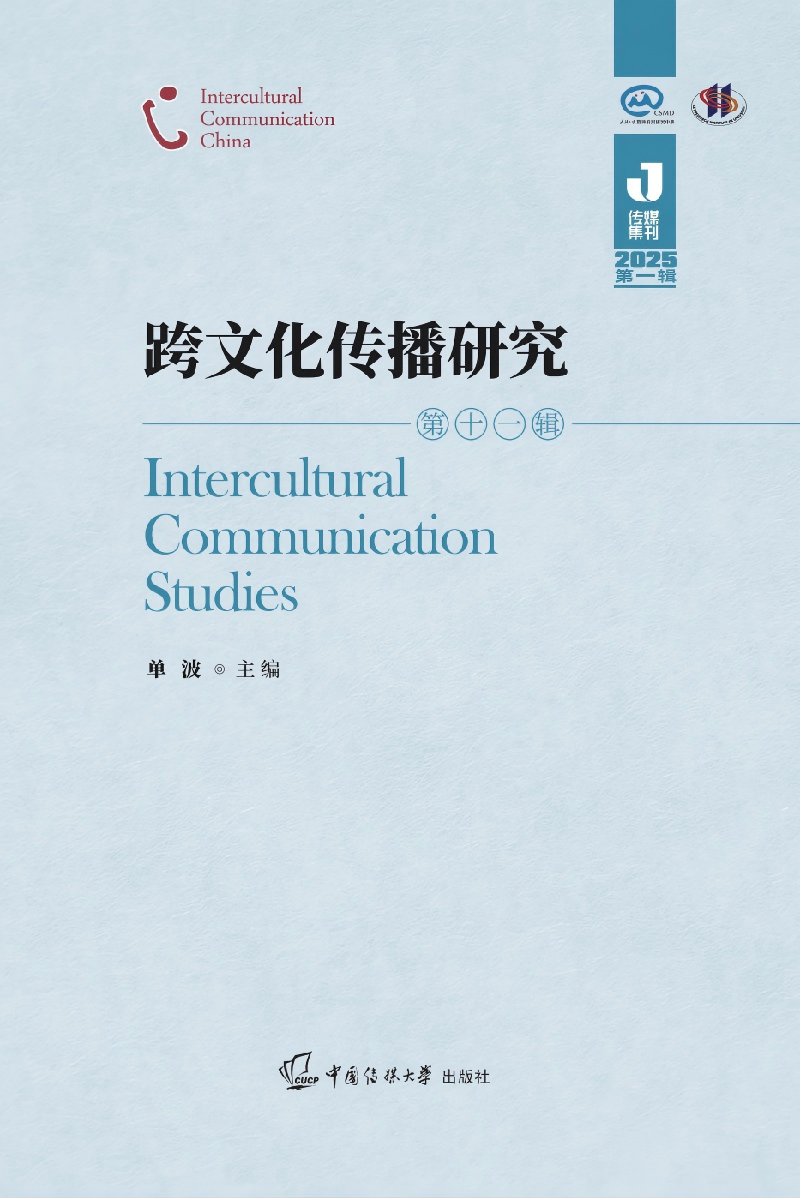
从生活传承维度进入乡村文化活动:
一种方法论反思
李红艳
摘要:在生活传承这一维度上,日常生活的内容成为一个观察文化活动的立足点。从生活传承维度进入乡村文化活动,就要以见微知著的方式经历从身体在场到“浸入”日常的过程,“浸入”日常意味着身处此时此刻的日常文化活动中,那么在经验研究中,此时此刻的文化活动与彼时彼刻的文化活动之间的联系体现在何种维度上呢?在这些维度上,如何理解文化活动形式与个体身体之间的关系呢?本文基于对一个村落日常生活文化活动中身体经验的观察,以睡觉、吃饭、婚丧嫁娶以及唱歌等日常活动为观察对象,探索一种在田野中获得文化资料的“试验”路径,并对这种路径面临的潜在挑战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讨论。
关键词:日常生活;文化形式;观察者;观察时间;个案研究
一、提出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化讨论,对中国基层社会的实证研究和理解还比较缺乏。想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就需要理解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即普通民众,“通过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反思和比较,才能相对客观、真实地看待中国社会的传统和传统文化,也才能对传统和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给予客观和全面的评价”。同时,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往往仅重视文化的“文献传承”而忽视其“生活传承”,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生活传承都远比文献传承更具基础性与决定性的作用,在生活传承这一维度上,日常生活的内容成为一个观察文化活动的立足点。因为日常生活领域是一个连续而动态的过程,“日常生活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之中”,“每个人无论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的地位如何,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对于每个拥有日常生活的村民而言,“浸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或许才是理解地方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钥匙。
马塞尔·莫斯在《身体技术》中指出:“‘身体技术’这个词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式。”“每个社会有着自己的身体习惯。”与不同身体技术相关联的是文化和道德评价:“我们身体的一切都是受到控制的。我正在给你们做报告;你们见证了我的坐姿与我的声音,而你们则坐着并不安静地听我说话。我们有一整套允许或禁止的、自然或不自然的姿势。因此,我们给凝视这个事实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在军队里,这是礼貌的象征,而在日常生活中则是无礼的象征。”借助身体技术的概念,研究者延展出身体经验的概念。身体经验是指“在一定社会生活中个人和集体的身体实践经验。学者们只有通过对这些身体经验的体会才能全面了解一个社会中人的生活”。即身体经验是日常生活中与他者共在的一个方式,“身体经验”的体验与观察,是观察日常生活文化活动的一个有典型意义的视角。
基于此,从日常生活实践这一维度出发,通过对日常生活中身体经验的观察,对乡村文化活动进行调研,从理论意义上看来是一种可行的方式。那么,如何从这一维度出发,在实践层次上进入乡村文化活动的观察现场呢?本文通过一个村落的文化观察试验进行探讨,并展开方法论思考。
二、走入乡村的田野试验
对一个“陌生”村落的日常生活进行调研,有很多路径。基于本地人这一身份进入乡村社会,是第一种路径;选择有研究基础(包括学术基础和资料基础)的村落进入乡村社会,是第二种路径;以“熟人”为中介进入乡村社会,是第三种路径;基于完成行政任务而自上而下进入乡村进行调研,是第四种路径。进入乡村调研路径的不同,会对田野调查初期、中期乃至后期带来不同的盲区。在面对这些盲区时,细致地“浸入”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是“填补”这些盲区的路径之一。那么,如何“浸入”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呢?本文以2019年至今调研的村落为例,从方法论视角进行考察与讨论。
本文调研的村落H,处在山西省左权县。选择这个村落的缘由要追溯到2012年,彼时基于左权本地一位作家的介绍,同事A老师带着学生在A村进行摄影课堂的教学实践,教学实践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年。2019年,笔者需要选择一个村落作为本科生在京外的实习基地,同时确定一个对乡村文化进行长期调研的村落。在A老师的推荐下,我们围绕A村周边的村落进行考察,以便选择一个符合上述要求的村落。
2019年7月初,在与该村落没有任何事先联系的情况下,笔者及团队从县城直接进入了H村。这是一种乡村“冒险”,也是一种调查试验。试验的目的是:希望观察在没有“事先联系”的情形下,进入一个村落调研会“遭遇”怎样的状况。经过2019年到2024年的调研,我们发现,调研团队与H村形成了“十分熟悉”的社会关系。基于此,从方法论上来回顾这种考察文化活动的过程,具有个案探讨的意义,希望由此为乡村文化调查提供一种路径。
三、“浸入”日常生活:身体的在场经验
格尔茨认为,日常“是一个文化体系,尽管通常不是一个整合得非常紧密的体系,但是它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与其他同类体系的基础无异;被它所掌握的人,坚信它自有其价值与真确性。在这里就像是在其他领域一样,一切事物皆系人所自造”。进入乡村的日常就像是进入一个文化体系。那么,对研究者而言,进入一个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差异较大的社会圈子时,首先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浸入”当地人的生活中。当地人的生活是历史惯习与社会演变的结果,研究者可以看到的正好是“当下的这种结果”,而不是历史惯习和社会演变的动态过程。因此,研究者以静态的视角进入乡村社会的一瞬间,所看到的现象不但是表象,而且是表象的碎片。从这些碎片中,研究者进入了另一种动态的、系统的社会生活。其次,尽管是碎片化的表象,它却是富有“灵韵的”。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从时空角度这样描述“灵韵”:
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一边休憩着一边凝视着地平线上的一座连绵不断的山脉或一根在休憩者身上投下绿荫的树枝,那就是这座山脉或这根树枝的光韵在散发,借助这种描述就能使人容易理解光韵当代衰竭的特殊社会条件。
在田野中,这些带有“灵韵”的碎片化表象扑面而来,携带着对身体的呼唤与要求,研究者就“带着身体”进入了田野。
(一)“日常议程”:睡午觉这回事
如前所述,进入一种与研究者迥异的社会系统中,首要的因素是如何进入其日常生活,对流动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也包含对空间性、社会性、情感性的多重意义空间的关注。因此在村落中,不仅需要“浸入”其日常生活中,还需要在日常生活议程中获得体验,即体验日常,这种体验往往与身体在场关系密切。
对于H村而言,进入日常生活的体验的第一印象源自最初抵达时的“一件小事”。2019年7月4日上午8点半抵达H村,我从A同事处得到了该镇副镇长Y的联系电话,Y联系了H村的村书记,并告知我该村刚刚换届。拿到电话号码,我马上给村书记打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了速度较快、夹杂着方言的男声普通话,有些表述由于语速过快,我并没有听清楚。大概意思是说他在镇里开会,开完会就过来找我,需要20分钟。
于是,我坐在大巴停靠地旁边的餐馆里等候书记的到来。20分钟后,H村的书记W准时来了。他面色黝黑,穿着朴素,脚下是一双十分干净的旅游鞋,身着蓝色T恤衫和黑色裤子,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一进来就坐在桌边和我聊了起来,完全没有客套的表述与行为,仿佛昨天我们刚刚见过面。他说他刚在镇里开完会,接着他顺手把手里的文件递给我。我看了一眼,是关于脱贫攻坚工作安排的文件,等他说完村里脱贫工作的部署后,我说明了调研的目的,他说:“好啊,你需要了解什么,我帮你联系。”我们加了微信,互相留了手机号。10分钟后,他又去镇里开会了,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中午到家里来睡午觉啊。”我回答:“好的,好的。”
在城市社会的日常话语体系中,这是一句“空洞”的表述,类似于问候语“你好”,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即便当时笔者觉得“睡午觉”这种表达听着有些不太寻常,有一种过于“熟悉”的感觉,但也没仔细思考这句话有何不寻常,脑子里一闪念就让“它”过去了。当日中午调研结束,调研团队吃过午饭后在餐馆整理调研资料和讨论下午的工作。下午3点,团队继续在村民家里调研,3点半左右收到W书记的微信电话,书记问道:“李老师,你没去家里午休,家里人一直在等着,她都没敢出门。”此刻,我马上意识到上午所感知的“不太寻常”体现在什么地方,对我们而言,这是一句空洞的“交往语言”;在他看来,当我回答“好的”时,去他家睡午觉就成为一种实在的“交往事实”,而且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十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事实”。这种“事实”也意味着一种“承诺”。“承诺”了而不遵守便是“言而无信”。意识到我的“言而无信”的行为,我赶忙连续说了很多声“抱歉”。
当天的调研日志中,我写道:
今日遇到了村里的书记,他的方言很重,说话速度很快,要有些费劲才能听懂80%。分开的时候他说中午上他家里睡午觉,我以为是一种客套话,就没当回事,没想到他让妻子不出门,等了一个下午,我心里十分愧疚,觉得辜负了村书记的一片心意,也打破了村落里的一种礼俗关系。明天一定要记得去他家里睡午觉。(2019年7月4日)
中午走在H村的小路上,除了热辣辣的太阳,处处都很安静,下午3点之前,除了路过的客人之外,村民们都在“睡午觉”。对H村村民而言,“睡午觉”是一个不可缺少、富有“强制性”的日常议程。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大事。说是大事,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在四季的时间里自然而然地循环着;说是小事,是因为他们的午觉,如果有事,不睡也不是不行。显然,“睡午觉”的表述在H村的社会系统中,是村民日常的生活议程之一,外来者使得这种议程变得“十分正式”。因此,“睡午觉”这种看起来“空洞”的表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富有意味的身体行为,这种身体行为再次确认“交往的事实性”。作为一个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社会行动者,村书记在这个话语表述中,其行动和话语表述的意义是高度一致的。对他而言,每天中午睡午觉是一个议程;对于外来的我而言,中午没地方睡午觉便是这种日常议程的“匮乏”之处,村书记自然而然地通过邀请我去睡午觉以“弥补”这种匮乏。因为在他看来,在乡村日常生活中,这种“匮乏”意味着对日常议程的一种破坏,他有义务维持日常议程的完整性。
这同时意味着,如果我要“浸入”乡村的日常议程中,就必须“主动弥补”这种“匮乏”。于是,第二天中午我准时到村书记家,村书记夫妇二人都在等候着,他们洗好黄瓜、桃子,在盘子里放好瓜子,并为我整理好房间和床铺,然后去隔壁房间睡午觉了。在这一刻,我“浸入”了乡村的日常生活议程中,也“浸入”了乡村日常生活的自然节奏中。
此后几年,每次去H村调研,中午去村书记家睡午觉成了一种“常态的行为”。有时候他在微信里留言说“有事出去了,留门了”,我就直接去他家,熟练地进入家中,烧水,洗水果吃,然后睡午觉。这种日常的“习惯”逐渐形成一种更为亲近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使看起来单调、“匮乏”的话语成为“现实”和“行动”的话语,也完成了身体在场的实践。
睡午觉这种话语模式并非传统乡村独有,在很多乡镇村落,人们在工作之余都有午休的时间和地点,邀请外来者去家里睡午觉这种行为,是传统村落日常文化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村落不断开放,日常文化议程不断修正,睡午觉渐渐变成村民个体的行为,村民的家也开始凸显出私人生活的含义。邀请外来者去家里“睡午觉”这一话语,不但在表达层面,而且在行为层面渐渐“衰退”为一种“空洞的”文化表达。
(二)体验日常:吃饭这件事
当“睡午觉”这件事成为我的一个日常议程后,我开始进一步观察H村的日常。2019年7月5日的调研笔记写道:
村里最繁华的地方就是东西两条大街交会处的大槐树,白天的人流量并不大,最多也就可以看到20多人。整个村庄的结构是以一家小卖部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各往前延伸两百米左右。虽然只是个小村落,但五脏俱全,街道两旁有驾校、公园、学校(幼儿园、小学、中学),道路两边的树木经过精心修剪和打理,十分规整。街道十分干净,几乎看不到垃圾。很多家庭都养了小猫或者小狗,它们可以到处散步,随时随地趴在地上晒太阳,也不会被拴绳子或者关在笼子里,幸福指数很高。(2019年7月5日)
走在街上,狭路相逢的总是村民和不知道谁家的猫猫狗狗。由于这些猫猫狗狗太自由了,也会有外村的人来偷走狗,或者卖了,或者杀了,村书记家的狗在我去的这几年间已经丢失三条了。即便如此,村民们也不会因此就把猫狗拴起来。在村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日常节奏,也是一种日常议程。在这种节奏中,与睡午觉相对应的最为突出的议程节点为吃饭。
在H村调研过程中,临近中午的时候,村民们通常会邀请你吃饭。例如村书记在关心睡午觉这一事务之外,我们如何吃饭、在哪里吃饭也是他关心的问题。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中午在哪里吃饭?上我家去?”显然,在他们看来,吃饭是除了睡觉之外更为重要的一件事。在此后的调研中,无论调研团队的成员们进入哪一家,只要到了午饭时间,留吃饭是一句标准的话语表述。
不仅在H村,在考察其他村落时也是如此。有一次,我们去附近的村里调研,在一户人家门口遇到一个村民正在和面,聊了几句。离开的时候,村民询问道:“到家来吃个面?”这种吃饭的表述是村落日常交往的一种礼仪表达,无论是对于陌生人还是熟人而言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你真留下来吃饭,身体成为被邀请“吃饭”的在场时,就“违背”了这种话语叙述的内在逻辑,成为一种尴尬的存在。下面这几段话语将呈现这种现场,由于类似的话语每年都在重复,所以“时间”在这里被模糊,也被抽象化了。
场面1:在村里走着遇到了前任村副书记N的妻子,因为经常去家里找她丈夫聊聊村里的事情,我见过她几次。她手里拿着塑料袋,用方言说:“李老师,来了?我刚买了肉,到家里吃饺子吧。”我马上回答:“不用啦,我要带着学生一起吃饭。”她回答:“那下次吧。”
场面2:第二天,我在村里又遇到了她,她手里拿了塑料袋,里面是桃子。她用方言说:“李老师,来啦?到家里吃饭,我中午擀面条。”我马上回答:“不用啦,我要带着学生一起吃饭。”她回答:“那下次吧。”
场面3:第三天,我在村里的河边遇到了她,她正在清洗衣服,说家里的水清洗不干净。聊了几句,她说:“李老师,来村里好几年了吧,还没上我家吃过饭,中午去吧?”我回答说:“中午要和学生一起吃吃饭。”她回答:“那下次吧。”
在过去几年的调研中,我去过村民家里很多次,在街上见到村民很多次,每次都会遇到“吃饭”这种邀请。如果不吃饭的话,他们会很着急,希望赶紧找点东西给我带上,作为不吃饭的一种“补偿”。
因此,每次从H村离开的时候,我手里会有核桃、桃子、杏等。由于每年去的时间不太一样,手里的东西也会不同。例如2020年9月去村里,那一年因为霜冻,核桃歉收。离开的时候,W书记从家里拿了一袋核桃,说:“这是我从集市上购买的,特别好吃,尝尝吧。”然后,他抱歉道:“今年核桃不行,没有收成。”说完,他不停地搓着手,十分歉疚的样子。在村民看来,吃饭是一种日常议程里的邀请仪式。但是离开时带一些东西则是村落礼俗的一种必要形式,离开了这种形式,日常生活议程在他们眼里便被打断了,日常不再是日常,而成了一种“例外的日常”。因此,村书记觉得家里没有东西时,会从集市购买。在他看来,“好的东西”才是与礼俗匹配的。
基于同样的感受,从第一年开始,每年调研的第一天去村民家里前,我们都会从小商店购买牛奶、酸奶和饼干之类的东西带过去;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同样买牛奶、酸奶和饼干之类的东西去告别。在对于“吃饭”这一话语的叙述背后,是对身体在场的一种虚拟期待和交流期待。在交流的这一刻,身体获得了在场感,一旦离开了这种在场感,“吃饭”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换言之,说着“吃饭”中的身体是在场的,但是真正“吃饭”的身体是缺席的。缺席的身体与在场的身体在不同维度的体验,使得“问候吃饭”这一行为成为村落日常生活交往的固有方式。
概括而言,在睡午觉和吃饭这两种日常事件中,日常时间是抽象的,空间则是抽离的,仿佛村落的日常生活在这个瞬间被确定下来,成为日常不变的形式。研究认为,农民在时间的掌控中,是有一定阶级意识的,本土性的民间节日和地域性的季节性日程表就是一种证明。H村的日常生活议程被吃饭和睡觉这两个具体而微的时间节点凝固了,在日常的议程中,外来者唯有在凝固的时间节点才可以进入村落的日常生活,而这些时间节点与身体的体验紧密相关。
四、进入“文化活动”:身体的多重体验
“在某些领域,国家力量的进入基本是成功的。”但是在日常生活领域,是否也如此呢?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由时间场合中的片段组成的,村落的文化活动也是这一系列片段中的组成部分。因此,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同时意味着进入了日常生活的片段中,即文化活动中。H村的文化活动多种多样,在村落中与文化活动的相遇往往是十分自然的过程。就像上文所描述的人与动物的关系一样。在“文化活动”的展开中,身体成为多层次、多维度的体验载体,成为“吃饭睡觉”议程之外的多重节点,这些多重节点具有流动性的属性,呈现出如下的特征:日常展示性与即时即地性。
(一)日常展示性:从凝固到流动
在基层调研中,要具备见微知著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吃饭和睡觉之外,就是属于人类“精神”活动的部分了。那么,这个部分如何通过身体来体验呢?2022年7月的一天,我在去H村老K家路上的巷子里,发现了墙壁上开始褪色的红色贴纸,仔细辨析可以看出,这些红色的纸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婚礼的送礼情况,以名字和礼金数额为序排列。第二部分是婚礼的节目部分:这部分占据内容的80%,节目由老L主持,主要是三句半、相声、唱歌、武术等。第三部分则是分工与安排,比如大管家以及围绕婚礼所形成的组织管理部门。同样,我在村里另一个村民家里发现,婚礼虽然结束了,但婚礼依然在“现场”:进入大门,从门后面往里的院墙都盖着红色绸缎,一直延伸到院子中间。红色绸缎上的新娘新郎照片被粘贴在红色绸缎的中央。踩着地上的红毯,一直可以走到院子中间的客厅里。客厅里的老人坐在沙发上,指着客厅对面的房间说:“这是孙子的婚房,门口还贴着对联呢。”我问:“什么时候结婚的呀?”老人回答说:“春节的时候。”显然,婚礼这一原本是打破了日常生活节奏的事件,在日常生活的轨迹里被拉长了。第二年再去的时候,我发现这一家的新婚夫妇照片在风吹雨打后已褪色,但依然挂在院子的墙上。同样,贴在门口墙上的红纸,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风雨,不但颜色开始变淡了,纸张也开始碎裂,已经不完整了,却还在那里,等着大自然进一步消化,因为这些贴在墙上的东西不到一定时间是不能撕掉的。
2023年7月在H村调研时,我们“遇到”村里一位92岁高龄老人的葬礼。葬礼的安排和婚礼类似,墙壁上贴了白色的纸,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葬礼的送礼情况,以名字和礼金数额为序排列。第二部分为葬礼的节目部分,这部分的节目主要是聘请专门的唢呐团队完成。第三部分则是分工和安排,比如大管家以及围绕葬礼所形成的组织管理部门和人员。无论是婚礼还是葬礼,大管家都是村书记。村书记在H村既是行政上的管理者,也是村落日常生活节点的“理所当然的”引导者。
无论是婚礼还是葬礼,都是日常生活中被凝固的时间节点,也是文化活动的实践节点。在这些节点中,文化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平日里,“有些组成部分”并不是沉默的,而是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要素,如同吃饭和睡觉一般。婚礼和葬礼中的村民们以身体参与的形式进入日常生活中凝固的节点,透过这些节点,我们方能感知乡村日常文化活动的流动感。
如果说婚礼和葬礼这样的节点是文化活动凝固的一个表象,那么村民们在其他节点,比如春节、丰收节、五一劳动节等自发组织的活动则是乡村日常文化活动的身体自发行动。我曾经参与一个这样的文化活动,村民们以H村的主街道为展示地点,手中拿着各种乐器行走,沿着主街道走完一圈,就回到村委会一起聚餐,聚餐费用AA制。W书记说:“村民们爱好这个,他们自己组织的,村委会不管这些。”(2023年7月10日)村民们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着,走在街道上与围着看下象棋的、打牌的、看着行人的、聊天的、路过的和坐着的乡亲打着招呼,日常就在身体的具体而微的细节中,成为经验着的“身体”。
因此,婚礼或者葬礼,节日或者其他,在村民们的日常文化活动中,既是凝固的日常,也是流动的日常。无论是流动还是凝固,对于日常文化生活而言,都意味着一种展示,这种展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二)即时即地性:从技术到日常
在日常文化活动中,最能体现日常的便是日常本身了。在村民的视野中,日常意味着生活本身。比如我在微信里询问W书记:“最近怎么样?”他回答:“还是那些事情,没变。”“没变”就是日常生活的底色。那么,这里还是从日常的底色入手观察。
H村有一条河,村里的公园依河而建。由于H村里的自来水是定时供应,村民不舍得在家里洗衣服,通常会去河边洗。在河边走一走,就会遇到在那里蹲着洗衣服的村民。2024年7月9日,我在河边遇到一位村民F,他身着红色的T恤衫和深蓝色的裤子,脚穿一双运动鞋,鞋面十分干净,看起来像是全新的。他正在洗衣服,说到村里的文化活动,他说:“唱歌啊,直播啊。”他自幼喜欢唱歌,参加过全国歌唱比赛。他家的院子靠着村边的路,临街开了一家农机服务商店。他说着放下手里正在搓洗的衣服,拿起放在地上的手机,熟练地从手机里找到歌曲伴奏播放出来,准备开唱。我询问他介不介意手机录视频。他痛快回答:“好!”于是,他站在河边,声音洪亮地唱了起来。河边洗衣服的身体成了唱歌的身体。观看他演唱的我们,也成了河边听歌的身体。唱完一首歌曲,他问道:“你们要不要跟我去看看唱歌直播的村民家里?”我问道:“是不是会耽误你洗衣服?”他笑着说:“没事。”
我们来到一家根雕和农机服务店铺,有几位村民正在讨论农机价格问题。店铺里的直播设置背景、三脚架都很显眼地放在那里,直播的背景后边是一幅山水画,直播台是一个大型的根雕。村民F和直播村民M(也是店主)说,我们要看看他直播唱歌的场景,M很开心,说:“下午吧。我来直播。”大约3点,店铺关着门,M和太太还在睡午觉,我们敲门后,他们起来洗了一把脸,打开三脚架,放置好手机,进入抖音账号,拿着旁边自己打印的歌谱,唱了起来。直播持续了3个小时,我们就在旁边观看了3个小时,调研团队成员也参与直播,唱了一首歌曲。其余唱歌的都是进来的村民,他们有的是本村的,有的是外村的,进了店铺,询问了农机信息后,看到M在直播就拿起话筒唱歌。其中一位村民唱了3首歌曲,其余的唱2首。村民来来往往的,十分热闹。但是即便歌声嘹亮,也没有来围观的村民。在他们看来,随时随地唱歌,也是日常议程的组成部分,直播唱歌不过是另一种唱歌形式。
生活在这一刻,如此系统化地被嵌套在一起,成为一种凝固的程式。无论是河边唱歌的F还是随机直播的M,他们都将对乡村日常文化活动的兴趣“浸入”个体选择层面。在这一刻,他们不单是H村的村民,而成了他们自己。
五、方法论探讨:“现在时”中的我、他者及其他
由于日常“使不熟悉的事务变得熟悉了;逐渐对习俗的溃决习以为常;努力抗争以把新事务整合进来;调整以适应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日常就是整个过程或成功或挫败的足迹”。那么,“浸入”乡村的日常文化现场,观察“现在时”的乡村文化生活,并将重心放在身体经验维度上,在方法论意义上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呢?
第一,本文是一个个案研究。“个案研究需要运用人文地理志、制图术、人口志、历史编纂学、传记学、语词编纂学等各类民族志方法,通过‘事件化’的社会激活过程,呈现出多重社会构成的脉络。”如何形成多重社会构成的脉络呢?换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表述便是:个案研究如何走向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典型化或者普遍化?有两种路径,即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类型学研究范式和人类学者提倡的“个案中的概括”。本文的研究则是属于其二,即“个案中的概括”:首先,我们在对村落日常的观察中发现,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经验,是围绕着日常时间的维度展开的,吃饭和睡觉成为日常生活的两条主导脉络。外来者的身体进入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经验也被纳入本村人的身体体验系统中,形成基于本村人身体经验的外来者的身体经验。这两种身体经验在日常生活中混合与交融,“浸入”乡村的日常生活脉络中。其次,从日常文化活动出发可以发现,村民的文化活动源自凝固与流动两种日常。这两种观察结果既是对个案的一种描述,也在试图对个案的特殊性进行类型学方面的概括。由于这种概括源自研究者一开始对村落选择的“试验”属性,便显得有些不寻常,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如此进入乡村研究在路径上是有“缺陷的”。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乡村工业化、社会信息化、人口流动和数字化等外来因素冲击后,中国乡村仍然以各种不同形态存在,而不是走向简单化意义上的终结,其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文化、社会和制度原因。因此,超越类型学的个案和概括性的个案,以一个在学术研究中“不那么典型”的村落作为个案展开研究,理应在经验研究的乡村个案维度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如何处理个案中的时间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当下的乡村研究中,各种各样的观察法成了流行的方式,辅之以访谈法,在文本呈现中就会将这些具体人物作为代号,成为研究的佐证材料。由于本文主要源自对村落的参与式观察,即对村落生活的观察、对村民行为的观察、对村落文化形式的观察。基于本文的上述资料描述,不可回避的问题便出现了:村民的日常时间与观察者的时间如何在观察对象身上实现统一?如果无法统一的话,这些观察资料是在何种维度上与村民的“现实日常”对话的呢?因为,观察者希望进入这两种文化活动议程中时,会发觉几乎不太可能对话,观察者只能做日常文化活动的旁观者,比如进入日常文化现场进行观看,又或者通过日常文化活动痕迹进行反思。在这两种过程中,观察者往往被村民看作日常文化活动中的“大惊小怪者”或者“陌生人”。观察的时间因素在此需要更多的关注:无论是观察者还是旁观者,都是针对具体的某一时间维度而言的,这些观察结果与村落绵长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得到有效的处理,才能便于学者在对观察结果进行解释时,不仅仅是站在写作的维度,而更多地站在社会发展维度上。这就需要延长观察时间,即选择每一年的固定时间节点进行观察,进行反复比较,逐步建立起时间与观察对象之间的“活”联系。
最后,在上述问题基础上衍生出第三个问题,即处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他者与我是否具体而微地处在“同一个身体经验”中?我们的身体有日常的历史,既有个体的,也有集体的,更有社会的。在这些不同的身体历史中,源自多个系统中的我与他者,如何成为我们?或者完全不需要成为我们,只要“成为他者在场”即可呢?又或者说,我们将观察视野放在身体经验上时,如何将身体与身体的历史关联起来,而不是仅仅将身体看作瞬间的身体?
上述这些问题,仅仅是对于日常生活中文化现象观察的反思,想要更好地进入田野,获得丰腴的文化经验材料来对正在演变中的乡村文化进行阐释,村落个案只是一个起点。时间就在田野里,田野也在时间里。每次我们回头,都会发现新鲜的资料在召唤,唯有不停地返回田野中,回应这种召唤,进而不断进入对文化的深描中,才有可能不断接近乡村文化的原貌和全貌。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李红艳.从生活传承维度进入乡村文化活动:一种方法论反思[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5,(01):43-57.
作者简介
李红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