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十一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跨文化平视理解》,作者张路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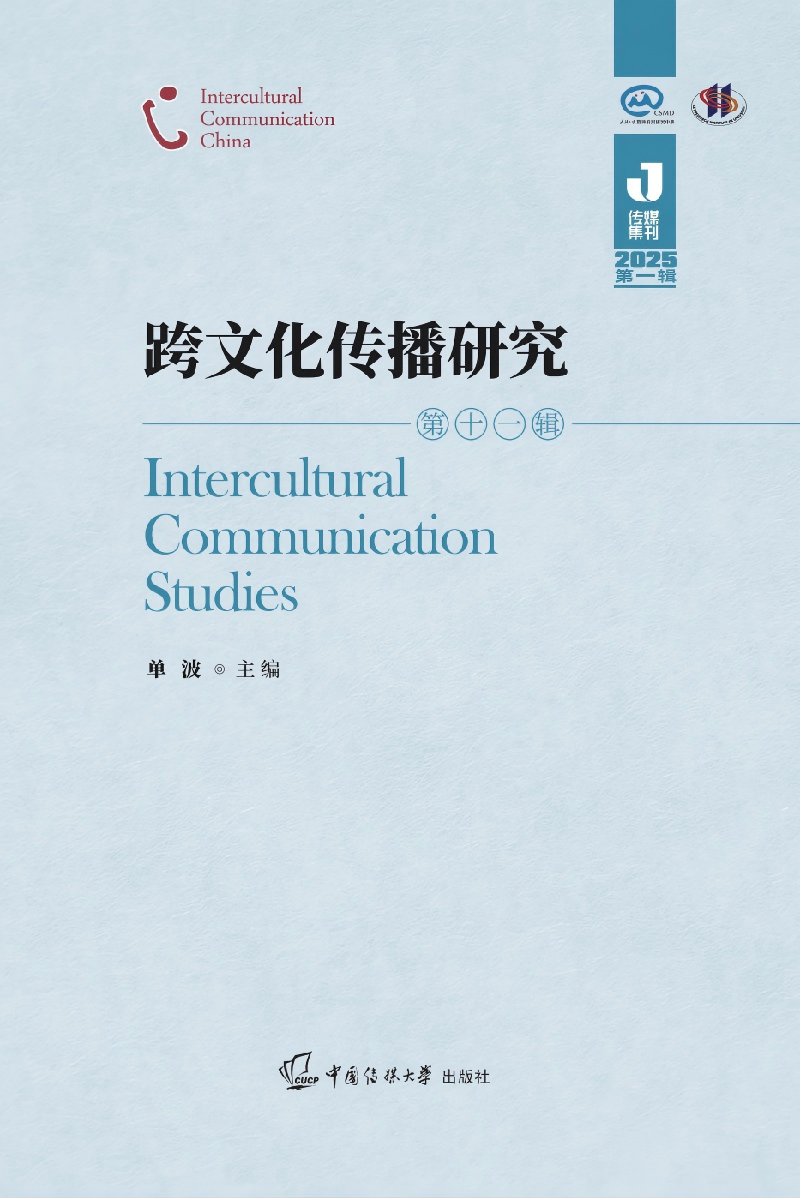
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跨文化平视理解
张路黎
摘要:克利福德·格尔茨于20世纪50~60年代到印度尼西亚、摩洛哥从事田野调查,敏锐地在后殖民语境、跨文化交往中抛弃西方学者的优越感,而平视当地民众,入乡随俗,感同身受,“置身于他人之中”,以他人的眼光看自己,获得当地人的接受与认同。他以平等的心态观察、体认、理解,致力于个案深描,获得地方知识。他的《文化的解释》和《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等著作正是跨文化平视理解的代表作。这种跨文化平视理解的方式为我们考量世界价值观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参照。
关键词:克利福德·格尔茨;平视;后殖民;深描;地方知识
在跨文化交往、传播以及调查研究中,看待对方的视角至关重要,大致有俯视观察、仰视接受、平视理解三种看待方式。俯视视角往往表现出观看者高人一等的心态;反之,就是仰视视角;不仰望对方也不歧视他者,可称为平视视角。
20世纪后期的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通过在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身体力行的田野作业及其文化阐释,引起广泛关注,其特点正是在跨文化观察体验中平视对方,深描个案,书写地方性知识。不同于殖民时期人类学家俯视“野蛮人”的姿态,格尔茨不是居高临下,不是显摆优越感,不是发现新大陆;而是在不同文化的后殖民处境中,平视他者,以平和心态深入当地情境,与民众平等交往,体认深描,获得地方知识,其关键在于“平视”。
一、平视与后殖民语境中的格尔茨
什么是平视?平视是相对仰视、俯视而提出的,它们是观看、体察对方的三种不同态度。所谓仰视,是一种以仰望的心态将对象神圣化,崇拜英雄伟人的观看方式。所谓俯视,是一种以居高临下的心态看对象,俯察低等人物的观看方式。而平视不同于仰视和俯视,平视是以平静的心态看世事,以平等的身份写人物,以平和的声音讲故事,并希望接受者平等参与对话交流的观看体察方式。
在汉语典籍中,“平视”出自汉代经学与史籍。《礼记·曲礼下》的“衡视”,郑玄注:“衡,平也。平视,谓视面也。”《三国志·刘桢传》裴松之注:“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此语称赞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当贵人出现之时,具有不卑不亢的神态。平视,不同于俯视黔首和仰视权贵的方式。古代帝王俯视臣民,强迫民众仰视帝王或上帝。平视他人则十分可贵。
在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往中,常出现仰视、俯视、平视的不同方式。虔诚的教徒到远方朝圣,就怀着一种顶礼膜拜的仰视心态;而殖民者以及自视高贵的学者则以俯视的眼光观看殖民地与其他落后地区的原住民,同时强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顺民仰视接受殖民者的治理。格尔茨曾以辛辣的笔墨讽刺那些俯视他者的人类学家:“在很多经典的民族志中,都有人类学家站在他的土著中间的照片”,来自西方的人类学家高高站在照片中央,而围着他的土著往往“表情呆滞地凝视着镜头”。
近年来关于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平视、俯视、仰视”已被运用于表述作者的不同视角和跨文化交往的不同心态,例如《对外传播》发表的《从俯视到平视从宏观到微观:近年来外媒涉华报道视角变化案例分析》等论文。特别是在殖民时期及在后殖民语境中的人类学著作中,更明显可见平视或俯视他者的不同叙述视角。如费孝通所说:“读了《金枝》我们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金枝》是早期人类学名著,明显表现出白人学者弗雷泽(英国)俯视原始土著的心态。再如,赫赫有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也是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俯视他者的代表。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是一部获得过盛赞的著作,而格尔茨直率地批评那只不过是“失望的浪漫主义”碎片,因为列维-斯特劳斯怀抱的是“作为第一个揭开土著社会秘密的白人”的兴奋憧憬,他一旦遇见了印第安人,便感觉“他们都太野蛮了”“我可以触摸他们,但是不理解他们”。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列维-斯特劳斯著作中的殖民主义俯视心态:“因为他已经用他自己的文化污染了他们”,“遮蔽了他们”,因而“不能与他们沟通”。格尔茨又在《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一书中再度批评列维-斯特劳斯:“他的探索以无果和失败告终。当他最后遇到他长期寻找的终极野蛮人”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是不可即的”。
开创田野民族志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凭借《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蜚声学界,却因身后被人出版《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而泄露心语。格尔茨在《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中摘引了马林诺夫斯基日记中的某些语句,分析了他作为白人学者俯视原住民的双重人格心理。一方面,马林诺夫斯基长年身居远洋海岛,“加入蛮人”践行田野,“见野蛮人所见,思野蛮人所思,说野蛮人所说”,作为“赤身裸体的野蛮人的记录者和代言人”,欢快于“我将是创造他们的那个人”;另一方面,他又在内心把那些原住民看成“新石器时代的野蛮人”,甚至是“畜生”,因其“粗暴”而沮丧、愤怒,陷入“参与观察”愿望的“困境”。
其实,马林诺夫斯基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是绝顶聪明的智者,在各自学术领域的建树无人匹敌,他们为什么陷入人格矛盾与沟通困境呢?就因为他们属于殖民时期的人类学家,未能跳脱西方殖民霸权话语的窠臼,不可避免地成为适合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需要的学者,如格尔茨在《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中所说的从事“作为帝国主义延续的人类学写作”。因此,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都显露出自以为高贵而俯视“土著”他者的痕迹。
格尔茨与他们不同,他20世纪50年代才步入人类学领域。与他的前辈学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格尔茨处在后殖民语境。二战之后,亚非拉先后有100多个民族国家获得了独立,不再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格尔茨自述1952年开始到印度尼西亚从事田野调查,1963年开始到摩洛哥从事田野调查,正是在这两个国家独立之后。印度尼西亚曾经沦为荷兰殖民地,二战中被日本占领,战后独立。摩洛哥遭受法国和西班牙入侵,沦为“保护国”,1956年获得独立。格尔茨从事田野调查之时,这两个国家刚刚独立不久。在田野实践中,格尔茨明显地感觉到:“殖民主义的终结彻底改变了那些询问和观察者与被询问和被观察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作为人类学家主要写作对象的人们被殖民者变成了主权国公民”,就“完全改变了民族志实践发生的整个道德场景”。时代不同了。格尔茨与他的前辈人类学家不同,他的田野调查正好赶上亚非拉国家独立浪潮兴起,他身处民族运动高涨的第三世界,面对的是后殖民时期的主权国公民,西方学者此时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拥有殖民者的霸权。这就为平视原住民创造了客观条件。
当然,更重要的是,格尔茨能跟上时代,进入后殖民语境,自觉调整自己的位置。他清醒地认识到“田野工作情境的固有的道德不对称性”,跨越文化隔阂,平视对方,“以了无牵挂的眼睛去看待他本人与他的报导人”,去沟通、交融,达到默契,从而使他在印度尼西亚、摩洛哥田野作业时能够深入认知调查对象,获得地方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格尔茨的田野调查和著述出版早于后殖民主义的兴起。一般认为,1978年萨义德推出《东方主义》开启后殖民理论。而格尔茨在20世纪50年代从事田野调查就写出民族志《爪哇的宗教》,60年代出版《旧社会与新国家》等著作,他的重要代表作《文化的解释》出版于1973年,比《东方主义》早5年。《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已不止一次用到“后殖民”一词。格尔茨在此书中写道:“1945年至1968年间有66个‘国家’从殖民统治下获得了政治独立。”他把这些国家称为“新兴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他用了好几章来论述“新兴国家”,作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
应该说,在后殖民主义兴起之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早就开始了。二战以后,随着一大批前殖民地国家独立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西方学术界也扩展到第三世界,思想敏锐的学者包括格尔茨等人率先意识到这种变化,率先反思。身处后殖民语境中的格尔茨反思了殖民历史,他在田野工作搜集的资料中发现了一篇19世纪西方作者记录巴厘岛献祭仪式的文章。其中描写了国王的三个妃子为国王投身火海殉葬的残忍情景。但其结论是,根绝这种殉葬痼疾,是西方文明征服和取代之的“坚强理由”。格尔茨批判说:“通过一声反对压迫女性的怒吼,将整篇文章变成了为帝国主义张目的论证。正因为要彻底消灭这种臭不可闻的痼疾,西方就得到了征服并改造东方的坚强口实。”时至今日,还有强国借口弱国非人道而企图去征服;相比之下,一个西方学者能够彻底抛弃种族偏见,以全人类的视野平视东方与西方,一针见血地揭穿殖民主义的歪理。这让人不能不钦佩格尔茨的思想境界和胸怀。
作为一个从事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的人类学家,格尔茨敏锐地意识到殖民主义终结发生的变化,他对批判帝国主义、领先后殖民思潮的人物十分关注,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到福柯、法农,称赞甘地、真纳、法农等人为“呼唤民族觉醒的理论家”。他处在后殖民语境中,自觉地平视原住民的田野,故能创造不同于前代学者的话语,以其独特的深描方法推出刷新耳目的民族志著作。
格尔茨意识到,原殖民地国家不欢迎曾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服务的人类学家再去做实地调查。一个西方学者,到新兴国家从事田野调查,首先得放下白种人的架子,消除当地民众的疑心。譬如,他自述初次进入巴厘村庄之时“怀着不确定而又渴望与人沟通的心情”四处徘徊,而当地人“对我们视而不见”,“实际上村民们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而且他们掌握着大量相当准确的关于我们的信息”,但他们的样子“就仿佛我们根本不存在”。怎样取得村民们的信任呢?转机发生在当地一场斗鸡活动遭遇突然袭击之时。“斗鸡”是巴厘岛的一种习俗,尽管政府禁止,但巴厘人依旧半秘密地举行,此次是替学校筹集资金,人们便以为不会受到干预。格尔茨夫妇也在一旁观看。比赛正酣之际,哪知一卡车警察突然降临,村民们马上四散而逃。格尔茨夫妇也本能地跟着村民逃跑,跌跌撞撞,显得惊慌失措。没想到这一跑,倒跑进了巴厘人的世界。让巴厘人高兴又吃惊的是,这两个美国人没有掏出证件向警察表明其与众不同的身份,却甘愿与村民为伍。村民们还一遍又一遍地模仿格尔茨逃跑时不优雅的样子。“在巴厘岛,被取笑就意味着被接受。”跟着逃跑,成了一个转折点,由此,他们不再被视为“入侵者”,而获得当地人的认同,整个村子都对他们开放,田野调查得以顺利进行。可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平视”,在于平等相待。
在后殖民语境中,格尔茨坚持入乡随俗的原则,放下身段,平视当地人,甘愿与当地人为伍,从而获得当地人的接受与认同。再如格尔茨发现,当时出版了一些关于印度尼西亚宗教的书籍,当地人对这些书籍的兴趣非常强烈,而殖民时期是禁止传播这一类读物的。于是,格尔茨想到为村民提供阅读方便,他写道:“我买了一些这类书籍,并将它们放在我在村里的住房附近,我们房子的前廊变成了阅读中心,成群的村民来到这里,坐上几小时,互相朗读这些书,时不时地评论书中的意思。”只有他平视当地村民,村民们才乐于走进他的阅读中心,这也表明格尔茨获得村民的认同。格尔茨的村民阅读中心,可以说是后殖民语境的一个形象标志。广大民众不接受高人一等的歧视,你能平等待人,他们才会平等待你。
二、深描中的平视视角
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第一章以“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为题,提出“深描”作为其民族志写作的创新方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深描,或译为“深度描绘”“浓描”等。许多读者、评论者都把深描视为格尔茨阐释人类学的代表方法。
在《文化的解释》中,格尔茨自述“借用吉尔伯特·赖尔的一个概念,就是详尽的‘深描’”。深描,不同于“浅描”。例如,对眨眼的“浅描”就是“迅速地张合眼睑”;而“深描”就可能是:“挤眉弄眼”“递眼色”“送秋波”“假装挤眼”“模仿假挤眼”“练习模仿假挤眼”等。从格尔茨的著作来看,“深描”其实是指人类学者平视其考察对象,从而对其中的文化意义进行多层次、有深度的描述和解释的手法。
仅仅说深入描绘是不够的。以前的人类学家也要求田野工作参与观察、深入描绘,献出一些深入细致的民族志。格尔茨的“深描”应该说不同于功能主义、不同于科学主义,也不同于结构主义的深入描绘。那么,深描的特点是什么?格尔茨的“深描”与之前的深入描绘有何区别?
格尔茨的“深描”,首先是平视其考察对象而如实记录。在跨文化的后殖民语境中,格尔茨描叙的犹太人科恩、表演皮影戏的爪哇人、演出巴龙舞剧的巴厘人、摩洛哥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爪哇莫佐克托的居民、参与斗鸡游戏的村民等,都是平视观察、平等言说的对象。平视,不是带有殖民色彩的俯视与歧视,当然也不是仰视。我们知道,格尔茨笔锋凌厉,善于诙谐戏谑,对身份高贵的欧美大师也曾予以尖刻讽刺;可是面对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等地的居民——田野作业的对象,他从不傲慢,始终保持平视的心态。
例如《文化的解释》第六章描述爪哇莫佐克托小镇一场被中断的葬,当地民众分为桑特里和阿班甘两派,前者的政治派别是玛斯尤米,后者的政治派别是波迈。但讲述者格尔茨无论是对正统穆斯林的桑特里,还是对本土倾向的阿班甘,都一样平视相待,客观叙述,没有歧视任何一派。平视,并不是毫无情感地机械叙述,作者在平静的描述中,对住在姨父姨母家的十岁男孩的不幸去世深表同情和惋惜。由于葬礼主持人莫丁与男孩的姨父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仪式一度中断。男孩的父母远道赶来,葬礼才终于完成。在三天后的斯拉麦坦仪式上,一个当地人物指着格尔茨说:“想一下这位美国人问你:什么是这个国家的精神基础?而你不知道,你不感到羞愧吗?”对于这种明显的冒犯,格尔茨并不计较,转而冷静地记叙了那位不幸男孩的父亲讲话的情景。男孩的父亲一直面无表情地安静地坐着,突然开始说话,声音温和,语调令人惊奇。他说:“我一直努力要做到艾克拉斯(超脱)……我自己并不很热衷宗教。我不是玛斯尤米也不是波迈。但是我希望孩子能以传统的方式入葬。我希望没有人受到伤害。”他说,他的妻子,现在也稍微艾克拉斯一点儿了。虽然这很困难。他反复告诫自己,这只不过是神的意愿。但是做到这一点如此困难,因为现在的人不能对事情取得共识;一个人告诉你一件事,另一个人告诉你另一件事。很难知道哪个是对的,弄不清该相信哪个。他很感激所有来参加葬礼的莫佐克托人。他说,他正在努力做到艾克拉斯。到场的每一个人都因为这位父亲的话而受到震动,现场出现了痛苦的沉默。这真是一段了不起的深描实录,不动声色之中,这位无名父亲的形象超越了政治与仪式,超越了东方与西方,令人尊敬,令人难以忘怀。可见,平视观看、如实记录就是格尔茨深描的特点之一。
就民族志而言,单一的描叙不是深描,深描是多层次的文化解读与描写,并且往往是跨文化的。如格尔茨告诉我们:“民族志描述有三个特点:它是解释性的;它所解释的是社会性会话流;所涉及的解释在于将这种会话‘所说过的’从即将逝去的时间中解救出来,并以可供阅读的术语固定下来。”这段话包括三点:一是解释性;二是社会性会话流,即鲜活的文化,含义丰富;三是固定于文本。格尔茨自己为“深描说”举的例子,取自他的摩洛哥田野日志中的一段“科恩的故事”,是在1968年收集到的一件1912年发生的事。犹太商贩科恩遭到柏柏尔人抢劫,科恩逃去向法国殖民军团告状,然后带着玛穆什酋长和一队人去报复,夺得了柏柏尔人的一群羊,而法国军团把科恩关进牢房,没收了那群羊。这个殖民时期的故事包括三种不同的解释框架:犹太商人的、柏柏尔牧人的、法国军团的。这简直就像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格尔茨并没有给他记录的故事定下唯一的实证结论,反而为之设想了故事走向的多种可能性。他说:“关于羊的那些冗长而杂乱的言语—假作的偷盗、赔偿性移交、政治性没收—本质上是(或曾经是)一次社会性对话。”社会性会话流本来就不是单一的,民族志应该保存其多义性。因此,深描就是“追溯社会性对话的曲线,把它固定在一种可供考察的形式里”。
需要强调,深描是微观的描述,是通过当地人的个案来述写民族志。格尔茨说,深描还有第四个特点:“它是微观的。”深描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就是说,深描不是概括科学规律,也不是机械照相,需要的是微观个案,平视观察,从而展示当地人特殊的性情、生活基调与氛围。备受称赞的深描之作是格尔茨1972年发表的《沉溺性赌博:论巴厘人的斗鸡》,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题为“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斗鸡现象中外古今普遍存在,而巴厘岛的斗鸡情景经由格尔茨的深描得以彰显,几乎独占鳌头。其描述中可见,斗鸡习俗乃是巴厘文化的一种符号,是巴厘岛民社会生活的载体;斗鸡中出场的公鸡实际上是巴厘男性的象征,是巴厘人权势、等级与荣誉的象征,也是人性中兽性的象征。因此,巴厘人特别精心养鸡,“人们眯着眼睛以钻石商人一般的专注检查它们是否有弱点”。巴厘男子可以把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训练公鸡上,格尔茨说:“我的房东,一个按照巴厘人的标准只是很普通的爱好者,经常在他又一次挪动笼子,又一次给鸡洗澡,又一次饲喂它们时这样念叨着:‘我是雄鸡迷。’”在斗鸡场上,受伤公鸡的训练者一直发疯似的为那只鸡忙着,“他向鸡的嘴里吹气,把整个鸡头放在自己嘴里吸气和哈气,为它抖松羽毛,给它的伤处敷各种药物,他会做所能想到的任何事情,以激发起或许藏在鸡体内什么地方的最后一点斗志。在他不得不把鸡放回赛场的时候,他时常弄得到处是鸡血”,坚持拼命只是为了斗鸡取胜。正是由于格尔茨以平视心态深入田野,得到村民认同,他才可能入乎其内,将斗鸡的微观情景记述得惟妙惟肖;当然,他又能出乎其外,深入进行跨文化分析,看出斗鸡这种沉溺性赌博,不仅是为了金钱的输赢,真正博弈的是巴厘人的名望身份,是巴厘社会结构与地位关系的戏剧化呈现。巴厘人的散漫与威武、沉静与凶狠、优雅与嫉妒、妩媚与残暴等各种情感欲望、性格气质、深层心理与价值观念在斗鸡游戏中一展无遗。任何关于巴厘岛斗鸡的文本都不如格尔茨的深描那样活灵活现。
再如,格尔茨描述巴厘民众参与表演巴龙舞剧的微观情景:“当似乎浪达最终要占上风时,一些鬼魂附体的迷乱的人站起来,手里拿着短刀,冲上来支持巴龙。然后浪达急速地退回庙里,躲开被激怒的人群。我的信息提供人说,这些人如果看到她孤立无助会杀了她。巴龙在手里拿着短刀的舞者中走动,对他们敲响牙齿或是用胡子刺他们来把他们弄醒.……他们还是迷乱的,他们在沮丧中把短刀转向自己的胸膛。通常在这时真正的大混乱在人群成员中,男女都有,爆发了,在剧院里的所有人都落入迷乱状态,冲出来刺杀自己,互相扭打,吞活鸡或粪便,痉挛地吞下泥土,等等。”格尔茨详尽地描述巴龙舞剧的表演过程,对巴厘人来说,它不仅是可供观看的场景,而且是一种可投入操演的仪式。格尔茨由此表现当地的宗教仪式与神灵崇拜。
如果一部民族志遗漏了考察对象的性情与生活氛围,那就是重大缺失。格尔茨2001年发表《走访:评蔡华著,<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一文,评蔡华所著《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文章正面肯定了蔡华这部著作的贡献,同时指出:“本书有一个严重的漏洞,一个难以忽略的缺失,即几乎见不到纳人生活的基调和氛围,以及他们的性情和经历,只有很少几处匆匆地、简略地提了一下。书中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关于个人情感和判断的记述,也没有对于希望、恐惧、异议、反抗、幻想、懊悔、骄傲、幽默、失落或者失望的记述。”可见人性情感、喜怒哀乐、生活基调和氛围都是格尔茨解释人类学与深描民族志不可缺少的内容。
三、平视视角与地方性理解
格尔茨的另一部力作《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于1983年出版。他在《序言》中自述从《文化的解释》开始倡言“意义的网络”和“深描”的主张。如何理解“地方知识”?关键在于平视地方、阐释文化、编织意义之网。
众所周知,格尔茨深受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他引用韦伯之语来阐释文化,成为一个著名的比喻。《文化的解释》开篇就说:“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这一比喻非常形象,从格尔茨的文化理论与民族志实践来看,他所说的“意义之网”,每个网眼、网结都不一样。
“地方知识”正是编织意义之网的网结。格尔茨认为,人类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寻求规律,不追求实证,不要求普遍性,“人们写不出一部《文化解释的普遍理论》”,民族志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因此不宜采用数理统计、样本测量、自然试验等做法。需要的是平视与深描,由于平视,才能发现地方知识;通过深描,才能写出合格的民族志,编织意义之网。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出版的同一年,格尔茨受邀于全美人类学年会上做了题为“反‘反相对主义’”的演讲,全文首次刊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1984年6月号。这篇演讲显然与格尔茨关于“地方知识”的思考相关。
反“反相对主义”,是十分聪明的提法,表明格尔茨“既不是虚无论者,也不是主观主义者”,不是相对主义者,但更不同意反相对主义。他巧妙地运用二律背反和双重否定来表达看法。一般认为,所谓相对主义,强调事物的特殊性与相对性。所谓反相对主义,强调事物的绝对性与普遍性,而否认相对性与特殊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鲁思·本尼迪克特等人,即格尔茨的前辈学者,不满于文化殖民主义和种族中心论,提出文化形态无高低之分、每一种文化都值得尊重的观点,或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这种尊重差异并要求互相尊重的思想应该说影响了格尔茨,使其田野考察顺利进行。譬如语言,人类各民族、各地区语言不一致,存在相对的合理性,不可能绝对一致。但是语言可以翻译、可以跨文化沟通,并非完全隔绝;而个别之处又很难翻译,影响跨文化交流。于是新的反相对主义和普适主义跳出来批判相对主义,反相对主义的西方学者又发文章又出版著作,宣称“相对主义必败,而普适主义有朝一日可能胜利”。企图“通过消除文化多样性的效力来解除文化相对主义的威胁”。这正是格尔茨发表反“反相对主义”演讲的背景。格尔茨称之为“热切的普适主义”或“咄咄逼人的唯科学主义”。格尔茨指出不是相对主义干扰了“绝对运动”,也不是相对主义干扰了“神圣的道德观”,使其混乱的乃是异常现象与异常现实。他说:“大多数人以及我本人,都是过于拘执于某种事物,或准确说,常常是受地域局限的。”因此,“我自己觉得地域主义乃是一种更真实的关切”。这篇演讲中提到的“地域主义”应该是与他所论述的“地方知识”相一致的。
格尔茨进而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的导言中提出:“以他人看待我们的眼光那样看我们自己。”他的《反“反相对主义”》演讲也说:“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透视镜去观看其他人类生活的,其他人类也是通过他们自己的透视镜来回看我们的生活的。”这两处的“看”正是格尔茨以平视视角看田野考察对象和写作民族志的一种表述。与《反“反相对主义”》相呼应,格尔茨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的导言中批评普适主义“一以贯之的大理念”宣称建立穷尽所有社会事物的“普遍性理论”和“建立一套囊括万物之科学的理想”为“自大狂”。格尔茨又在1999年为《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2000年版写的序言中说:“一切的发展都在强化以个案为基础的知识”,同时认为“一切的知识都试图企及数理物理学的境界或甚至更离谱的图表经济学”的观念已荡然无存。于是,格尔茨就“尽力把这些个殊之物”拉近,“用一种能使它们相互辉映启迪的方式把它们联系起来”,编织成网,“把特定类型的现象放在能够引发回响的联系中”,这就是格尔茨的地方知识之网,每个网眼、网结都不一样的文化之网。
从格尔茨的田野考察与民族志深描来看,他给我们展现了摩洛哥的山村、爪哇的宗教、巴厘岛的献祭仪式、皮影戏、巴龙舞剧、斗鸡习俗等种种个案,展现了跨文化平视视角所见的地方知识的特点。
例如,格尔茨所举“巴厘人定义人的规则”就是一种典型的地方知识。他通过田野调查详细地了解到,在巴厘岛,一个人的“标签”——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称呼——有六种,按顺序分别为:一、人名;二、排行;三、亲属称谓;四、从子称呼;五、地位头衔;六、职务名称。格尔茨将它们命名为“定义人的符号规则”,依次考察。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来看显然觉得太复杂,其实这六种称呼在中国都有,并且比巴厘岛的更复杂。譬如第一,人名,中国人的名字包括姓、名,又分小名、学名,还有表字。第二,中国人的排行:伯、仲、叔、季,古已有之。第三,亲属称谓,父子祖孙,更不可少,巴厘人仅仅追溯到上下三代或四代,中国人则有五服九代,亲戚称谓复杂细致得全世界少有。第四,从子称呼,即孩子他爹、孩子他妈,中国民间十分普遍。第五、第六,公众场合自然以头衔身份、地位职务相称。此外,中国人还有众多的别号、诨名、绰号、尊称、谦称来称呼不同人。从亚太文化圈来看,印度尼西亚的称谓文化很难说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惜格尔茨受到局限没有来中国考察,要不然他就不会感叹巴厘人的称谓多了。格尔茨显然对“排行”称呼很感兴趣,他在《文化的解释》第十四章叙述了巴厘人的“排行名字”,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第三章又一次介绍巴厘人的“排行”。他阐释说,生育构成一个“头生的”“二生的”“三生的”“四生的”这一“循环链”,“重复应用一个无止境的四阶段的不灭的形式。在肉体上,人们来去匆匆,但是在社会上,当新的老大或老四从永恒的神的世界中(因为一个婴儿离神也是一步之遥)替代逝者再次溶入神的世界时,剧中人物永远是不朽的”。他认为:这种出生次序命名体系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延续,一个永不磨灭的形式之无止境的四步骤反复。从肉体上来讲,人如蚍蜉般生生灭灭,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演出的人物却能够代代相传”。格尔茨如果接触到中国的《易经》也许会更为感慨,《易经》六十四卦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系统,从乾卦依次到未济卦,再到乾卦;六十甲子、二十四节气、春夏秋冬四季也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东方文化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观,用格尔茨的说法,可能也是一种地方知识。
格尔茨提出的“地方知识”中,最可贵的是平视弱者个体,体现了西方学者不再俯视前殖民地区平民的进步观。例如上文所引《文化的解释》第六章中对那位不幸男孩的父亲的描叙,再如《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第八章写到的巴厘岛村民瑞格瑞。
瑞格瑞这位普通村民诉请村议会帮他把私奔的妻子找回来。村议会的人虽表示同情但没办法也没能力采取行动,瑞格瑞于是拒绝承担村里的轮值义务。根据写在棕榈叶上的村落法律,拒绝履行义务将“自绝于村落”。对于大家苦口婆心、软硬兼施的劝阻,瑞格瑞毫不理会,因此被村议会依法除籍。此案发生在1958年,当时惊动了巴厘岛的前国王、新政府的地区长官。地区长官曾驾临该村为他平反,村民们皆跪拜迎驾,却无法从命。可怜的瑞格瑞竟然遭到放逐而流浪,精神失常,语无伦次,被彻底抛弃。一个可怜的人遭到非人性的放逐,却无可奈何。格尔茨十分平静地深描此案,对涉案各方皆无褒贬,体现了一种平视弱者的眼光。此案成为“地方知识”的代表之一,被广泛引用。
值得提醒的是,有的评论者把格尔茨倡导“地方知识”夸大为对“西方中心论”或“我族中心观念”的挑战。如果说是挑战,也只是西方学术界内部的“挑战”。我们应该清醒:巴厘的习俗,或者中国的文化,在西方学者眼里,恐怕只不过是一种地方知识而已。格尔茨细致观察异国平民的生活情景,其范式之可贵在于平视弱者,并不是把弱者提升到中心地位。在他的民族志文本中,实际上描写了当地的许多落后面,譬如上面提到的可怜的放逐、沉溺性赌博、农业的内卷、火葬活人献祭等。
格尔茨只是一名跨文化的处境观察者。他并不希求改变现状,而只是给我们提供一种跨文化平视理解的方式。他写道:“以他人看待我们的眼光那样看我们自己,可能会令我们大开眼界。”在跨文化交往中,如果双方都能平视对方,就达到理想化了。“置身于他人之中来看我们自己,把自己视作人类因地制宜而创造的生活形式中的一则地方性案例”,乃是一种宽宏博大的境界。这种平视理解对于考量世界价值观,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参照。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文化传播视野下当代价值观调查项目的中国认知研究”(项目编号:GSY21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用参考
张路黎.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跨文化平视理解[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5,(01):69-83.
作者简介
张路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