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十一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田野旅行:一项跨文化民族志研究的实践与反思》,作者金玉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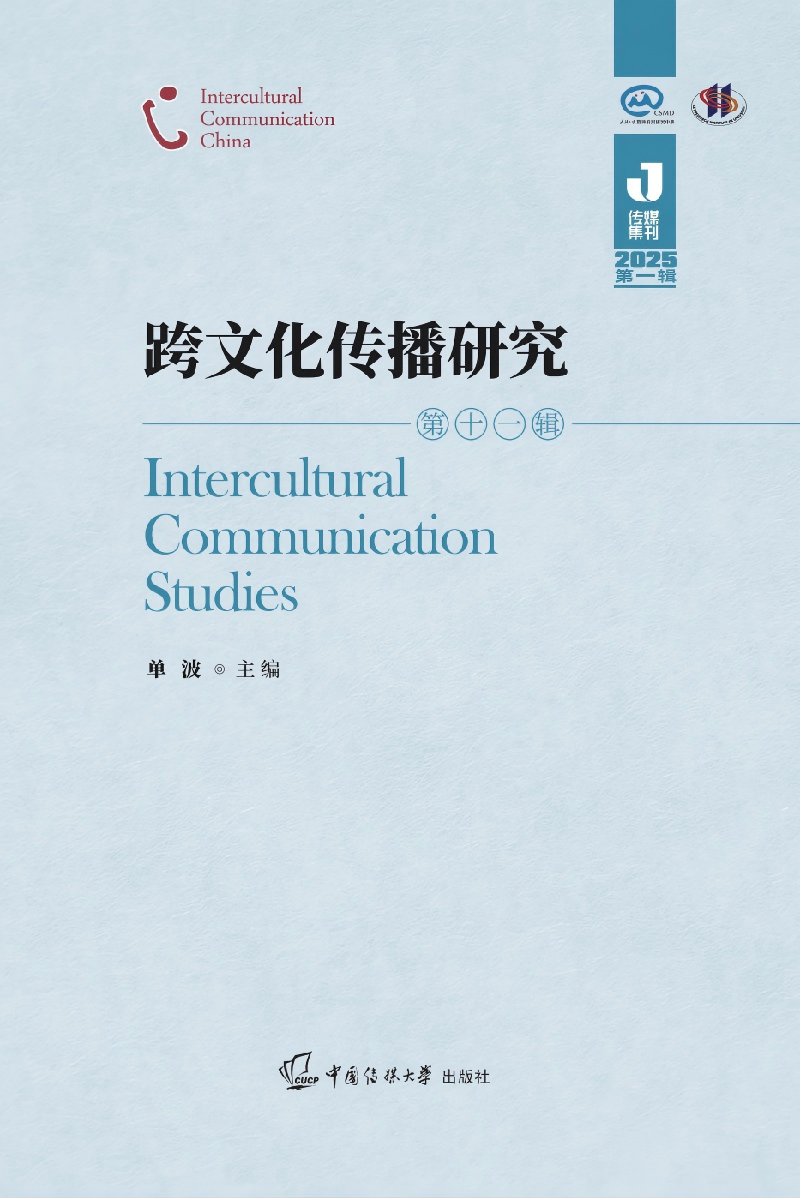
田野旅行:一项跨文化民族志研究的实践与反思
金玉萍
摘要:田野是民族志研究得以展开的核心场域。研究者通过进入具有异质文化特征的田野,探索“他们是谁”“我们是谁”,这项工作本质上是一场跨文化的田野旅行。民族志研究也是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田野与媒介技术密切相关,形成了乡村与城市、线上与线下等多元田野空间。本文结合笔者的民族志田野实践认为,田野的选择通常要根据探寻问题所决定,而应对跨文化田野的挑战需要做好学术、生活与心理准备,这背后的动力又来源于跨文化田野中偶然又必然的惊喜发现。反思跨文化田野之旅,在认识论维度,置身真实生活才能得以用整体观的视野认识田野;在方法论维度,研究者要在田野的具体文化情境中挖掘人们的社会实践并进行意义书写;在本体论维度,跨文化田野不是物理场所,而是被众多社会因素影响和建构的社会空间。
关键词:民族志;跨文化;田野
一、传播学民族志研究中的田野
田野是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田野在哪里”是民族志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人类学早期的经典田野往往是不熟悉的、不同的、地方性的,具有比较鲜明的跨文化色彩。人类学家大体都抱着对陌生社会的强烈好奇心,进入田野,与当地人交往,努力融入当地生活,捕捉发生在田野中的各种故事,以理解他者的眼光介入生活。
西方学者的人类学研究起源于航海、探险以及殖民活动,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向国外,投向未开化的部落,经历了由研究“他们是谁”到研究“我们是谁”的转变。我国的民族志研究则从观察自己,思考“我是谁”开始。20世纪30年代,我国边疆危机加深,带着关于国家、国族与民族的思考,一些学者开始了对西南边疆的田野工作。边疆危机引发的论争也变成国家与国族观念演变的契机,这段学术史很自然地变成了重新理解和书写民族与国家的历史。1933年,凌纯声和芮逸夫在湖南进行苗族调查,是我国较早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他们于1940年写就《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些边疆民族调查亦开启了学术传统的转化。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与林耀华的《凉山夷家》,费孝通和张之毅的《云南三村》、许烺光的《祖荫下》、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等这些中国早期民族志研究的经典作品,无一例外都具有跨文化的性质。
所以说,民族志研究中的田野从一开始就具有跨文化的特性,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无异于跨文化之旅,奈吉尔·巴利在《天真的人类学家》和《倒霉的人类学家》中就生动描绘了人类学家在陌生田野遇到的一个个新鲜有趣、尴尬奇怪的故事。在或悲或喜、或哀或乐的田野旅行中,人类学家理解“他者”,架起不同文化沟通的桥梁。同时,由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在田野中搜集资料,采用自然主义的发生机制,注重对意义的阐释和深描,具有良好的包容性,很快突破学科界限,被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广泛运用。
传播学与人类学的相遇,始于“媒介”。纸、笔是人类学家记录书写的基本工具,作为最初的辅助设备,媒介也是田野故事走向大众的重要途径。随着广播电视、录像机、随身听的发展,民族志研究开始把媒介自身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关注与大众传媒相关的多元社会实践,探索其中蕴含的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伯明翰学派为传播学中的民族志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肇始的新受众研究则把其推向高潮,使其突破欧洲大陆走向全球,其影响延续至今。在我国,这一过程始于21世纪初期,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而被研究者大量使用。笔者对2022年1月至2024年10月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上的文章进行检索。首先以“民族志”“田野”“参与式观察”为关键词在“篇关摘”和“全文”内搜索,然后逐一进行人工筛选,统计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和梳理介绍民族志方法的论文数量。检索发现以上两类论文共计114篇,占四大刊总刊稿数量的8.11%,其中,《国际新闻界》中两类论文占比为13.26%,《新闻大学》中两类论文占比为11.59%。研究议题涉及亚文化、数字劳动、媒介使用、情感传播、乡村传播等。民族志方法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可见一斑。
传播学民族志研究中的田野,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媒介技术不断打破田野的边界,从乡村到城市,从线下到网络,传播学民族志研究中的田野呈现多元发展趋势。仍以四大刊近三年刊发的有关民族志方法的论文为例,以“线下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章占49.1%,以“网络民族志”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章占28.1%,以“线下田野调查、网络民族志”相结合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章占15.8%,还有少量研究与引介多点民族志、踪迹民族志、录像民族志等的文章。田野的空间迁移,产生不同的运行逻辑,进而带来社会空间的变化。
二、我的跨文化田野实践
高丙中先生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的总序中写道:“学术并非都是绷着脸讲大道理,研究也不限于泡图书馆。有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研究者对一个地方、一群人感兴趣,怀着浪漫的想象跑到那里生活,在与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们生活的故事,最后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开始有条有理地叙述那里的所见所闻。”这段话非常贴切地描写出了我自己进行田野研究的初衷与目的。在早期的学术经历中,我通过一串串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时候,就对日常生活中受众对大众传媒内容的理解和接收情况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在新疆这样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形态丰富、宗教信仰迥异、各种文化荟萃的地区,不同民族的观众观看那些从媒介内容生产者意图出发制作的电视节目时,会存在文化差异吗?他们是如何理解其意义的?这些意义是如何生成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吸引我进入田野,期望获得“生活中的故事”。
(一)田野在哪里?
田野的选择通常要根据研究者想探寻的问题来决定。我对于田野调查的想法开始于2008年。彼时电视还是最重要的家用媒介。电视能打破物理空间界限,冲击区域文化的封闭性,创造超越时空的联系。通过电视,观众可以随时见到自我与他者,体验各种差异性存在,产生认同的欲求。所以,电视往往被学者与全球化、民族国家、族群、文化认同等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我希望从受众的电视使用中了解族群、国家等抽象观念的构成性动因,研究电视如何连接家庭、国家与国际领域,维持各种想象的共同体。这决定了田野应该放置在电视已经嵌入受众日常生活,其社会文化效果产生持续影响的地方。根据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我最终确定了三个衡量指标:人口比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成立县广播电视台的时间。根据这三个指标对全疆的六十多个县进行筛选,有三个县符合要求,之后再考虑便利性因素,确定最终入选的县级田野点。沿袭我国民族志研究的村庄传统,我从入选的县中将田野地点确定在托台村。
(二)如何进入田野?
托台村位于县城的城乡接合部,由五个自然村构成,居住着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多个民族的群众。由于城区改造、人口流动、房屋买卖等原因,自然村的行政区划边界逐步变得模糊。托台村在自然条件方面缺水、多风、干旱,当地传统上以农业为主,为发展经济,地方政府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退粮还经”,有些农户从事小型养殖业、简单加工业、零售业。
托台村对于作为研究者的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这意味着进入田野的过程也是跨越文化障碍的过程。跨文化田野工作需要研究者不断去解决问题:怎样才算进入田野?如何跟村民交流?如何克服文化休克?如何让村民敞开心扉?如何融入村民家庭?等等。村庄可能不是想象中的相对集中的物理空间,不是一栋栋房屋的简单集合,研究者常常会产生行走在田野却又像是在田野之外的感觉,怎么才算进入田野是研究者需要反复考量并解决的问题。在跨文化田野中,研究者会面对村民的好奇、不解、排斥甚至抗拒,如果语言不通,则无异于雪上加霜。正是因为如此,马林诺夫斯基才提出掌握当地语言是从事人类学研究的要件。跨文化田野工作中还极可能遇到文化休克现象,研究者必须将进入田野的热情转化为田野工作的韧劲,不言放弃,坚持到底。格尔茨在和当地人一同逃跑之后获得当地人的认可,迈出了田野工作的关键一步。所以,田野资料的获取来源于参与观察和访谈,更来源于研究者与当地人的同吃同住同劳动,融入村民家庭生活。由于媒介使用的私密性,这一点对于研究者尤其重要。
进入跨文化田野,需要研究者做好前期准备。首先是学术准备。民族志研究要在田野工作中逐步明确研究问题,但不意味着不做准备就进入田野,而是要提前熟悉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明确自己的研究目标,对未来的田野研究重点有多种预判和想象,带着相关领域的学术积累和开放的学术心态进入田野。其次是生活准备。跨文化的田野基本是研究者之前不熟悉的、陌生的地方,要提前了解当地的自然条件、气候状况、风土人情,要具有应对气候、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的勇气。最后是心理准备。对进行跨文化研究的民族志学者来说,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物质条件的不适应是比较好克服的,最难的是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让他们对研究者熟视无睹,把研究者看成自己村庄的一分子,这样研究者才能从田野运行的自然状态中获得真实材料。这个过程通常比较漫长而艰难,需要研究者始终保持学术好奇心、探索未知的热情和应对挑战的笃定。
(三)田野旅行中的“惊喜”
跨文化田野研究虽然辛苦,但田野中可能随时出现的“惊喜”恰恰是民族志研究的魅力所在。当地人的文化中一定存在不轻易让局外人了解的方面,而这些往往又是研究者必须获取的。在我的田野之旅中,当我对当地人如何通过电视勾连起地方、国家和全球而百思不得其解时,在某次深度访谈中,我遇到了一位健谈的退休女教师;在我为当地人如何从电视使用中获得族群或者宗教方面的情感体验而苦恼时,接纳我住在家里的一位和蔼而消息灵通的大叔,在我们的一次日常聊天中对我敞开胸襟;当我不知道卫星电视天线的安装和当地人电视使用之间的关系而导致从媒介技术角度分析受众电视使用遇到瓶颈时,马路边偶遇的一位从事卫星锅安装工作的年轻人为我解开了疑惑;还有陪我做深度访谈的一位大学毕业生、八户各具特色的家庭、很多位热心而友好的村民,让我了解了茶会、族谱记忆、木卡姆表演以及坎儿井记忆......一个个瞬间构成田野研究的“惊喜”,让我体验到田野研究的无穷魅力和蔓延着的喜悦,也让我为田野研究而着迷。
田野中的“惊喜”是偶然的、没有任何征兆的不期而遇,但又是研究者和当地人朝夕相处的必然。研究者很难期望一进入田野就收获“惊喜”。“惊喜”往往会在研究者对研究问题越来越明确,资料的积累越来越多,心中的疑惑也越来越聚焦的情况下不期而至。研究者只有深入当地人的生活,让当地人完全接纳,成为他们的朋友,甚至意识不到研究者的存在是对他们生活的打扰,才能收获“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美妙体验。
三、跨文化田野之旅的反思
(一)置身真实生活的重要性
民族志是一种把研究者自己作为研究工具的研究方法。置身其中,是跨文化田野研究的必要条件。与入户调查和询问、深度访谈相比,“参与其生活进行观察”在获得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上是非常不同的。一些现象靠询问是根本没有希望获得的,只能在完全具体的现实状态中被观察。对此,西尔弗斯通曾指出:“探询观众的问题不是要探询一组预先安排好的个人或已严格定义的社会团体,而是应深入到一系列日常实践和话语中;正是在这些实践和话语中,观看电视的复杂行为与其他行为并置在一起。”
置身真实生活才能得以用整体观的视野审视田野。民族志的使命是以整体的方式写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整体观,意味着注重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联系。我在田野工作中发现,电视之于观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电视节目,还与电视机的摆放位置、家庭房屋的物理空间关系、电视节目的接收方式、家庭结构、经济条件等产生勾连,由此衍生出作为物的电视、作为技术的电视和作为媒介的电视之分析框架。运用整体观观察、记录、体验田野,才能为把握观众对电视节目的解读意义提供丰富的注脚。如果不置身于真实生活,那将无法挖掘观众电视使用的丰富意涵。
(二)随时记录,做好田野笔记和意义书写
民族志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运用“撰写”让“日常”与“历史”和“环境”发生关系。民族志的书写是对田野现场工作进行的文化解释,文本写作带有“高度情境性”。研究者要在田野中发掘人们的经验和社会实践,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做整体性的观察与书写。
随时记录是田野工作的基本要求,研究者要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完完整整记录下来。从田野回到研究室,仔细分析整理田野笔记,开始意义的创造过程。不同于量化研究强调外在效度,追求对外部世界的规律性探寻,民族志方法强调的是内在效度,追求对意义的阐释和深描。也正因如此,民族志研究方法引发了一些争议。对此,罗伯特·埃默森等在《如何做田野笔记》中谈道:“由于描述过程中加入了研究者的感受和阐释,所以很可能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情况和事件的描述也会各不相同。”研究者需要以局内人的立场,依托丰富的田野经验材料,进行意义书写。严格来说,所有的民族志研究都是既典型又不典型的。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明确指出:“研究的地点并不是研究的对象。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
在民族志方法内部,研究者通常会有不同的学术立场和理论倾向。在理论取向上,民族志方法处于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自然主义传统、阐释主义传统和后现代的批判传统。自然主义传统通过科学规范支撑起民族志研究的“科学性”时代,注重现象描述,对研究现象做后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和分析,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阐释主义传统看到了人和社会的相互性和交往性,注意到研究者在理解和解释中的能动作用,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以对文化符号的破译及对文化行为的深层描写及阐释而备受瞩目。后现代的批判传统认为任何研究都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关注社会改革,采取批判理论的取向。我国的传播学民族志研究主要呈现出描述和阐释的取向,而西方学者则一贯使用“批判的民族志方法”进行受众研究。
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理论取向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意义书写,在这一过程中耙梳资料,进行理论化,完成田野旅行的最后一站。
(三)作为社会空间的田野
跨文化田野研究中的田野到底意味着什么?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尤其是基于网络文本的各类民族志方法的出现,对田野研究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
罗伯特·库兹奈特在《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中将“网络民族志”描述为:“一种基于线上田野工作的参与式观察。它使用计算机中介传播作为资料来源,以获得对文化或社区现象的理解和描述。”斯图尔特·盖格(R. S. Geiger)提出“踪迹民族志”(trace ethnography),着力于深挖社群参与者的网络活动和关于相关事件的言语痕迹,进行重新组织和深度描写,即一旦对话数据被解码,网络中存在的记录痕迹就可以被研究者分析、组合成丰富的互动叙述,从而探讨社群关系、交往实践、知识传播与建构、平台制度和其他社会、组织现象。“多物种民族志”的目的是理解多元物种“交染”共生的世界生成过程,其研究关切主要在环境研究、科学技术研究和动物研究三个领域。多物种民族志拓展了传播学研究范畴的反身性以及学术表征范畴的开阔性,其兼容并包的学术视野与知识谱系可以很好地渗透学科壁垒,用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姿态对现实问题进行移步换景的观照。
从线下民族志到网络民族志,民族志研究中的田野由实在的田野转向虚拟的、离散的流动空间,多物种民族志的提出又使田野呈现“物质”转向,扎根在更为丰富多元的空间中。可见,传播学民族志研究中的田野不仅是物理场所,而是由空间、时间、历史和关系等维度构成的综合体,是被众多社会因素影响和建构的社会空间。田野研究,需要深入分析诸多关系构成的社会空间。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社会空间由社会生产,同时也生产社会。在媒介深度参与建构社会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参与生产的,即媒介化空间。媒介通过创造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人际交往模式而改变社会空间的边界,打破了原本空间内的行为机制,建立新的空间秩序,进而在重塑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生产社会”。
跨文化民族志研究,尤其是受众研究,要努力去理解生活在某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某一类人,诠释有意义的媒介使用行为。这需要研究者详尽“阅读”文本,思考它传递的多种信息,结合具体情境解释隐藏在文本中的意义,形成对部分和整体关系的深刻理解,寻找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才能获得意义。由于媒介使用行为的私密性和家庭化,这类研究进入真实的田野空间愈发困难。网络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实体空间介入的障碍因素,更方便操作,但对于研究者详细“阅读文本”也提出一系列挑战,在脱离真实生活环境后,依靠阅读网络文本能否诠释媒介使用的丰富意义尚值得商榷。
不论田野的空间向度如何迁移,跨文化的民族志方法不能完全脱离实地的田野调查。只有通过现实中的田野经历,研究者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地方性知识,理解和反思研究对象媒介使用的意义,而在田野工作中经历的种种挫折、喜悦抑或文化休克在另外一层意义上赋予研究者奇妙的旅行体验,吸引研究者心向往之。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润疆背景下县级媒体的多语种传播实践及效能提升”(项目编号:23BXW1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用参考
金玉萍.田野旅行:一项跨文化民族志研究的实践与反思[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5,(01):58-68.
作者简介
金玉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